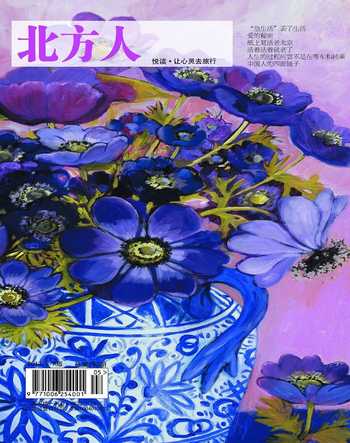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如何管理國(guó)家“錢袋”
周鑫宇
議會(huì)掌管國(guó)家預(yù)算權(quán)力,是現(xiàn)代政體的基本標(biāo)志。既然現(xiàn)代國(guó)家是民主的或者人民的,那么國(guó)家的錢怎么花,自然交由人民選舉的代議制機(jī)構(gòu)來決定。這作為一種政治觀念,說起來很容易,全球公認(rèn),但是具體如何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錢袋”的科學(xué)、透明、有效管理,就是一項(xiàng)艱難的國(guó)務(wù)了。美國(guó)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現(xiàn)代民主國(guó)家,其國(guó)家預(yù)算決策以成熟、嚴(yán)格和科學(xué)著稱,但有時(shí)也出演政府“關(guān)門”的鬧劇和利益輸出的丑聞,背后反映的政治現(xiàn)象饒有趣味,亦發(fā)人深思。
世界上最難念的“財(cái)政經(jīng)”
美國(guó)的財(cái)政經(jīng)怕是世界上最難念的。2012年美國(guó)的聯(lián)邦財(cái)政預(yù)算計(jì)劃總額達(dá)3.7萬億美元,是中國(guó)中央財(cái)政預(yù)算的近五倍,也是世界上花錢最多的政府。如何決定這筆巨賬的撥付和使用,權(quán)力主要掌握在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參眾兩院手中。美國(guó)憲法第一條明確賦予了美國(guó)國(guó)會(huì)掌握國(guó)家的征稅權(quán)、舉債權(quán)和撥款權(quán),再加上在財(cái)務(wù)方面的監(jiān)督權(quán),使得美國(guó)國(guó)會(huì)掌握著包括收入和支出在內(nèi)的全面的“錢袋子權(quán)力”(Power of Purse),成為美國(guó)國(guó)家財(cái)政的“管家主婦”。在這之中,政府財(cái)政預(yù)算的審議、決定和監(jiān)管,又是美國(guó)國(guó)會(huì)最主要的財(cái)務(wù)權(quán)力和工作內(nèi)容之一。
當(dāng)然,“分權(quán)制衡”的政治設(shè)計(jì)不會(huì)讓國(guó)會(huì)在預(yù)算程序中一手遮天。花錢的權(quán)力還掌握在總統(tǒng)手中。因此,每年美國(guó)聯(lián)邦財(cái)政預(yù)算的出臺(tái)過程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行政機(jī)構(gòu)和立法機(jī)構(gòu)的互動(dòng)過程。這一過程也隨著總統(tǒng)和國(guó)會(huì)的博弈而分為三個(gè)階段:
第一步自然是總統(tǒng)先提出他想花多少錢。每年1月初,美國(guó)聯(lián)邦政府會(huì)提出下一財(cái)年的預(yù)算計(jì)劃。各政府部門想要花多少錢、合理性何在、預(yù)計(jì)效果如何,都要在方案中詳細(xì)報(bào)告。白宮編制這樣的文件是十足的技術(shù)活,要從所有的政府部門中收集、整理和精算數(shù)據(jù),耗時(shí)費(fèi)力,還要“講政治”,能夠平衡部門間的利益沖突。
當(dāng)總統(tǒng)的預(yù)算方案提交到國(guó)會(huì)后,國(guó)會(huì)就開啟預(yù)算立法程序——注意,不是批準(zhǔn)程序。因?yàn)閼椃ㄒ?guī)定預(yù)算案的提案權(quán)掌握在眾議院。因此,從理論上來說,總統(tǒng)辛辛苦苦搞出來的預(yù)算計(jì)劃只是一個(gè)“建議”,國(guó)會(huì)可以參考,也可以完全不理會(huì)。無論怎樣,國(guó)會(huì)需要自己提出一個(gè)真正的預(yù)算案,然后表決通過。
這時(shí)候技術(shù)門檻的問題就又出來了。總統(tǒng)方案中的那一大堆專業(yè)數(shù)據(jù),不是每個(gè)議員都看得懂的。國(guó)會(huì)各委員會(huì)的委員們即便對(duì)相關(guān)領(lǐng)域相對(duì)精通,也干不了一個(gè)會(huì)計(jì)師的活。因此,國(guó)會(huì)議員們也有一幫技術(shù)人員幫忙。這就是至關(guān)重要的“國(guó)會(huì)預(yù)算局”。在“國(guó)會(huì)預(yù)算局”的專業(yè)人員幫助下,從2月份開始,美國(guó)國(guó)會(huì)參、眾兩院各委員會(huì)開始圍繞自己職責(zé)范圍舉行聽證會(huì),傳喚政府官員解釋情況,收集有關(guān)資料。國(guó)會(huì)預(yù)算局也會(huì)為國(guó)會(huì)議員提交自己的專業(yè)建議報(bào)告。根據(jù)這些信息,各委員會(huì)做出預(yù)算評(píng)估,并在兩院的預(yù)算委員會(huì)形成一份初步的預(yù)算共同議案。大概到4月份的時(shí)候,參眾兩院會(huì)分別就自己的預(yù)算共同議案進(jìn)行表決,在預(yù)算授權(quán)總額、赤字、債務(wù)水平等關(guān)鍵數(shù)據(jù)上形成基本框架。
有了共同議案作為基本方向,眾議院各委員會(huì)和撥款委員會(huì)各小組開始擬定正式預(yù)算授權(quán)法案和撥款法案,并先后提交眾、參兩院全體表決。如果兩院意見不一致,還要組成聯(lián)合委員會(huì)進(jìn)行協(xié)商和再次表決。通常來說,一份年度預(yù)算案的最終通過要在國(guó)會(huì)經(jīng)歷10次左右的投票,最少歷時(shí)數(shù)月之久。
預(yù)算背后的“分權(quán)制衡”
從前兩個(gè)階段可以看出,美國(guó)國(guó)會(huì)把握著預(yù)算制訂的主要程序性權(quán)力。國(guó)會(huì)通過復(fù)雜的制度設(shè)計(jì),盡力實(shí)現(xiàn)預(yù)算審議的科學(xué)性、專業(yè)性和民主化。
然而總統(tǒng)仍然被賦予了制衡的手段。國(guó)會(huì)預(yù)算案表決通過以后,預(yù)算程序就進(jìn)入第三階段:總統(tǒng)簽署批準(zhǔn)。理論上來說,總統(tǒng)是可以否決國(guó)會(huì)的預(yù)算法案的。但如果國(guó)會(huì)兩院能夠再次以2/3多數(shù)通過議案,則可推翻總統(tǒng)的否決,形成最終法案。
這樣的戲劇性事件看起來似乎很刺激,但一般美國(guó)總統(tǒng)和國(guó)會(huì)很少為了預(yù)算的事情走到使用否決和再否決的地步。在意見分歧的情況下,總統(tǒng)和國(guó)會(huì)兩黨領(lǐng)袖通常寧愿長(zhǎng)時(shí)間“協(xié)商”,最后出爐一份彼此都能接受的議案。不過這一“協(xié)商”的過程有時(shí)未免太長(zhǎng),以至于到了10月份新財(cái)年開始的時(shí)候還沒有解決,美國(guó)政府就會(huì)面臨無錢可用、“關(guān)門大吉”的尷尬了。美國(guó)2011年度財(cái)政預(yù)算甚至直到2011年12月才簽署,這時(shí)候整個(gè)財(cái)年都已經(jīng)結(jié)束,該花的錢也都大多被一個(gè)個(gè)臨時(shí)撥款方案花走了,預(yù)算幾乎變成了決算。
顯然,在美國(guó)預(yù)算制訂制度設(shè)計(jì)的背后最大的特征就是“分權(quán)制衡”,尤其是總統(tǒng)與國(guó)會(huì)之間的相互制衡。這一點(diǎn)即使是與英國(guó)這樣的議會(huì)制民主國(guó)家相比也大為不同。世界上大多數(shù)國(guó)家都實(shí)行權(quán)力分置的制度,以便分工和監(jiān)督;而美國(guó)分權(quán)的目標(biāo)卻是在機(jī)構(gòu)之間設(shè)置程序上的麻煩,從而從根本上遏制政府的權(quán)力。“國(guó)家錢袋”的管理就是實(shí)現(xiàn)這種遏制的重要手段,并被美國(guó)國(guó)父鄭重地寫在了憲法的開頭。
好的預(yù)算:制度還是觀念?
美國(guó)國(guó)會(huì)的預(yù)算審議制度經(jīng)過了上百年的演變和成熟過程。今天,我們喜歡討論這種制度的優(yōu)劣,看它如何帶來了預(yù)算的透明、科學(xué)、易監(jiān)督,或者如何造成了效率的低下。然而,如果更深一步地觀察,在法律條文、操作程序、機(jī)構(gòu)設(shè)置和制度框架的背后,真正決定美國(guó)預(yù)算政治的還是當(dāng)時(shí)的國(guó)家處境、政治格局,甚至是最容易被忽視的政治觀念和信仰。
比如,美國(guó)的預(yù)算制度是主張“權(quán)力制衡”的,其最終目的是制約政府的權(quán)力。可是在兩百年的時(shí)間里面,美國(guó)政府的權(quán)力實(shí)際上呈現(xiàn)不斷擴(kuò)大的趨勢(shì),花的錢也越來越多,稅收越來越高、債務(wù)越來越大,甚至形成了今天讓全世界受累的高額赤字。這背后的根本動(dòng)因,是美國(guó)成為世界霸主的需要。這是美國(guó)政治最根本的潮流和大局。在這個(gè)過程中,美國(guó)國(guó)會(huì)與政府一起,提供了至關(guān)重要的財(cái)務(wù)支持。
又比如前文提到的“協(xié)商一致”實(shí)際大于“制約對(duì)抗”的現(xiàn)象。妥協(xié)精神是美國(guó)民主的長(zhǎng)久根基。大多數(shù)時(shí)候,較高程度的政治共識(shí)保證了美國(guó)民主的穩(wěn)定性和較好效率。然而,2011年美國(guó)政治出現(xiàn)“極化”趨勢(shì),兩黨內(nèi)斗加劇、預(yù)算難產(chǎn),政府?dāng)?shù)次面臨關(guān)門。這種變化的背后不是制度決定的,而是整個(gè)國(guó)內(nèi)政治環(huán)境的惡化,美國(guó)政界對(duì)此深感憂慮和恥辱。
最后,我們還是要注意,即便是美國(guó)如此追求“制衡”的制度,也未必能根除腐敗。在出臺(tái)預(yù)算的過程中,許多國(guó)會(huì)議員往往都會(huì)在其中加上一些“專項(xiàng)撥款”,比如在自己所在的選區(qū)修條路、為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團(tuán)撥些項(xiàng)目款之類的。這種專項(xiàng)撥款濫用無度,鬧出了很多丑聞,包括很多臭名昭著的“面子工程”,可是卻得到了相應(yīng)選民的選票。在花錢問題上,讓國(guó)會(huì)制約總統(tǒng),讓選民制約國(guó)會(huì),可誰(shuí)來制約選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