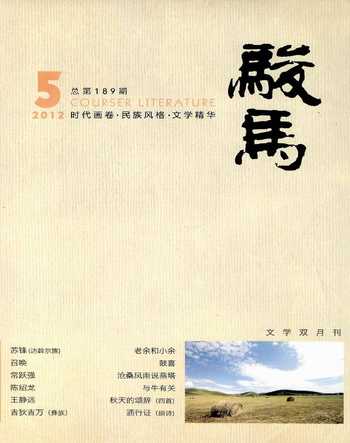鼓喜
召喚
一
荷花的嫁期正是金狗出師的日子。
三年的光陰,像刀削豆腐,“嗞”地一下就沒了。
三年前,義父馬蹬鼓牽著金狗來龍頂鼓的門下“摻師”學藝時,還是個愣頭青。眨巴眼,金狗就成人了。成人的一個最明顯的標志,就是想女人。是那種巴心巴肝地想。這一點,金狗以為只有他清楚。其實,師父龍頂鼓早就看出了他心里的小九九。當然,也沒有逃脫荷花的眼睛。
江漢平原興給死去的老人打喪鼓,是沿襲了多年的風俗。義父馬蹬鼓之所以名揚荊楚大地,就是得益于祖傳的“腳蹬鼓”。想想,一只龐大的牛皮鼓,被鼓師雙腳“嗖”地蹬上天,再不慌不忙地拉完一泡長尿后,回鼓場剛一躺下,雙腳就穩穩地接住了鼓。嘖嘖,這絕技了得。非馬蹬鼓莫屬。馬蹬鼓有意把祖傳的絕技,傳給兒子馬光亮,可兒子不是那塊料,他只得打義子金狗的主意。
義父送他來龍頂鼓的門下摻師,目的就一個,把他“捧”成喪鼓場上的“全胯子”,就是既能腳蹬鼓、又會頭頂鼓的鼓師。
龍頂鼓的絕,跟馬蹬鼓的絕不同。后者靠“腳蹬”,前者憑“頭頂”。龍頂鼓不僅把鼓頂出“花”來,還有蒙眼頂“盲鼓”的本事,無論鼓在哪個方位、何種角度,龍頂鼓的頭,都能準確無誤地頂上。赫赫有名的龍馬兩家幾代鼓師,向來都是老死不相往來,你蹬你的鼓,我頂我的鼓。據說,有一年,荊州城里的一專員為老父超度亡魂,硬是把第一代龍馬兩位鼓師請到府上,聯袂演繹了一場“腳蹬鼓”“頭頂鼓”的“全胯子”喪鼓,讓古城人大開了一回眼界,從此,也讓龍頂鼓、馬蹬鼓名揚天下。
到了這一代,龍頂鼓和馬蹬鼓兩家的關系活絡了一些,以至于兩家搭上了親家。要不是看在親家的情份上,龍頂鼓咋舍得把祖傳的“頭頂鼓”傳給馬蹬鼓的義子金狗呢。三年前,當馬蹬鼓提出讓金狗來龍家摻師學頭頂鼓的藝時,龍頂鼓的心里著實“咯噔”了一下。可馬蹬鼓的話,到底是摧毀了他心里的最后防線。“親家,總不能讓你龍家的頭頂鼓失傳啊,何況,金狗是我的義子呢。”一想到自家祖傳的絕技瀕臨失傳,加之按“傳男不傳女”的古訓,又不可能傳給女兒荷花,龍頂鼓心一橫,就應承了下來。
當一只纖纖玉手,把金狗牽進龍家時,那一刻,他感到眼前豁然一亮,淤積了十六年的黑暗,倏然消失。
玉手把他攙到竹椅上坐下,說,我叫荷花,叫我荷花好了。你呢?
他扇了扇鼻翼,似乎還沉在一縷荷花的幽香里,半天才說,金狗。
嘻嘻,金狗。荷花丟下這話,就走了,卻把彌久的幽香留在了他心里,一直彌漫到現在,或許永遠。
那時,龍頂鼓望著金狗,竟閃出了一個怪怪的念頭:要是金狗是我龍家的女婿,該多好啊!
二
金狗今日出師。
荷花今日出嫁。
怎么會是今日呢?
怎么偏偏就是今日呢?
金狗一直打坐著,從雞鳴三更,又到五更。
陪他打坐的,是師父龍頂鼓。
師父就打坐在對面,距他僅三個步子。
師父說,天亮了。
金狗說,天亮了。心卻跟他的瞎眼一樣,黑沉沉的。
師父說,今日你出師。
金狗說,嗯。心卻說,我怎么偏偏今日出師呢?荷花怎么偏偏今日出嫁呢?
師父說,今日拗場子。
“拗場子”是行話。大有黑白顛倒、喜怒互換的意思。
金狗一頭霧水。想再怎么拗場子,也不可能把他的瞎眼,拗擰出亮來。
師父說,鼓喜。
金狗說,鼓喜?
師父說,就是打喜鼓。
金狗說,給誰?
師父說,荷花。
金狗一哆嗦,雙手合十的手掌,打胸口垂到了襠間。
金狗不解,我學的是打喪鼓——專給死人。
師父說,樂極才生悲,不知喜樂,怎懂傷悲?喜從悲來,悲從喜來,生兮伴死兮,死兮伏生兮。這是道。
金狗說,道?
師父說,道可道,非常道。只能意會,不可言傳。
按道上的規矩,喪鼓師在出師給亡者打喪鼓之前,得給結婚的新人“鼓喜”一回,讓鼓師去悟“喜”中有“悲”的內涵,或是給剛出生三天的嬰兒“喜三”,讓鼓師領悟“生”“死”輪回之道。
可是,這些世俗的非凡之道,師父不得明說,也說不了,全仗鼓者去徹悟。
三
今日,荷花就要嫁給義父的兒子馬光亮了。金狗一直想不通,婚期偏偏選定今日不說,竟還要他去“鼓喜”。
怎么會這樣呢?金狗糊涂了,真不知師父是什么意圖。
其實呢,鼓喜沒啥的,不就是給新郎新娘助助興、祝祝福、添個樂子加個彩么。這事兒要是擱在別人頭上,也沒啥的,問題是,新娘子是——荷花啊!
馬光亮跟金狗同庚,也跟金狗一個被窩里滾大。
金狗六歲那年成了孤兒。打喪鼓的馬蹬鼓見了心疼,就把小瞎子抱回了家。從此,馬光亮跟金狗像親兄弟一樣打鬧、說笑,在一個被窩里睡了整整十年。
什么猜謎語啊,打歇后語啊,成了他倆的家常便飯。
馬光亮說,打串謎語你來猜:天生眼——
金狗說,星星。
馬光亮說,地長皰——
金狗說,墳塋。
馬光亮說,水長骨頭——
金狗說,冰。
馬光亮說,路接腰——
金狗說,橋。
馬光亮心服口服。
金狗說,我打你猜。
馬光亮說,好。
金狗說,被窩里放屁——
馬光亮半天語塞,猜不出。
金狗說,從腳臭到頭。說完大笑,這是我瞎編的。
馬光亮就朝金狗一腳蹬去一個歇后語,睡著吃炒米——歪嚼。
金狗倏地從被窩里鉆過來,摟著馬光亮睡,說,兩個啞巴睡一頭——好得沒話說。
不知怎的,今日荷花嫁給馬光亮,金狗的心頭涌出一股莫名的醋意;今日去給馬光亮鼓喜,他是那么地不甘不愿。
師父刻意把出師地點選在放鷹臺,是有意的。因為放鷹臺巫氣彌漫,是善好的開悟之地。
此刻,師父就打坐在對面,開始用嘴皮子“頂鼓”:
頭頂鼓喲——開天鼓,
天鼓翻過坡,引來好多歌。
一唱顛倒歌,先生我,后生哥,
姆媽出嫁我打鑼,爺爺結婚我抬盒。
鼓打金狗的頭頂飛過,帶起一陣狂猛的旋風。
頭頂鼓喲——相思苦,
二唱情愛歌,牛郎要過河,
苦等幾千年,織女隔天河。
鼓又跳到河邊,河風浩蕩,蕩得天河越來越寬,牛郎織女越來越遠。
一陣風掠過,樹葉沙沙地翻過去,呈陰面,又沙沙地翻過來,呈陽面。金狗明明聽見了,又似乎什么也沒聽見。
四
在學藝的三年里,金狗大都在東廂房里“默鼓”。實在憋不住了,他就唱喪歌。這些喪歌,都是義父馬蹬鼓唱的,當然也有師父龍頂鼓唱的。偶爾,他也會唱一些撩情撥意的情歌,讓一直憋著的心軟和一些:
日頭漸漸往下藏,
情姐出來收衣裳,
衣裳搭在肩膀上,
手搬竹竿往上揚,
一收衣裳二看郎。
歌子隨了小南陽風旋到院子,驚了正在收衣裳的荷花。咦,怪唦!金狗不是瞎子么?他、他、他……?她懷疑他不是睜眼瞎,就踮起腳尖,朝東廂房打望了一眼,她沒想到,他正坐在窗前,睜大雙眼,瞅著自己呢。
荷花的心被瞅得一熱,就撩起額前的一縷青絲,唱:
太陽下坡往西歪,
姐打字謎情哥猜,
言旁加午由郎想,
目旁加分請郎猜,
情哥若是猜對了,
人旁言字拿出來。
金狗做夢都沒想到,自己無意唱的歌子,竟歪打正著地引來了有心人的《字謎歌》。他思忖了一會兒謎底,突然一拍腦殼:猜謎是假,傳情是真啊。
情姐生來秉性乖,
打出字謎我來猜。
言旁加午許配我,
盼望你我結成雙,
情姐若是不嫌棄,
人旁言字捎信來。
荷花只覺得臉紅心跳,就用衣袖掩住半個臉兒,往閨房顛,嚇得一群雞滿院子亂飛。
砍腦殼的,還瞎子呢,比明眸人還明亮哩。荷花的胸口像揣著一只驚兔,蹦跳得不敢看東房,怕不小心跟那雙濃眉下的大眼碰上。
荷花時常出神,老是想金狗頭一回邁進家門的情景。花兒,快把東房收拾一下。父親龍頂鼓囑咐。荷花曉得是給濃眉大眼的金狗收拾的。往后,金狗就住在這里了。收拾好屋子,她回到西屋,坐在西窗下發呆。夕照把窗外的一樹桃花,染得花紅葉綠。一根連理枝斜伸進了窗沿,一雙歸巢的黃鸝正在上面啾啾纏綿。這時的花是香的,風是香的,連黃鸝的叫聲,也是香的。荷花的心情無端地好起來。她拿來花繃兒,照著眼前的情景描紅。她描夕陽,描桃花,描連理枝上的黃鸝和鳥鳴,描得她自個的心房也花呵朵的。荷花甩了一下辮子,幾瓣脆氣的鳥啼,落在描紅上,就一浪浪地撥動了她的情愫……
荷花抬頭時,就看見,那“郎兒”真踩了她的歌子,在自家的院子“穿門”。只是,只是那“郎兒”是父親攙著的。
穿了前院,穿后院,穿了東屋,穿西屋。當“郎兒”穿到她的西屋時,那對黃鸝已“跳”到描紅上,叫得歡勢哩。她羞紅了臉,慌亂地把描紅藏在了枕頭下。可那黃鸝的叫聲,卻怎么也藏不住,不時地從連理枝上“跳”到描紅上,又從描紅上“跳”到連理枝上。父親一眼就看出了女兒的秘密。那“郎兒”似乎也“看”到了她的秘密。在她看來,那雙又大又圓的眼睛,怎會看不見呢?
直到父親把“郎兒”牽回東房,荷花還沉在她的心事里,沒出來。
“郎兒”說,師父,只要人領我把這房前院后穿一遍,往后就曉得大門怎么進,后門怎么出了。
父親“哦”了一聲,說,你是天眼啊!
第二天,荷花盯著“郎兒”的大眼,終究把心頭的疑惑說出了口,金哥,你到底是不是……
瞎子。他接過話頭子,就把她心中的疑團說了出來。天生的,好看不中用的睜眼瞎。
她禁不住倒“咝”了一口涼氣,把心頭的憐惜,一絲一縷地抽了個盡。她退出東房,說不出的哀傷險些絆了她一跤。她坐在西窗下,卻想著東房的人,發呆,兩行熱淚滑過臉龐。等娘喊她吃飯時,才發覺嘴角,除了咸,就是澀。
五
“嘭嘭嘭——”
荷花敲響東窗是在一個雨天。窗外的雨點打在芭蕉上,噼噼啪啪地響。芭蕉一款,脆嫩晶亮的響聲就潑了一地。
金狗正心無旁騖地閉目默鼓,入了魔道。
金哥——
她又輕輕地叫了一聲。雨打芭蕉,也打在他的心上。
有雨點從屋頂上漏下來,不偏不倚,落在他的左肩上。他只顧默鼓,又把鼓從鼓心、鼓沿、鼓側頂了七七四十九個來回,才從鼓場上回來,就聽見了夾雜在雨點里的嘭嘭聲。
哪個?
還有哪個?
荷花!
嗯。
雨點越來越大,也越來越急。
雨大,快進來唦。
門“吱呀”一聲就開了。東屋的門原本就沒閂過。她第一眼就瞅見了他被漏雨淋濕的肩頭。
哎呀,你個呆子,看肩頭都打濕了。快脫下,換干的。他笑笑,沒事,又不會把肚子里的飯打濕。她就隨手扯過一條干毛巾,塞進他的肩頭,把濕隔開。
他一下覺得受用了許多。
她找來一個洋瓷盆,接漏雨。一滴一滴的雨點打在瓷盆上,先是丁當丁當的脆響,不一會兒就變成了嘀嗒嘀嗒的聲音。節奏分明的嘀嗒聲,極像兩個人的心跳。
沉默。誰也不說話,摸著心口,靜靜地聽這看似雨滴、實則心跳的聲音。
過了好半天,荷花瞅著他露出了腳趾頭的鞋,說,咦,看你的鞋都小雞拱蛋殼了,我試著給你納了一雙新的,不曉得合腳不。說著,就把疊著的一雙新布鞋遞給了他。
荷花轉身離去,把一屋的雨滴和溫情留給了他。
這是一雙千層底,黑燈絨緞面、白布沿、松緊口……他摩挲著,手指在鞋的每個部位,一指一指地游走,纏綿。剎那間,他的指間漫起一條河流,河面上浮起一朵并蒂蓮,散發著誘人的幽香。突然,狂風乍起,傾盆大雨襲來,水鳥驚飛,蒿草折斷,那并蒂蓮仍是抱成一團,永不分離……
他把新鞋緊緊地貼在心口,癡想著那朵任憑風吹雨打也不分離的并蒂蓮……
沒幾天,就是端午節。端午這天,當地有一些沿襲的習俗。一是掛艾蒿,以驅邪消災、除惡避毒。據說,五月五日是“惡月惡日”,也是“五毒”邪災興風作浪之日,家家戶戶的大門上懸掛一串艾蒿,熏驅邪惡,降以吉祥。一是送端午,凡是訂了婚的女婿,只要到了男大當婚的年齡,不管婚前婚后,都要在五月初五這一天,挑上一簍子黃鱔、兩包荷葉包好的油條、一刀腰條肉,去拜見岳父岳母。
這一天,荷花起了個大早,要到東荊河灘上去采艾蒿,說一人孤單,要金狗去做伴。父說,那就去吧,快去快回。娘正好從廚房出來倒洗鍋水,說,艾采帶露水的。花兒,快些打轉,有稀客要來呢。
荷花曉得娘說的稀客,就是自己的女婿。媒人幾天前就上門來提婚期了,要龍家翻過年來“把人”。當地都興把嫁閨女說成“把人”,就像一件東西,把到該去的地方和人家。
金狗轉了一下眼珠子,說,好的,說不定半路上會碰上光亮呢,就當給你接稀客唦。
荷花在前,金狗在后,就一前一后,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地來到了東荊河堤上。
到了。荷花說,就在這里采。
金狗又轉了轉眼珠子,說,荷花,還是到南堤上去采吧。南堤是光亮的必經之地。
南堤的沒北堤的好。
嗬,天底下的艾都一個香。
那你說,人跟人一個樣么?
說不定。人有同相,狗有同樣。他拗不過她,只好就地采起艾來。這些帶露水的艾,散發著比露水還要晶亮的熏香。
啊,真好聞!荷花突然打了一個噴嚏。
他也打了個噴嚏,把一棵掛滿了一串露珠的艾蒿遞給她。
哎呀!她驚喜地大叫,這露珠一個也沒破哩。
定力。他說,這是道傳給我的定力。
定力?
當然,光定力還不夠,還得有神力。
神力是么子?
神力就是從神性里游出的魂……
荷花在若有所悟,又是茫然不知中喃喃道,你是神人!
返回的路上,他跟荷花一樣,行走自如,腳下的步子,和正常人一樣,沒有半點疙瘩、磕絆,以至于荷花再一次地心生疑惑:你真看不見么?
天生就看不見。
你現在為么子又看見了?
還是看不見。他故意把眼往大里睜了睜。
可你明明像看得見一樣。
來是生路,回是熟路。來跟回,永遠都是兩碼事呢!
荷花是突然發現的,金狗擎起的那棵艾頂上,一顆碩大無比的露珠,像顆藍寶石,晶瑩剔透,閃著五彩鮮活的光亮兒。
荷花驚訝地“呀——”了一聲,這顆露珠好大好亮!
金狗說,這不是露珠。
荷花說,那是么子?
金狗說,夢。
沒想到,一直揣在金狗心窩的這個美好的夢,到底今天卻徹底無望地破滅了。
六
眼看婚期杵到了鼻尖,荷花心里泛起一種莫名的感傷和愁緒。按婚俗,出嫁前一個月,是“繡花月”,待嫁女不下地,把自己關在閨房,趕織各種用品,什么鴛鴦枕啊、繡花鞋啊、連理被啊,盡是一些喜興的東西。身上的,腳下的,床上的,都有。
這天,同村的老了人。師父和師娘一大早就去幫忙了。師父走時,特地囑咐金狗,喪鼓響到雞鳴三更的當口,你再去。他一下子點穿了師父的意圖,師父是要我趕鼓哩!師父“嗯”了一聲,說,喪鼓場上,水深得很,么子意想不到的事都會發生。在場子上混,跟滾釘板一樣,就算你脫了三層五層皮,也不一定滾得出來。師父又說,趕鼓是頭一道門檻,你今就去試試深淺唦。
師父走后,他鬼使神差地穿上了那雙從未穿過的千層底,一邊踱著步子,一邊默鼓。西屋沒有一絲動靜。一直靜到狗把月亮咬上樹梢,西屋才有響動,是一首《繡兜兜》的情歌,纏綿著不盡的相思:
姐在樓上繡兜兜,兜兜要繡那九州:
金官州,銀官州,丙子州,同心州,
行行打架施洋州,紡線織布百里州,
扳罾打網大燕州,桃園結義大荊州,
鐵打的狀元磨盤州,情哥你上來抹兜兜,……
金狗怦怦亂跳的心,一下躥到了嗓子眼,同時,腳板心的一股暖流,也跟著涌到了嗓子眼:
南風輕輕好做鞋,情哥沒拿樣子來,
照著腳印量幾量,心思撲在郎心懷。
穿起來,穿起來,穿起情姐做的鞋,
幫子納的芝麻點,底子納的人字排,
腳上踩的情姐的愛。
東屋的歌子剛落,西屋的歌子又響起:
去年同哥喝杯茶,香到今年八月八,
不信哥到閨房看,床頭開著茉莉花。
不知哪來的膽子,金狗加大了嗓門:
紙貼窗戶舌舔開,一朵鮮花盆內歪。
只要情姐有心意,今晚房門半打開。
可是,荷花怎么也沒弄明白,那晚她半開的閨門和敞開的心扉,一直沒等來她巴望的人……
七
現在,荷花就要出嫁了。
真是鬼使神差,金狗偏偏穿上了那雙鞋底納著并蒂蓮的新鞋,作為鼓手,他要參與“送親”和“接親”的兩套“鑼鼓點子”。江漢平原的鑼鼓點子概由鼓、大鑼、大鈸、馬鑼、小鑼五件擊樂器組成,分別擊打出“咚、哐、鏘……”的聲音。鼓聲熱烈持重,大鑼渾厚奔放,大鈸穩健明快,馬鑼開朗明快,小鑼清脆悅耳。各種曲牌的起頭、高潮、轉承、收尾,均由鼓來引領、掌控。
鼓不分紅白喜事等各種場合,只要派上用場,喜怒哀樂全由鼓手盡情演繹。金狗先是長槌當歌,引出一陣“開臉”的曲牌,烘托新娘難舍難分娘家的氛圍。
此刻,荷花正坐在閨房“開臉”,嬸子雙手繃住兩股交錯的白線,在她剛撲過粉的臉上,一溜一溜地彈扯著汗毛。婚前少女“開臉”是當地古有的習俗。叫開臉,開了臉,新娘才會真正變成“新人”,才會到婆家“新吉新發”。
“開臉”的鑼鼓點子剛溜進閨房,嬸子的手輕輕一抖,說,咦吔!花兒你說,這金狗真神哩,眼看不見,心卻看得見,硬是曉得你正開臉喲。說著就唱起了《開臉》:開臉開臉,轉換新顏。一開金枝玉葉,二開貴子狀元,三開龍鳳呈祥,四開百事合歡。開臉開臉,開臉大吉,花果團圓……
兩行清淚爬出荷花的眼眶,像兩條蚯蚓掛在粉臉上。
花兒,你么子了?
嬸,我好想哭……
哭吧娃,今日該你哭哩。
外頭的鑼鼓點子,像知道荷花的心思似的,“開臉”一個“鯉魚打挺”煞住,接著,又一記悠槌“孔雀開屏”,“扇”出了“風擺柳”似的《哭嫁》。荷花鼻子一酸,隨了鑼鼓點子,不由哀哀哭號。
嬸子又是驚嘆,哎呀,我說這金狗,神得硬是你肚子里的一條蛔蟲喲!
嬸子不說還好,一說荷花反倒哭得更兇了。嬸子說,娃,誰要你長顆哭痣呢。上唇長顆痣,不是苦,就是哭。姑娘家,橫豎就哭這一回。看來,你不哭醒,是不會住的。嬸子心想,姑娘出嫁這天,都會巴心巴肝地哭的。她也是。娘也是。娘的娘也是。天底下的女人,不都是這樣哭過來得么。
總算是挨到了“發親”的鑼鼓點子響起。荷花也哭醒了哭夠了,就打住哭聲,任嬸子把一頂紅蓋頭,頂在頭上。一世界,就縮到了她的鞋尖子上。
一乘大花轎停在院落。嬸子背著荷花,只消邁過門檻三個步子,就把她顛上了轎。這當兒,主禮人端著裝了茶葉、谷粒的升子,立在轎前,隨了“老鷹散翅”的鑼鼓點子,邊念邊撒:吉星高照,諸煞避讓。男婚女配,長發其祥。米撒佛神前,福祿壽喜全。米撒虛空所,盜賊遠遠躲。平安歸一路,萬事無坎坷……
又是一陣“緊急風”刮過。起轎。四個轎夫閃起丁字步,踩著稠密的鑼鼓點子,顛起大花轎,朝龍馬灣一路晃去。
拐一個之字彎,再下個陡坡,東荊河就被甩在了后頭。一腳邁過去,就是龍馬灣了。送親的隊伍打住步子,等著迎親的過來敬煙。如果迎親的有一絲怠慢,送親的會故意找一些碴子來為難對方。所謂“抬頭嫁姑娘,低頭娶媳婦”,是當地老早就有的舊俗。還好,送親的鑼鼓點子剛一住下,迎親的就以“吆耶嗬”的曲牌還禮致謝。
這時,一輪滿月掛在中天。龍馬湖泛起一湖晶瑩無邊的波光。要想進入龍馬灣,還得走一趟水路。在返回的送親隊伍里,金狗沒有同行,而是加入到了迎親的行列。
金狗真是會做人哩。
是唦,那邊是師父嫁閨女,這邊又是師父娶兒媳。
這叫兩個啞巴睡一頭——好得沒話說。
金狗立在船艙,雙手抱拳,朝挨身司鼓的馬掐神一拱,叔,我替你歇歇。馬掐神一笑,這娃子,幾日不見,禮性越來越大了哩。
金狗只三槌,就牽出了悠悠揚揚的“倒線耙子”。槳聲咿呀,晶瑩的波光,就碎了,碎成了一湖銀。荷花的視線落在船前的湖面上。一對鴛鴦依在波光里,即使“吊鷹掌”的鑼鼓點子砸來,也不棄不離。嫁船平穩而喜慶地在湖面上行走。眼看船挨近了“鴨母坑”,人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鴨母坑是龍馬湖最深的湖窩子,傳說這里有一只鴨母精,每年都要吃掉一個人。“蹚過鴨母坑,過了鬼門關;繞道鴨母坑,一生心不安。”龍馬灣沒有幾個過了鴨母坑的,除了別簍跟苕貨,大都是繞道而行。人們說別簍、苕貨都是“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主,沒有顧忌,膽子大,火焰旺,才能過鴨母坑。也有不信邪的,那年,金狗的爹就是過鴨母坑時被拉下水的,害得金狗娘改嫁,落下金狗一人活造孽。那些繞過鴨母坑的人,總是心有余悸,惶惶不可終日,生怕哪天生災害病。
船,漸漸慢了下來。剪槳的舵手聽著鑼鼓點子,確定行船的方位。金狗的鼓槌忐忑起來,在“蹚”和“繞”之間拿捏、徘徊。如果硬“蹚”過去了,新郎新娘就會吉祥避災;如果“繞”道行之,一對新人只圖得了一時吉祥,圖不了一世安詳。豆大的汗珠子從他的額頭冒了出來。不,不!我要讓荷花一生一世都吉祥安康。一陣巫風旋過。鴨母精!有人驚呼一聲。可是金狗主意已定,一陣“緊急風”的鼓點驟然刮起,一下鎮住了巫風。他一邊擊鼓,一邊念起了《殺鴨》的咒語:鴨子鴨子你不怪,你是人間一碗菜。今日持刀把你宰,變只鳳凰不回來!
啊——!
一個浪頭騰空而起,又狠狠地砸下來。人們看見,那扇起翅膀的鴨母精,被浪頭劈折。只聽得三記硬槌,鼓聲大作,眾人吆喝,船硬是有驚無險地闖過了鴨母坑……
八
鬧洞房時,龍馬灣人又多了一個話題:金狗的神鼓闖過了鴨母坑。人們感慨,有了金狗的神鼓助威,往后再闖鴨母坑就不怕了。這時,就有人提議,讓金狗來司儀婚禮。金狗客氣地推辭說,不敢不敢,還是馬爹來吧。馬爹是馬氏家族的長者,一向是受馬家人尊重的紅白喜的司儀先生。說這話的人自然是背著馬爹的。金狗怕得罪馬爹,就摸到黑角落坐下,靜靜地等著人們鬧洞房。
新婚三天無老少。每每有人結婚,在新婚三天里,鬧洞房是不分男女老少的。越鬧越喜慶,越鬧越吉祥。于是就有人變著法子鬧,鬧得新人越難堪越好。
金狗雖沒司儀過婚禮,但他不少聽過,對鬧洞房的一整套程序,早已在心里默得滾瓜爛熟。那些吉祥如意、詼諧幽默的洞房歌,只要在耳朵里過一遍,就會過耳不忘,牢記在心。在當地,每個灣子都有司儀紅白喜事的先生,但大都是“半個胯子”,要么司儀喪事,要么司儀婚禮。像馬爹司儀紅白喜事的“全胯子”幾乎沒有。金狗何嘗不想成為又紅又白的“全胯子”呢。可是,他不能搶了馬爹的飯碗啊。
新人還沒入洞房呢,洞房里卻擠滿了人。酒味汗味煙味和嗝出來的餿味摻和在一起,快要把天蓋掀翻。洞房內的是想搶占一個有利的位置,好看熱鬧;洞房外的自然不甘心,就拐著肘朝里擠。有人突然捏住鼻子,說,哇——好臭,是哪個雜種放悶屁?
是馬大腦殼放屁。有人邊說邊彎起指頭,在馬大腦殼的頭上敲了一丁棍。
馬大腦殼摸了摸頭說,我承認剛才是放了屁,可是響屁。響屁不臭,臭屁不響唦。
人們轟地大笑后,又開始追查放悶屁的人。
我曉得,悶屁是誰放的。苕貨說。
是哪個?
苕貨說,是新娘子。
人們又笑,你么曉得是新娘子?
苕貨嘿嘿一笑,一本正經地指著新娘說,我、我在她的褲襠里聞到的。
又是一陣更大的轟笑。有的笑岔了氣;有的笑出了眼淚水;有的笑痛了肚子。別簍笑得直翻白眼,轟然倒地……就有人喊,馬爹爹快些救人,別簍,嗆過去了。
馬掐神不僅掐時是個角,掐人中也是把好手。馬掐神慌亂中沒忘他司儀的正事,就對人群喊,金狗吔,搭把手,我得救人哩。就要把一雙筷子和一個竹筒要交給金狗。金狗客氣地推脫,但還是硬被馬掐神塞到了手中。人們一邊起哄一邊直拍巴掌,嚷嚷著要看金狗司儀婚禮。
馬掐神只一掐一擰又帶一揪,別簍“哎呀”大叫一聲,痛還了魂。別簍清楚,馬掐神使了暗勁子,主要表現在那一擰一揪的指法上。狗雜種,舍不得死啊!別簍裝憨,我怎么了?馬掐神氣得又擰了他一把,朝他的耳根子惡狠狠地說,跟老子裝!
別簍雖吃了馬掐神的暗勁子,心里頭卻化開了蜜。誰都不知道,為了讓馬掐神交權,別簍使得是苦肉計,不僅蒙騙了眾人,還蒙騙了馬掐神。當然,馬掐神最終還是“掐”出了他的陰招。真是人不可貌相,狗不可貌樣啊。我馬掐神居然栽在了別簍的手里。好在眾人不知,他馬掐神里子面子也都過得去。
哦,快看金狗開金口啰。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唦。
往后我兒子娶老婆,就要金狗鼓喜司儀。
說這話的都是嫉恨馬掐神的,這回終于找到了報復的機會。
我也是!苕貨踮起腳尖說。人們又轟地大笑。
死苕貨,婆娘都沒得一個,還兒子呢!
別簍“嘎嘎嘎”的笑聲,像母鴨子叫。苕貨從人縫里鉆過去,揪了別簍的耳根子,哼!你狗日的不曉得丑賣幾個錢一斤呢,笑老子!
人家別簍有老婆哩。有人故意挑撥。
是吊著胯子屙尿的。
走起路來搖尾巴的。
別簍的耳根子又被擰了幾下,說,是不是?
別簍的眼淚水都被擰出來了,是是是,反正比你沒有強。
苕貨就忍不住,跟了大伙一起笑。
再不能這樣鬧下去了,得趕緊進入正題。這就要看司儀掌控整個場面的能力了。馬掐神退到一旁,巴望場面越糟越好,一副看戲不怕臺高的陰笑神態。
金狗后背滲出一身冷汗。光腳板子不怕穿鞋的,人都死了還怕進棺材?來就來。于是,他雙腳站上板凳,吆喝了一個悠長的甩腔后,念白道,入洞房——
男歸中堂,女歸繡房,
夫妻偕老,百世其昌。
新娘被新郎背進洞房時,她的目光一直盯著板凳上的那雙繡有并蒂蓮的千層底。
來個拜堂歌。新娘還沒落座,就有人叫:
墻上一蔸草,風吹兩邊倒,
今年過喜事,明年娃兒吵……
金狗剛一唱完,就有人揭了新娘的紅蓋頭,硬把她推到了新郎的挨身。
不過癮。
來刺激的。
就是做那事的。
金狗清楚,人們指的是《筷子插竹筒》。就是新郎新娘對站,新娘雙手掌竹筒,新郎右手掌兩雙筷子,向新娘的竹筒插去,再一人一句進行表演。這表演,說白了,就是象征性生活的開始。
原本并列站著的一對新人,硬被扯成了對站。有人很快把竹筒和筷子分別塞給了新娘新郎。
司儀的,快開始。
金狗一愣,說,只做不唱,行唦?
眾人齊答,不行。
金狗沒轍了。
還是按規矩來。說這話的是馬掐神。老規矩就是,不僅要做,而且還要唱。
金狗知道,馬掐神是想讓他出洋相的同時,也順帶讓一對新人難堪。他只得硬著頭皮引領:
——新郎唱:筷子插筒子。
新郎就邊唱“筷子插筒子”,邊把筷子插進筒子。
——新娘唱:明年生太子。
新娘就邊掌竹筒,邊唱:“明年生太子。”
——新郎唱:如果不生呢?
新郎就唱:“如果不生呢?”
——新娘唱:是你沒得用。
新娘就唱:“是你沒得用。”
——新郎唱:敲我幾筷子。
新郎就唱:“敲我幾筷子。”
人們聽著筷子在新郎的腦殼頂上“嘭嘭嘭”直響,禁不住大笑起來。就在這時,只聽“咣當”一聲,竹筒從新娘手中突然脫落,眼看竹筒就要落地的一剎那,立于一旁的金狗,說是遲,哪是快,居然冷不丁伸出一雙手,穩穩準準地接住了竹筒,也接住了一對新人即將破滅的喜慶和吉祥。
人們不禁暗暗唏噓:嘖嘖,如果竹筒落地,定會摔成兩瓣,新郎就會遭遇絕后之災呀!
唏噓之后,人們又把目光齊刷刷地射到金狗的兩只眼睛上:
咦,金狗咋會接住竹筒呢?
金狗莫非裝瞎?
狗日的金狗真神啊!
金狗拖著虛脫的身子,踉蹌出洞房,只見一道天光劃過,眼前赫然躍出一條明晃晃的道來……
(責任編輯 高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