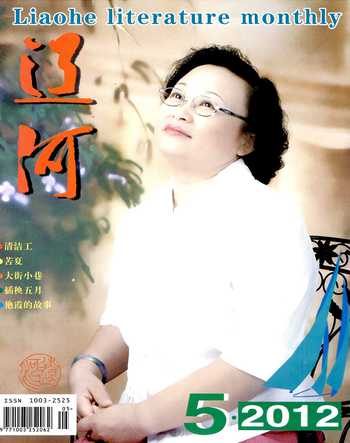我看程默散畫
劉全軍
程默先生“開創散畫論,立派自成體”, 他以豐厚的生活底蘊、獨特的思維視角和不羈的藝術表現,描摹世相百態,展示大千世界,抒寫會意人生。在欣賞程默先生散畫的時候,我的腦際時刻在想一個問題,好像我的視覺里并沒有畫,而是心里在想一幅畫。這是“畫”嗎?當然是畫,是什么畫?散畫。程默先生畫的散畫。什么是散畫?我沒有找到這個概念的解釋,只是感覺到他創作的靈感帶有突發性,“恍惚而來,不思而至”,偶爾得之,俯身拾遺;表現形式是隨意的、拈來的、表層的、淺顯的,朦朧而模糊,渾拙而迷惑,像是捉迷藏猜啞謎。
我不敢稱自己是個藝術欣賞者,我只是怡情看畫的過路客,因為藝術欣賞是一種精神享受,欣賞者進行的是“二度創造”,所以要求欣賞者具備一定的生活閱歷和藝術修養,這兩方面說我具備也不具備,因為我到現在也沒看懂一片樹葉是怎么飄落到樹下的,是因為風嗎?不是,一日問一個正在酣玩的小孩,小孩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它不掉,樹還會綠嗎?”我愣在那里。
看程默先生散畫是要用心看的——看什么東西都是要用心看的,反復看幾遍,味道就出來了,意蘊就發散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后的“頓悟”是這樣描述的:如果讓一個從沒畫過東西的人來畫一只貓,他會盡力發揮把這只貓畫的越像越好,他也可能畫的酷似貓,但他畫出的只是一只貓而已,因為他在畫貓的時候心里只尋思著把貓畫的像模像樣,而沒去想為什么要畫這只貓。看程默先生散畫的時候,我也聯想起了賈平凹的畫,你敢說賈先生的畫“丑”嗎?丑到了極點就是美到了極點,這是賈先生在《丑石》這篇散文里說的。我時常在想,那些刻在龜甲、獸甲上的“契文”,那些鑄在青銅器上的“獵碣”,那些隨勢屈曲的瓦當文,哪里是字,而是畫,到底是先有字還是先有畫,我認為先有畫,有了畫字后才有字畫。有了這點啟發后,我才意識到,散畫的“看似尋常卻崎嶇”了。
我把眼光停留在程默先生的四幅散畫上:《名為霸王蕉,無花也無蕉》、《樹人》、《吃長面講短話》、《看檳榔》。霸王蕉我沒見過,也沒吃過,還是從他這幅畫得知世上還有這種熱帶果樹,從霸道的名字看,估計價格不菲。畫面是兩片碩壯的葉子,且不說這幅畫的形式和技巧——如果看散畫只偏于形式和技巧,建議最好去牡丹廳看牡丹。不看樹枝桿,僅就看兩片霸王蕉葉,你會聯想到人和事的是非虛實,這樣的人這樣的事每個人都會遇見,也都會碰見,也許這樣的人和事就發生在身邊。《樹人》更有意思,一棵粗實的樹上露出一張人臉,幽默而喻諷,育人樹人,人和樹融為一體。《吃長面講短話》告訴人們,吃進肚子里的東西越多,吐出來的話卻不要是廢話。《看檳榔》是從唱“香檳”開始的,一男一女幾乎是后傾斜著身體斐然的仰望著樹上檳榔,卻心里想著當年采下的檳榔是送給哪位女子的,當年含在嘴里甜蜜的檳榔是哪位男子爬向高高的樹上為她采摘的。檳榔不是情物,站在檳榔樹下唱著甜蜜的歌相守一生的男女又有幾何?
任何一種理論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在充分繼承前人理論遺產基礎上創造出來的,將不斷吸取其他的一些理論成果中的精華,并隨著文藝實踐的發展不斷予以充實更新。散畫理論要形成一個文藝流派,是要有一個有機聯體的藝術家群體來結集,他們的思想傾向、藝術觀念和創作實踐需具備一直性或相似性。流派沒有藝術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藝術家作品的數量和質量,所以散畫理論真正成為一種藝術流派,還需要源于自然,根植生活,在創作實踐中不斷繼承、創新和發展。
(責任編輯:孫玉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