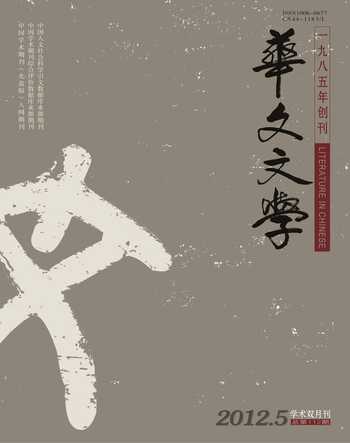“俠”中乾坤大:金庸小說主題再認識
劉忠
摘要:千古文人俠客夢,凡人與俠客、現實與理想、自由與羈絆的對立,讓武俠小說保留了一份“對抗存在的被遺忘”的功能,金庸小說注重武俠內在精神的提升,不僅呈現了一個想象的武林世界,也描繪了一個豐饒的人性世界。“俠”中乾坤不再是忠君報國、冤冤相報的傳統主題,而是人的個體存在和精神自由度。金庸小說已經超出雅俗二分的傳統規限,走向了自在和自覺。
關鍵詞:金庸小說;主題;俠客;乾坤;自由
中圖分類號:I0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677(2012)5-0112-05
求神拜佛,做個長生不老的神仙,這是我們先人樸素而不乏迷信的理想,后來,人們發現,修仙得道不過是人類的一廂情愿而已,根本無法實現;相反,做個仗義守信、古道熱腸的俠客,卻是可行而且可能的,畢竟,神仙離我們太過遙遠,而俠客就在我們中間,且近且親,武功蓋世、濟民衛國者本身就是,市井百姓、文人墨客亦可以做一做“俠客夢”,把自己想象成為一個情重似海、義薄云天的江湖俠士,擺脫塵世的種種羈絆和紛擾,進而獲得一種身份認同感。今天,許多學者把武俠小說稱為“成年人的童話”,我想,也包含著這層意思。
一、“俠”中乾坤大
作為中國文學的一種原型,“俠”之想象源遠流長,從最初游離于正統社會體制和規范之外的俠士到現代人為擺脫生存困境和身份焦慮而做的俠客夢;從韓非子筆下的“俠以武亂法”到金庸筆下“為國為民,俠之大義”,我們看到,俠客身上承載了太多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操守。俠中乾坤大,壺中日月長,千古文人俠客夢,一個“俠”字,表達了人們對公平、正義的呼喚與堅守;一個“壺”字,裝載了多少文人的愁腸與抱負。追問、反思……人類自我認同的腳步一天不停歇,俠客夢就一天不會中斷。凡人夢想成為俠客,擁有改天換地的偉力,鏟除邪惡;而俠客呢?功成身退,了卻江湖恩怨,做個普通人,幾乎是俠客的普遍愿望。凡人與俠客、現實與理想、自由與羈絆的對立,讓武俠小說保留了一份“對抗存在的被遺忘”的功能①。
人們常說,江湖險惡,既如此,何以還要執著地做俠客?俠客不事生產,以劫貧濟富、伸張正義為安身立命的根本,他們的特征之一就是流動性,陳平原指出,“驅使俠客上路,是游俠傳奇得以展開的一個基本前提”②。游動不居的處所、遠離政治的江湖身份、持守如一的道義,都賦予俠客們較大的人格獨立空間。試想,在等級制森嚴的社會里,擁有個體人格空間該是多么彌足珍貴!何況在俠客身上,人們看到了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可能。這一點,在金庸為代表的新派武俠小說中表現尤為明顯。江湖是俠客們的表演舞臺,俠客的信條就是江湖的規則。鏢局、商賈、豪杰等俠客之外的江湖人士雖然各有所屬階層或行業的行為規則,但在整個江湖體系中,遵循著大體相同的行為規則。“俠之大者,義也”。猶如一條潛在的律令,不僅被俠客們奉為高標,也讓普通百姓神往不已。《笑傲江湖》的田伯光“采花”無數,罪大惡極,名門正派之人即使沒有見過他的面,也想將他碎尸萬段,連定閑大師這樣以慈善為懷的出家人也不原諒他,不給他改惡從善的機會。后來,田伯光被假和尚不或強迫收為徒弟,遭遇閹割,喪失了采花能力。之所以如此結構故事,我認為,是江湖道義使然。
俠首重節義,這雖然是人們出于道德立場的價值判斷,但它卻是人類社會普適的價值觀念,并在歷史的長河中不斷強化。唐人李德裕在《豪俠論》中說:“夫俠者,蓋非常人也。雖然以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李衛公外集》卷二)“俠”與“義”的同構關系,金庸也是認同的。他說:“武俠小說,一方面形式跟中國古典章回小說類似,第二它寫的是中國社會,更重要的,它的價值觀念,在傳統上能讓中國人接受,是非善惡的觀念,中國幾千年基本沒有很大的改變。”③作為一種道德規范,“義”在武俠世界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違背義,人皆恨之;奉行義,人皆仰之。令狐沖以少年之身化解江湖危難,扶弱濟貧,成為武林的“在野之王”,并不是他的武功高強到萬眾歸順,而是道德力量在發生作用。
應當說,在以“武”為表征,以“俠”為內核上,金庸小說與其他新派武俠小說并無二致,急人之難、千金一諾、扶貧濟困、除暴安良、伸張正義等俠義風范在小說中皆有表現,不同之處在于,金庸小說注重武俠內在精神的提升,尤其是人的個體存在和精神自由度,對忠君報國、冤冤相報等傳統武俠小說主題做了創造性轉化,人性、人道主題開始顯現。用金庸自己的話說,就是“武俠小說本來是娛樂性的東西,但是我希望它多少有一點人生哲理或個人的思想,通過小說可以表現一些自己對社會的看法”④。“我寫小說,旨在刻畫個性,書寫人性中的喜愁悲歡。小說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責,那是人性中卑污陰暗的品質,政治觀點、社會上的流行理念時時變遷,人性卻變動極少。”⑤從金庸小說題目聯綴而成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來看,他的小說做到了這一點。
在他的小說中,我們能夠解讀到兩個密切相關的文本——“人界”與“武界”,人界的凡人、俗人遵循的是人的一般規則,而武界的奇人、俠客遵循的則是俠的特殊規則,兩者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凡人俠客夢難圓,俠客還俗愿未了。困擾他們的不僅有人性的種種弱點,還有社會強加給他們的各種積習,各種欲望的膨脹、權力話語的介入、冤冤相報的循環、勢利小人的挑撥……常常令俠客們愁腸百結。面對物欲、權欲、情欲……的引誘,縱然是武林教主,也難以避免。好在金庸小說在對世俗生活藝術轉化中,大量地運用愛情、親情、友情等美好的東西進行燭照,盡可能過濾武俠小說固有的邪惡、仇殺因子,剝離出人性的閃光面和詩意性,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人間情懷始終流淌在文本深處。棄絕、否定之聲引導著俠客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躍出“苦海”,逃逸“武界”,進入到一個澄明與敞亮的詩意境界。《書劍恩仇錄》開篇就塑造了一個“小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大隱隱于野”的人物形象陸菲青,小說結尾,“紅花會”群雄在“復明”大業未成、反清殺乾隆的愿望落空的情形下,相繼“豹隱回疆”。同樣,《碧血劍》中的主人公袁承志,開始時滿腔熱血,把建功立業作為人生的第一目的加以追尋,結果也走上了一條歸隱的道路,“空負安邦志,遂吟去國行”。《神雕俠侶》中的楊過和小龍女、《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連城訣》中的狄云、《越女劍》中的阿青、《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天龍八部》中的虛竹、段譽等人,也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歸隱山林或離疆去國的道路。
“歸隱意愿”使俠客與世俗生活保持了一定距離,從中脫身出來,獲得一種暫時的虛清和淡泊。單獨來看,“歸隱”意味著一種退守、一種被動解脫,但誰又能否認其中內蘊的人性的溫柔部分!它可以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自曠,道家“且自逍遙無人管”的自然,也可以是佛家“回到內心”的修身,……包含太多太多的人生寓意。如果說歸隱意愿是一個尚不規范的批評術語,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指出它的本質所在就是俠之追求的自由境界。綜觀金庸小說,我們看到這樣一個“俠”之系列,從陳家洛、袁承志到楊過、張無忌,從段譽、虛竹到令狐沖、石破天,他們往來穿梭于“人界”與“武界”之間,無不在展開對生命自由的追求,希望藉此消泯世間的一切恩怨殺伐,讓生活獲得一種本有的安適,讓生命返歸一種自然的狀態。在他們的人生中,我們感觸最深的不是多難興邦的豪言壯語,也不是一統武林的美好愿景,而是對生命自由的如一追求。
二、“俠”之自由精神
金庸小說中,“俠”之自由精神具有多種表現,它是一種生存方式,也是一種小說敘事方式;它是一種情感意緒,也是一種引導圖式;它是一種個體存在的極致,也是一種自我人格的維護;它重建了存在,也超越了存在。
首先,俠之自由精神具有消解庸常生活的功能。如前所述,金庸小說在演繹正邪對抗、群雄爭霸、快意恩仇故事時,目的并不是把玩丑惡、兇殺、權術,而是欲使“一個描寫對象從其通常的感知領域轉移到一個新的感知領域,形成某種語義變化”⑥。從文化規范、道德倫理、人性深度等方面進行審視,擺脫庸常生活規限,沉思人的生存境界。這里,俠之自由精神不僅消解了世俗生活的丑惡、兇殘,而且還使主人公獲得自省的激情與動力,把“自我”作為一種“他者”加以觀照。《笑傲江湖》中,金庸通過一系列權力爭斗場面顯現權力對人性的扭曲作用,好人一旦走到權力的重要位置,也有可能腐化墮落,任我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起初,他堅決反對東方不敗搞個人迷信,但當他登上教主寶座之后,思想立刻發生變化,“又覺得東方不敗定下的這套規矩也挺有意思的”。這里雖然寫的是人性的弱點,但卻形象化地提出了一個權力缺乏監督滋生腐敗的社會問題。
其次,俠之自由精神具有自我閱讀功能。金庸小說武打場面描寫氣勢恢弘,各派武功招式自成一體,想象力之豐富非一般人所能及,主要人物對武功的演練、習得潛在地對應著他們對人生諸般境界的閱讀、提升。與所有的武俠小說家一樣,金庸也描寫武功從平庸到神奇,直至不可思議的過程,但他并不一味地推崇武力、蠻力,而是講求以內制外、以柔克剛、以靜制動。交戰雙方,在進入相持階段之后,生死大限往往維系在正邪一念之上。鐵砂掌、毒砂拳固然凌厲有加,但精湛的內功能夠輕而易舉地使之銷于無形;即使是博大精深的全真劍法,如果沒有內功配合,也只能是徒有虛名,不能用來護身報國。如此內功何以習得?關鍵一點即在人生閱歷。從小說中看,只有那些經歷人生磨難,閱盡人事紛爭之人,方能在刻苦演練中習得。這一點上,它與宋儒朱熹倡導的“心到”重于“眼到”和“手到”的讀書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于一個“俠者”而言,武功非凡是必備的條件,《射雕英雄傳》中生性遲鈍的郭靖靠降龍十八掌獨步天下,黃蓉的打狗棒法青出于藍勝于藍;《笑傲江湖》中令狐沖的獨狐九劍更加是使得出神入化;《神雕俠侶》中楊過算是武功學得最多的,打狗棒法、彈指神功、蛤蟆功、九陰真經、默然銷魂掌……不過,僅有高超的武藝還不夠,還要有一顆能夠閱讀世人的“仁愛之心”,對父母要孝,對兄弟姐妹要親,對國家要忠,對自己要嚴。武德上者,俠士也。郭靖,以一介平民之身,“鐵肩擔道義”,死守襄陽十數載,最后以身殉國。蕭峰,處在宋遼對峙的夾縫中,面對大宋百姓的災難,義字當先,以死弭兵。武功與修身對應關系十分明顯。
最后,俠之自由精神具有言說與對話功能。作為人類相互溝通與交流的方式,言說與對話本身就是自由,雅斯貝爾斯說它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實現”⑦;巴赫金認為“人類的本性在于對話,無論是在自我與自我之間、自我與其他之間,還是在自我與世界之間”⑧。金庸小說在人物設置和塑造上,體現了這種對話與言說功能,不僅人物之間形成對比和反差,即使是同一類人物身上,也要凸顯他們各自的品行,追求復調相和的效果。家庭連遭變故的謝遜自述說:“我生平最崇仰、最敬愛的一個人(謝遜的師傅成昆)欺辱了我,害得我家破人亡,父母妻兒一夕之間盡數死去。因此我斷指立誓,姓謝的有生之日,絕不再相信任何一個人。”為了逼迫成昆露面,謝遜不計后果,殺人如麻。然而,當張無忌的出生的啼哭聲傳來時,他的仁愛之心復生,開始懺悔所犯的一系列罪過。戀愛一再遇挫、失敗的李莫愁,因為心愛的男人背叛了自己,就憤而殺死情敵一家,成為嗜血女魔,但當手捧嬰兒郭襄時,母性覺醒,用平時用來殺人的浮塵為她驅趕蚊子。她在凄婉的“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許”的歌聲中出場,又在元好問的這首詞中死去,終未參悟“情為何物”的真意。
三、“俠”之雅俗之別
金庸小說已經為人們所熟知,關于他的小說價值,學者們也給予了高度評價,嚴家炎說:“金庸小說雖然用幾百年前的歷史做背景,卻滲透著真正的現代意識;既有反對封建專制的民主思想,也有反對民族壓迫的平等觀念;既有樸素的階級意識,也有弗洛伊德、榮格以來的現代心理學知識;還有現代的悲劇觀念、喜劇觀念以及《鹿鼎記》所代表的先鋒意識,金庸小說深烙著鮮明的時代印記,是20世紀中西文化交匯時代的產物。”⑨現代意識、民主思想、平等觀念、先鋒意識、中西文化交匯等評語不僅道出了金庸小說深廣的內涵,也揭示了金庸小說為人們廣泛接受和反復闡釋的內在動因。但是,受傳統積習影響,人們一直把武俠小說歸屬于通俗文學門下,斥其品位不高,宣揚綠林精神,難登大雅之堂。對此,金庸也坦誠地說:“武俠小說雖然出現的時間不短,但寫得比較好的卻還是近代的事,從前的武俠作品雖然多,但佳作卻很少見。”“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最初發展的時候,都是很粗糙的。……忽然之間,有幾個大才子出來了,就把這本來很粗糙的形式、大家都看不起的形式提高了。假如武俠小說在將來五六十年之間,忽然有一兩個才子出來,把它的地位提高些,這當然也有可能”⑩。除了缺少精品佳作,金庸還認為,武俠小說的冷遇還與政治、傳統因素有關,“政治、傳統因素甚于藝術因素”,歷史地看,貶低武俠小說的“都是大知識分子,他們在政治上有地位或影響力,而且整個中國文壇主要也是由這些人組成的”?輥?輯?訛。與缺少精品佳作相比,政治、傳統的因素才是造成武俠小說地位低下的主要原因。精品佳作的出現可以期待,改變傳統不僅要假以時日,還需要思想觀念的轉變,難度可想而知。不過,金庸就是金庸,有著超出常人的思維與識見,他轉而跳出雅俗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一個更為寬泛、深廣的時空背景下來討論武俠小說的屬性和格調。他認為,不管是俗文學還是雅文學,不管是武俠,還是愛情,抑或是偵探,只要是文學,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好的文學永遠是表現世道人心的。武俠、偵探、愛情……不過是它們的表現形式而已。“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跟它用什么形式來表現完全沒有什么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他任何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武俠小說也和其他文學作品一樣,有好的,也有不少壞的作品。我們不能很籠統地、一概而論地說武俠小說好還是不好,或是說愛情小說好還是不好,只能說某作者的某一部小說寫得好不好……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和它是不是武俠小說沒有關系”?輥?輰?訛。
2002年新版的《金庸作品集》序言中,金庸又一次重申了上述觀點,認為“武俠小說只是表現人情的一種特定形式。作曲家或演奏家要表現一種情緒,用鋼琴、小提琴、交響樂或歌唱的形式都可以,畫家可以選擇油畫、水彩、水墨或版畫的形式。問題不在于采取什么形式,而是表現的手法好不好,能不能和讀者、聽者、觀賞者的心靈相溝通,能不能使他的心靈產生共鳴。小說是藝術形式之一,有好的藝術,也有不好的藝術”?輥?輱?訛。這里,金庸雖然談論的是小說的類型學意義,但用在他的小說創作上也是十分熨貼的。金庸小說描繪的五彩斑斕的江湖世界是一個以世俗社會為參照、融合了許多理想與現實因素的虛擬世界,它一方面為俠客提供了施展拳腳、恪守教義的廣闊背景,另一方面也為他們的人生走向設置了諸多必要準則,尤其是人性的良善、道義的深重、情感的真摯、精神的自由。一定意義上說,金庸小說中人的性格和情感因素比社會意義具有更大的重要性。金庸說:“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句話在今日仍有重大的社會意義,但我深信將來國家的界限一定會消失,那時候‘愛國、‘抗敵等等觀念就沒有社會意義了。然而父母子女兄弟間的親情、純真的友誼、正義感、仁善、樂于助人、為社會獻身等等感情與品德,相信今后還是長期為人們所贊美,這似乎不是任何政治理論、經濟制度、社會改革、宗教信仰所能代替的。”?輥?輲?訛金庸小說之所以能為廣大中外讀者所喜愛,這一點恐怕是最主要的,畢竟人性、人情才是文學的本質要素。
金庸一生具有多重角色,他不僅用筆名金庸寫小說,還用筆名林歡寫電影劇本,以本名查良鏞寫社論,集小說家、報社總編、學者、社會活動家于一身。在他的人生經歷和性格中,我們看到了他筆下人物的影子,陳家洛的儒雅、郭靖的樸拙、楊過的激情、蕭峰的豪邁、令狐沖的機智、韋小寶的靈活……古人論文說,“文品即人品”,用在金庸身上,同樣合適。作為一種文學表現形式,武俠小說雖然“主要是幻想的,一般人的生活不會這么緊張和驚險”,但在表現和揭示人類情感與人性、人道這一根本點上,它與其他文學樣式沒有什么不同,激烈沖突的情節、美丑互顯的幻想世界既是武俠小說的屬性使然,也是彰顯人性的復雜性和易變性的需要。因為沖突的集中和強化,必然使人物經常面臨生死、名利、權欲、恩仇等極端化境地,人性、人情主題藉此可以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在《韋小寶這小家伙》一文中,金庸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武俠小說中的人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惻隱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于正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于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直報怨,是出于是非之心”?輥?輳?訛。應當說,金庸小說不僅為我們呈現一個想象的武林世界,也描繪了一個豐饒的人性世界,他的小說已經超出了雅俗二分的傳統規限,走向了自在和自覺。
注釋:
① [捷]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44頁。
②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頁。
③ 金庸:《中國歷史大勢》,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頁。
④ 王力行:《新辟文學一戶牖》,《諸子百家看金庸》(五),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年版。
⑤ 金庸、池田大作:《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金庸、池田大作對話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頁。
⑥ [荷]佛克馬·易布斯:《20世紀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53頁。
⑦ [德]雅斯貝爾斯:《什么是教育》,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2頁。
⑧ 董小英:《再登巴比倫塔——巴赫金與對話理論》,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7頁。
⑨ 嚴家炎:《金庸小說論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頁。
⑩?輥?輯?訛?輥?輰?訛 費勇、鐘曉毅:《金庸傳奇》,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頁,第310頁,第125頁。
?輥?輱?訛 金庸:《書劍恩仇錄·新序》,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輥?輲?訛 金庸:《神雕俠侶·后記》,花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1頁。
?輥?輳?訛 金庸:《韋小寶這小家伙》,《明報月刊》1981年10月號。
(責任編輯:黃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