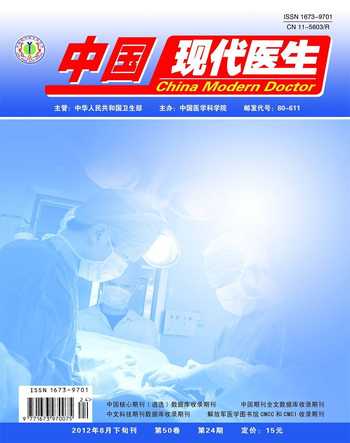我院臨床藥師參與感染性疾病會診調查
宋錦
[摘要] 目的 總結臨床藥師參與臨床感染性疾病會診對合理應用抗生素的作用及效果。 方法 2010年1月~2011年12月我院臨床藥師參與臨床感染疾病會診共112例次,對會診申請的目的、患者臨床資料、會診結果等進行分析。結果 要求會診的患者以肺部感染最為多見。85.7%的患者使用抗生素超過7d,67.0%的患者存在聯合使用抗生素情況,48.2%的患者存在多重耐藥。會診申請科室以ICU會診的例次最多。會診要求目的以抗生素的選擇最多。41.9%全部采納會診意見,采納組與未采納組抗感染療效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結論 臨床藥師參與感染性疾病的會診,能夠提高抗感染的療效。
[關鍵詞] 抗生素;合理應用;臨床藥師;感染性疾病
[中圖分類號] R95[文獻標識碼] B[文章編號] 1673—9701(2012)24—0123—02
隨著醫藥行業的發展,臨床合理化用藥的問題越來越突出,尤其是對感染的患者,隨著抗生素濫用、耐藥菌株情況的不斷增多,抗生素的合理應用成為臨床比較突出的問題[1]。臨床藥師參與感染患者的會診,對合理用藥提出自己的意見,協助臨床醫生正確使用抗生素,達到最好的療效成為臨床藥師的工作范圍之一。2010年1月~2011年12月,我院臨床藥師共參與臨床感染患者會診112例次,本文就會診的目的、患者臨床資料、會診結果等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為臨床藥師會診提供一些參考。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2010年1月~2011年12月我院臨床醫師共參與臨床感染病例會診112例次。其中0~14歲7例次,15~20歲3例次,21~50歲22例次,51~60歲31例次,>60歲49例次。所有患者均有完整臨床資料。
1.2 方法
對所有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統計分析,對會診邀請目的、會診內容、會診建議、會診后治療效果及患者臨床特點等資料進行分析總結。將意見完全采納和部分采納的病例設為采納組,與未采納的病例(未采納組)比較抗感染療效。
1.3感染療效評價標準[2]
根據臨床經驗及抗生素停藥指標制定感染療效評價標準。痊愈:體溫恢復正常>3d,復查血常規正常,原有的感染癥狀和體征消失,血培養無細菌生長;好轉:體溫下降,復查血常規較前好轉,原有感染癥狀或體征好轉,血培養仍有原致病細菌生長;未愈:未達到以上指標。
1.4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6.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需要會診患者感染部位及臨床特點
見表1。以肺部感染最為多見。85.7%的患者使用抗生素超過7 d,67.0%的患者存在聯合使用抗生素情況,48.2%的患者存在多重耐藥。
2.2 會診科室
見表2。ICU會診的例次最多,其次為呼吸內科、血液科。
2.3 會診邀請目的
見表3。會診要求目的以抗生素的選擇最多,其次為抗生素給藥劑量和途徑的選擇,是否加用抗真菌藥物最少。
2.5 會診后治療效果
采納組與未采納組抗感染療效比較見表5。
3 討論
2002年我國頒布了《醫療機構藥事管理暫行規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臨床藥師制度,隨后開展了臨床藥師培訓工作[2]。臨床藥師參與臨床查房、會診,其目的是為臨床醫生提供全面的、與藥物治療有關的技術支持,能夠為臨床制定個體化最佳治療方案提供意見[3]。近年來,我國醫療衛生行業存在濫用抗生素的情況,尤其是對于老年患者、多系統疾病的患者導致了大量耐藥菌的產生,使臨床上抗感染治療效果較差。因此,臨床藥師作為醫療治療團隊成員參與臨床感染患者會診,提出用藥建議,制定個體化的治療方案就顯得尤為重要。趙振寰等[4]對臨床藥師參與抗菌藥物分級管理的效果進行了分析,認為臨床藥師參與抗菌藥物的分級管理,能夠明顯提高抗菌藥物使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延緩耐藥菌的產生。趙俊等[5]對臨床藥師參與“特殊使用”抗菌藥物臨床會診進行了討論,認為臨床藥師參與會診有利于加強醫院對抗菌藥物使用的監管,有利于加強“特殊”抗菌藥物的合理使用,減少耐藥病例的發生。
本文對我院臨床藥師參與的感染患者的會診進行了統計分析,對病例的臨床特點、會診目的、會診結果等進行總結。我院臨床藥師參與臨床感染會診具有以下特點。從年齡分布上看,>50歲的患者最多,其中>60歲的患者49例,占43.8%,說明高齡患者抗感染治療療效較差,這與其存在多系統疾病、多合并肝腎功能下降有一定的關系。在感染部位的分布上,肺部感染最多,結合患者年齡分布及科室分布,可以發現,ICU和呼吸內科的患者最多,老年患者生病后多需臥床休息,咳嗽反射下降,導致墜積性肺炎,常易合并肺部感染,且老年患者老慢支的患者占有一定比例,秋冬季節,呼吸內科以老年患者老慢支合并急性感染為主。ICU的患者病情多較重,常需要氣管插管,也是肺部感染的高發科室,且因為病情較重,抗感染治療效果一般較差。本組85.7%的患者抗生素使用超過7 d,效果較差,67.0%的患者聯合使用抗生素,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耐藥菌株較多,抗感染效果較差的現象。多重耐藥的情況較為明顯,達48.2%,說明臨床上耐藥情況較明顯,尤其是治療效果差的患者。因此會診的目的多以選擇抗生素為主,其次是抗生素的劑量、給藥途徑,這與患者主要是中老年及ICU的重癥患者存在多系統疾病、肝腎功能不全有關。本文對會診意見完全采納與部分采納的患者治療結果進行統計,并與未采納的患者的治療結果進行統計,抗感染治療的總有效率有統計學意義,說明臨床藥師參與感染患者的治療,通過自身的專業知識,為臨床醫師制定個體化抗感染治療,具有較好的效果。
綜上所述,臨床藥師在藥物治療上的獨特優勢及自身的專業知識技能,參與臨床的治療,為臨床合理用藥、減少并發癥、改善療效起到一定作用。臨床抗生素的濫用及耐藥菌株的不斷增多,使臨床藥師進入臨床,協助臨床醫生合理使用抗生素,提高臨床療效變得越來越迫切。而臨床藥師參與感染患者的會診是一種有效的方法,能夠為臨床醫生提供個體化的治療方案,提高臨床療效。
[參考文獻]
[1]張慧明,彭梅,潘曉珍. 我院臨床藥師干預抗菌藥物臨床應用的效果分析[J]. 實用臨床醫學,2011,12(8):9—11.
[2]丁香,曹文麗,張應輝. 臨床藥師開展藥學服務的實踐與體會[J]. 臨床醫學工程,2012,19(2):307—308.
[3]張曦. 臨床藥師在臨床藥學工作中的作用[J]. 中國中醫藥咨訊,2011,3(22):188.
[4]趙振寰,荊偉麗,孫術紅,等. 我院臨床藥師參與抗菌藥物分級管理效果分析[J]. 中國執業藥師,2012,9(2):35—37,47.
[5]趙俊,姚文,孫偉偉,等. 臨床藥師參與“特殊使用”抗菌藥物臨床會診的體會[J]. 中國執業藥師,2012,9(2):31—34.
(收稿日期:2012—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