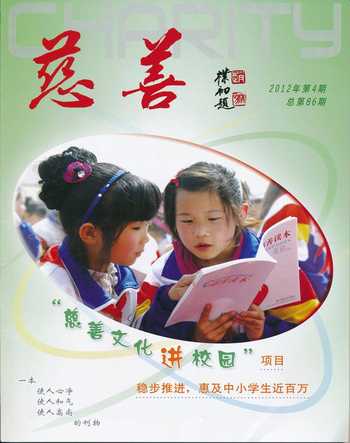我國慈善事業(yè)的國際交流
陸鏡生
我國慈善事業(yè)在國內(nèi)快速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走出國門,加強(qiáng)同世界各國、各民族的交流。我們愈來愈意識到,世界上許多民族的慈善理念同各自的文化密不可分,而他們的文化中深層部分往往是這些民族的宗教思想,比如美國,直截了當(dāng)?shù)胤Q自己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而貫穿于他們慈善事業(yè)中的慈善理念,則多源自他們的宗教經(jīng)典,有著他們的傳統(tǒng)宗教文化的底蘊(yùn)。因此,我們要在慈善事業(yè)方面增進(jìn)同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很自然地需要從慈善事業(yè)角度,乃至更廣的角度同他們進(jìn)行宗教對話,以便找到一條有效的相互合作的路。這就要求我們學(xué)習(xí)和熟悉各民族的文化經(jīng)典和宗教經(jīng)典,而非依靠道聽途說,從而對他們的慈善理念和慈善事業(yè)的活動方式等有一種不帶偏見和更準(zhǔn)確客觀的認(rèn)識和理解。這是慈善事業(yè)廣泛的、健康的國際交流的前提。我們努力以“和而不同”的態(tài)度,求同存異,樹立以“仁慈”、“博愛”為基礎(chǔ)的平等相待意識,不斷推進(jìn)慈善事業(yè)國際交流的進(jìn)程。
在我國,不少人對宗教有著很大的誤解,比如,以為儒釋道是三家宗教。其實(shí),我們查中文大辭典就知道,“宗”是重要的、主要的、尊崇的意思;“教”是教育。在我國,本土意義上的“宗教”是指重要的教育、主要的教育、值得尊崇的教育。儒釋道就是我國傳統(tǒng)上的這樣的教育,都是無神論。有神論的“宗教”一詞是舶來品,各個(gè)宗教都是信仰各自的一個(gè)“真神”。因?yàn)轳R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于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禁止宗教活動和迫害宗教信徒。我國在中國共產(chǎn)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路線以后,糾正了“文化大革命”時(shí)期的極左做法,重新落實(shí)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學(xué)術(shù)界也圍繞馬克思關(guān)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這一論斷進(jìn)行了討論,認(rèn)為,不應(yīng)將馬克思的這句話理解為其主要觀點(diǎn),也不應(yīng)理解為對宗教的絕對否定,并指出,在馬克思之前,西方已有不少宗教人士曾用“鴉片”比喻宗教。當(dāng)時(shí)歐洲人民把鴉片視為鎮(zhèn)痛治療良藥。這同經(jīng)過“鴉片戰(zhàn)爭”的中國人對鴉片的厭惡態(tài)度是不同的。愈來愈多的學(xué)者擺脫了對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的片面和教條的理解。在20世紀(jì)80年代后期,學(xué)術(shù)界進(jìn)而通過學(xué)術(shù)討論,對“宗教是文化”達(dá)成共識。一個(gè)民族的宗教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而且構(gòu)成了民族文化的內(nèi)在精神。自此,我國人民愈來愈多地能夠?qū)ν鈬诵叛龅乃麄兠褡宓淖诮逃辛似毡榈睦斫夂妥鹬兀慌c其同時(shí),也把我國的儒釋道看作是孔孟的教育、佛陀的教育、老莊的教育。比如,我國的香港等地信仰佛陀的民間團(tuán)體稱“香港佛陀教育協(xié)會”等而不稱佛教協(xié)會;稱修學(xué)佛家凈土法門的民間團(tuán)體為“凈宗學(xué)會”,等等,明確地表達(dá)了佛教的教育職能和非宗教的特點(diǎn)。我國現(xiàn)今除了非宗教的儒釋道的民間教育團(tuán)體外,也有信仰基督教等的民間宗教團(tuán)體。我國現(xiàn)行憲法第36條第一款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第36條第二款又進(jìn)一步具體規(guī)定:任何國家機(jī)關(guān)、社會團(tuán)體均“不得強(qiáng)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三款還規(guī)定“國家保護(hù)正常的宗教活動”。另一方面,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jìn)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害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tuán)體和宗教事務(wù)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世界各國大多在憲法上規(guī)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或信仰自由(信仰是更廣泛的概念,包括宗教信仰)。但同樣也規(guī)定,非正常的宗教信仰不受保護(hù),如借宗教之名進(jìn)行反國家、反社會的活動。
我們讀閱各民族的宗教經(jīng)典,會感到,每一個(gè)民族的宗教都有一個(gè)價(jià)值系統(tǒng)。各宗教的經(jīng)典明確地為人類規(guī)定了普遍的道德慈善價(jià)值。比如基督教的新教(基督教是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統(tǒng)稱,包括天主教、東正教、新教等。公元1世紀(jì),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1054年,東、西教會大分裂,東部自稱正教,即東正教;西部自稱公教,即天主教。16世紀(jì)時(shí),西部教會分裂,脫離天主教會的一些新教派稱為“新教”。)的圣經(jīng)中的《加拉太書》中圣保羅向加拉太人說:“至于圣靈所結(jié)的果子就是:博愛、喜樂、和平、忍耐、仁慈、善良、忠信、溫柔、節(jié)制。這些事是沒有法律加以禁止的。”天主教圣經(jīng)中的《哥羅森書》講:“你們該如天主所揀選的、所愛的圣者,有憐憫的心腸、仁慈、謙卑、良善和含忍。”印度教的經(jīng)典《商枳略奧義書》規(guī)定:“不害、不盜、貞行、仁慈、平正、容忍、堅(jiān)定、節(jié)食與清潔,此持戒十。”印度教的《舍得奧義書》規(guī)定:“不害、真實(shí)語、不盜、不荒淫、身外無長物、無瞋、敬師尊、純潔、知止足、正直端心行。”印度教的《攝句義法論》規(guī)定:“信法、不傷害、仁慈、誠實(shí)、擺脫不正當(dāng)?shù)恼加杏⒉灰艋瘎訖C(jī)、不瞋。”
各民族宗教不僅對其價(jià)值系統(tǒng)作了概括性表述,而且有許多關(guān)于慈善理念以及倫理、道德、因果等具體、豐富的教誡,啟發(fā)信教者和不信教者在生活上做有道德的人、有博愛情懷的人、深信因果善惡報(bào)應(yīng)的人、有高尚情操的人,從而大家互愛互助、平等相待、和睦相處,使地球成為所有民族共同的快樂家園。我們是從事慈善工作的,讓我們先領(lǐng)略一下各民族宗教關(guān)于慈善理念的教誡。這里引述的可能掛一漏萬。天主教圣經(jīng)的《若望福音》講:“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你們,你也該照樣彼此相愛。”“假如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們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的。因?yàn)槟遣粣圩约核匆姷牡苄郑筒荒軔圩约嚎床灰姷奶熘鳌!薄皯?yīng)與喜樂的人一同喜樂,與哭泣的人一同哭泣。”《格林多前書》講,“我若沒有愛,我什么也不算。”“愛是含忍的,愛是慈祥的,愛不嫉妒,不夸張,不自大,不作無禮之事,不求己益,不動怒,不圖謀惡事,不以不義為樂,卻與責(zé)任同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永存不朽,而先知之恩終必消失,語言之恩終必停止,知識之恩總必消逝,現(xiàn)今存在的有信、望、愛這三樣,而其中最大的是愛。”《若望一書》講,“我們愛,不可只用言語,也不可只用口舌,而要用行動和事實(shí)。”新教圣經(jīng)的《馬太福音》講,“你若要進(jìn)入永生,就當(dāng)遵守誡命,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見證,當(dāng)孝敬父母,又當(dāng)愛人如己。”“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你施舍的時(shí)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路加福音》講,“所以無論何事,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yàn)檫@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愛鄰舍如同自己,你的信救了你。”《約翰福音》講,“‘神愛世人,不可按外貌斷定是非,總要按公平斷定是非。”《羅馬書》講,“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人,要彼此推讓。”“不要以惡報(bào)惡。”《以弗所書》講,“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約翰一書》講,“我們相愛,不要只在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shí)上。”《使徒行傳》講,“施比受更為有福。”印度教的《毗濕奴往世書》講,“審慎者,常于行、思、言三處精進(jìn),而利澤眾生。”《摩訶波羅多》講,“如果全人類中無人行寬恕之道,那末人類就無和平可言。”“那僅喪失財(cái)富的人,不因喪失而痛苦,但那失去善行的就是真是喪失了。”“行善惟在今日。”《摩奴法典》講,“應(yīng)該不斷專志于誦讀吠陀,忍受一切,親切,凝神,常予而不取,對一切物類表示同情。”《簿伽梵歌》講,“行布施,出乎真心,不期回報(bào),且要適人、適時(shí)、適地。此之謂純凈布施。”《泰迪黎奧義書》講,“以敬而布施,以樂而布施,以慚而布施。”《摩訶那羅衍拿奧義書》講,“世間一切眾生,依賜予者而生活,以布施而怨敵乃除,以布施而仇讎為友。” 錫克教(于15世紀(jì)在北印度創(chuàng)立)的《卡比爾的歌》講,“我心中珍惜超過一切的乃是愛,它使我在塵世享有永恒的生命。”巴哈伊教(于1844年由侯賽因·阿里在波斯創(chuàng)立,他自稱“巴哈安拉”)的《巴哈安拉作品集粹》講,“與人性的尊嚴(yán)相匹配的美德,乃是能以容忍、美德、慈悲、同情和友愛,來對待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和眾人。”“慈善的言語是吸引人心的磁石,是精神的食糧,它使文更加有意義,是智慧與理解之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最好的勸導(dǎo),愿你們遵守它。”“要做窮人的寶庫,要做富人的勸誡者,要回答困苦人的哭泣。”巴哈伊教的《隱人經(jīng)》講,“朋友啊,在你的心園里,除了愛之玫瑰,不要栽種別的。緊握著摯愛與祈望的夜鶯,不要放松。珍視正義者的友情,避免與邪惡者的一切交往。”
在各民族的宗教文化中,慈善理念與道德相比,層次更高。它是以倫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為基礎(chǔ)的。在倫理教育方面,各民族宗教都強(qiáng)調(diào)孝敬父母。天主教圣經(jīng)的《德訓(xùn)篇》講,“孝敬父親的人,必能補(bǔ)償罪過,且能戒避罪惡,在祈禱之日,必蒙應(yīng)允;孝敬母親的人,就如積蓄珍寶的人。”新教圣經(jīng)的《出埃及記》講,“當(dāng)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神所賜的土地上得以長久。”《箴言》講,“你要聽從生你的父親。你的母親老了,也不可藐視她。”《馬太福音》講,“神說,當(dāng)恭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印度教的《摩奴法典》講,“在生育和教養(yǎng)方面,母親和父親所受痛苦,雖幾百年,也不足補(bǔ)償。”《泰迪黎奧義書》講,“毋輕慢敬神明、敬父母之責(zé),奉母如神,奉父為神,奉師為神,奉客如神。”
各民族的宗教經(jīng)典中有關(guān)道德的教誡尤其豐富,因?yàn)榈赖率亲鋈说母尽6米鋈耍艜杂X做慈善服務(wù)。天主教圣經(jīng)的《圣詠集》講,“誰能登上主的圣山,誰能居留在他的圣殿,是那手潔心清、不慕虛幻的人,是那不發(fā)假誓、不行欺騙的人,他必獲得上主的降福和拯救者天主的報(bào)酬。”《斐理伯書》講,“凡是真實(shí)的,凡是高尚的,凡是正義的,凡是純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榮譽(yù)的,不管是美德,不管是稱譽(yù),這一切你們都該思念。”《希伯來書》講,“待人接物,不應(yīng)愛錢,對現(xiàn)狀應(yīng)知足。”新教圣經(jīng)的《出埃及記》講,“不可隨夥散布謠言。”“不可隨眾行惡,不可在爭訟的事上隨眾偏行作見證,屈枉正直。”“當(dāng)遠(yuǎn)離虛假的事,不可殺無辜和有義的人,因我必不以惡為義。”《詩篇》講,“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他不放債取利,不受賄賂,以害無辜。”“不要仗勢欺人,也不要因搶奪而驕傲。若財(cái)寶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箴言》講,“不義之財(cái)毫無益處,惟有公義能救人,脫離死亡。”“心中安靜,是肉體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爛。”“貪戀財(cái)利的,猶害己家;恨惡賄賂的,必得存活。”《提摩太前書》講,“貪財(cái)是萬惡之根。”印度教的《薄伽梵往世書》講,“物質(zhì)的利益和欲望永不饜足,此之謂貪婪。人以既得為滿足,是為幸福。”《摩奴法典》講,“忍讓、以德報(bào)怨、節(jié)制、正直、清凈、抑制諸根(意為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欲望)、認(rèn)識法輪(意為弘法)、認(rèn)識最高我、求實(shí)、戒怒,這些是義務(wù)由之構(gòu)成的十德。”“不得侮辱身體殘廢的人、無知的人、上年歲的人、貌丑的人、窮人以及出身微賤的人。”錫克教的《賈卜吉》講,“愚者沉浸在感官快樂里,最終導(dǎo)致痛苦;安逸而有罪的生活是疾病的原因。”“真理是一切美德中最高的,但是比真理更高的是合乎真理的行為。”《古魯那納克的頌歌》講,“沒有德性,哪有美德;沒有德性,人的生命也就喪失了。”
各民族宗教也都重視因果善惡報(bào)應(yīng)的教育,勸導(dǎo)人們審慎地做事、待人接物和善待萬物。道德教育是教導(dǎo)人們知道哪些是該做的,哪些是不該做的。因果善惡報(bào)應(yīng)的教育勸誡人們要有敬畏心,不敢做不該做的事。基督教新教圣經(jīng)的《詩篇》講,“未見過義人被棄,也未見過他的后裔討飯。”“他終日恩待人,借給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們當(dāng)離惡行善,就可以永遠(yuǎn)安居。”“說惡言的人,在地上,必堅(jiān)立不住,禍患必獵取強(qiáng)暴的人,將他打倒。”《箴言》講,“禍患追趕罪人,義人必得善報(bào)。”印度教的《薄伽梵往世書》講,“人人都自食其行為之果。”《摩訶波羅多》講,“以寬恕征服怒氣,以誠實(shí)征服邪惡,以慷慨征服吝嗇,以真理征服虛假。沒有誰行善反得惡果的。”《摩奴法典》講,“那有恒心、溫和、并且忍耐的人,那避開惡行的人,那并不害人的人,那自制的自由的人,能夠得到天上的福樂。”
倘若我們真誠恭敬地讀閱各民族宗教經(jīng)典,會感悟到,各民族宗教的締造者都是教育家。他們的使命是教化人民。但是為什么不同民族之間常有文化分歧呢?原因之一是在有些民族的多數(shù)人群中強(qiáng)調(diào)本民族不同于,乃至優(yōu)越于其他民族,并且把本民族特有的宗教看作本民族文化的神圣起源。比如基督教的圣經(jīng)中上帝告誡猶太人,“我是你們的上帝。……除了我之外,你們不可以信奉別的神明。”圣經(jīng)的“十大誡訓(xùn)”中,第一條就是“在我之外,你不能有別的神。”這是信仰的絕對專一,也因此容易驕傲自大,而排斥其他宗教。這種情緒的延伸,以致在基督教內(nèi)部,天主教信徒同新教信徒之間,乃至在新教內(nèi)部,不同教派信徒之間,不相往來。宗教之間的分歧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對立。而西方列強(qiáng),尤其是美國領(lǐng)導(dǎo)人,往往利用不同民族間的文化和宗教分歧,大力輸出其強(qiáng)勢的基督教文化,貶低其他宗教和其他民族文化,干涉他國內(nèi)政,以圖達(dá)到獨(dú)霸全球的目的。不過,世界各民族中有識之士許多年來呼吁世界各民族宗教的團(tuán)結(jié)和平等相處,推動世界和平事業(yè)。十多年來,在新加坡,繼則在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出現(xiàn)了不同宗教之間的團(tuán)結(jié)和諧的新景象,而其成功經(jīng)驗(yàn)是不同宗教相互學(xué)習(xí)對方的宗教經(jīng)典,相互就容易交流、溝通和對話。真正學(xué)習(xí)其他宗教的經(jīng)典,而非依靠道聽途說,就會發(fā)現(xiàn),各宗教之間是同多異少,實(shí)際上是一家人,乃至可以說是一體的。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大利亞宗教團(tuán)結(jié)和睦方面,中國的儒釋道的傳統(tǒng)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中國文化傳統(tǒng)有一種很強(qiáng)的包容性,中國圣賢主張的“和而不同”,而非像西方那樣強(qiáng)調(diào)歧異,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
我國慈善事業(yè)一直不斷地?cái)U(kuò)大國際交流,而其基礎(chǔ)工作是慈善理念的交流和對話,從而會有愈來愈多的共同語言,使我們慈善事業(yè)的國際交流有愈來愈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和內(nèi)涵。這樣,我們慈善事業(yè)的國際交流自然就會美美與共,與其同時(shí),也會為世界和平作出積極貢獻(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