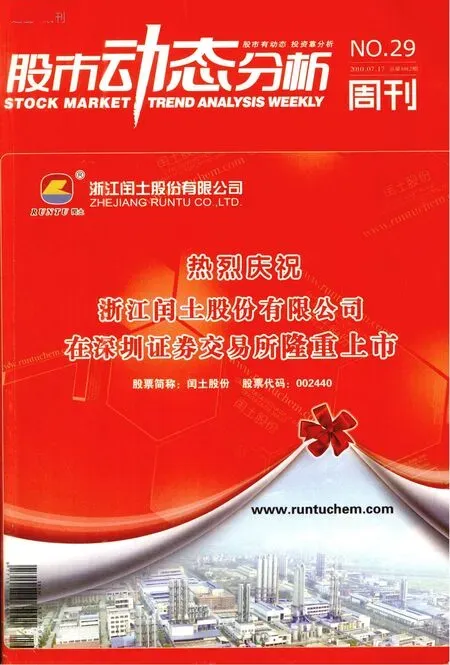“路線”大調整:此投資非彼投資
劉天智
今年“兩會”之后,中國完成了一次快速的上層建筑層面的調整——以果決的雷霆手段迅速厘定了延宕多時的中國未來改革發(fā)展路徑與模式爭論。三個月之后的今天,中國正在進行一場經(jīng)濟基礎層面的調整。這次雖不是“方向與路徑”的爭議,但即使是經(jīng)濟政策的“理論”(從凱恩斯主義回撤)和“具體手段”的差別(突出穩(wěn)增長下的投資拉動,與一層厚厚的“調結構”涂裝),也同樣會牽扯中國經(jīng)濟敏感的神經(jīng),特別是股市脆弱的心防。
自2009年以來,中國宏觀政策目標每年都在“增長、結構、通脹”之間徘徊。之所以這么糾結(特別是今年更加凸顯出政策抉擇的“兩難”),從根本上說,是長期以來對傳統(tǒng)高增長模式頑固的路徑依賴的必然。此前之所以會出現(xiàn)對原本早有定論的“經(jīng)濟改革發(fā)展路徑與模式”的爭論,恰恰是一種從既有模式的外部,對這種模式日益突出弊端的一次“修正和投機”。此次對宏調政策的基本理論和手段的探索與微調,則是從既有模式的內(nèi)部,對其弊端的一次“改良與補正”。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探索,都反襯出溫總理反復強調的“不通過改革,已經(jīng)取得的經(jīng)濟成果也將喪失”的迫切性。
中國在一季度末對所謂的改革路徑和模式爭論進行“撥亂反正”,迅速安定了中國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中長期路徑的預期,這是上半年中國決策層的一個重要成績。但二季度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差強人意,決策層對下半年經(jīng)濟形勢有所不安,隨著“十八大”的日益臨近,決策層必須盡快厘定經(jīng)濟層面的調整步驟和政策基調,但這一次卻難以如一季度對上層建筑層面的調整那樣快刀斬亂麻,否則,溫總理不會一周之內(nèi)四次調研,其他中央領導人也不會如此頻繁的開會、考察。這說明了經(jīng)濟形勢的復雜性、嚴峻性,也凸顯出決策層盡快“理順下半年經(jīng)濟關系、明確經(jīng)濟政策基調”的意愿。
在人大財經(jīng)委、政協(xié)經(jīng)濟委員會的一片呼吁“防止過渡刺激”的聲音之下,溫家寶總理、李克強副總理近期的若干次調研,均在強調“突出穩(wěn)增長、加大預調微調力度,需要一定的投資”之后,反復強調了N多的后綴。為何?
此次經(jīng)濟層面的政策調整,仍是一次復雜的“立場協(xié)調和關系重置”——已經(jīng)完成黨委換屆的各地方的上進心,和本屆中央政府的“求穩(wěn)定”之間;老一輩人的“繼往”,與新一代人的“開來”之間,都存在著立場、利益的磨合與調和;中央政府敦促的“調結構、開放民間投資領域”,和各部委在落實“36條”時“有原則、無細則”之間;國務院屢屢強調的“結構性減稅”,和各地方千方百計“抓大不放小、顆粒歸倉”式的地毯式征稅、擴大稅源之間,絕不僅僅只是落實不力、認識不充分的問題。至于那個“豬堅強”的房地產(chǎn)市場,為何在這么強悍的政策高壓之下,房價和成交量還能夠“起死回生”?
正因為此,溫總理才一周之內(nèi)四次開會、調研,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部門到居民個人、企業(yè)家、經(jīng)濟學家,從東部的江蘇到西部的四川,各方面的情況和利益都要了解、傾聽、兼顧。而最具代表意義的,就是“遍邀”反凱恩斯學派的經(jīng)濟學家到中南海座談,聽取不同意見,為正確判斷經(jīng)濟形勢、作出正確的政策抉擇做調研。我們認為,無論是對“推動投資”所附加的N多條件,還是國務院聽取“反凱恩斯”學者的不同意見,都反襯出決策層有意探索新的政策理念和模式的跡象,這是為未來更加長期的經(jīng)濟政策抉擇尋找理論的突破口,打破既有模式對政策抉擇的壓迫。但就短期而言,則更多是作為本屆政府不得不“再次依靠”投資來穩(wěn)增長的一種妥協(xié)。
全球經(jīng)濟衰退,中國經(jīng)濟環(huán)境惡化,疊加中國上層建筑謀求的“無縫對接”,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在2012年下半年交匯,使得中國經(jīng)濟及其上層建筑能否順利實現(xiàn)兩個不同階段的對接,這一疑問將始終懸在中國投資人的心頭。雖然,我個人仍然相信,在現(xiàn)有經(jīng)濟政治模式的護衛(wèi)下,我們最終能夠得以渡過這一“黑障期”,但不能夠確定的在于,其過程的控制是否讓身處其中的投資人受得了?如果多數(shù)人在殺向安全出口的半路上,就被周遭的險惡環(huán)境所恫嚇住,那么,眼下的“穩(wěn)增長”和未來“經(jīng)濟轉型”的成功,也只是一場“慘勝”,相當部分人可能要犧牲在長征路上,甚至是黎明前的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