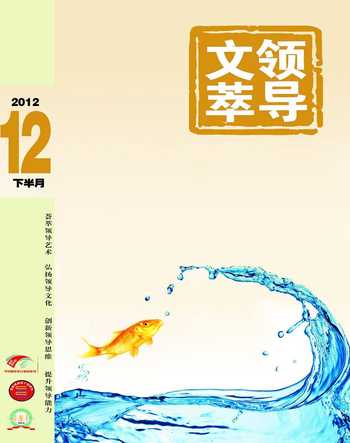20年后:西方視野中的戈爾巴喬夫
曉發
阿奇·布朗的功過評說
2011年2月28日,在戈爾巴喬夫生日之際,英國政治學家和歷史學家、《戈爾巴喬夫因素》一書作者阿奇·布朗撰寫了題為《戈爾巴喬夫80歲:對他成就的評價》的文章。布朗寫道:“他讓俄羅斯成為一個比以前更為自由的國家;他通過發揮非常決定性的作用結束了冷戰,提供了在更為和平與更為公正基礎上處理國際關系的機會。”他列舉了他所認為的戈爾巴喬夫取得的使俄羅斯和世界變得更好的12項重要成就:
實行公開性并將其發展為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釋放被監禁和流放的持不同政見者,為那些過去遭到不公正鎮壓的入平反;恢復宗教自由,結束了對教會的迫害;實行跨國界通信自由,包括停止干擾外國廣播和更多地交換信息,增加國外旅行的自由;實行真正的差額選舉以建立擁有實權的立法機構……
布朗認為,以上這些成就是對蘇聯歷史的根本性突破,俄羅斯和世界為此都要感謝戈爾巴喬夫。但同時,布朗也列舉了戈爾巴喬夫在改革中所遭到的失敗。他認為:“開始時是經濟改革,但是在改革后期,經濟處于一種不定狀態,既不再是指令性經濟,也不是有效的市場經濟。長期的共產主義統治使得蘇聯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比東歐國家或中國都更為困難。”
“另一個失敗是過于遲緩地由假聯邦制向真正的自愿的聯邦制的轉變。戈爾巴喬夫最為優先考慮的是:在國內進行自由化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在國外努力使國際關系具有新的基礎。蘇聯境內各民族和加盟共和國之間的關系沒有列入戈爾巴喬夫政治日程的前列,直到這些問題激烈地爆發出來。他的政治改革就是允許人民傾吐冤情和不滿而不擔心遭到逮捕和監禁,甚至允許選舉新的立法機構代表,打算為各加盟共和國尋找國家主權——這使得這個問題變得突出了。戈爾巴喬夫的對外政策以及他不贊成軍事干涉也使最為不滿的加盟共和國特別是波羅的海三國內部出現了期待。那里的人民開始相信,他們也能夠成為獨立的非共產主義國家。”
美國專欄作家的兩種對立評價
也是在2011年2月28日,美國作家和編輯卡特里娜·梵登·何弗在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登了題為《80歲的戈爾巴喬夫》的專欄文章,稱頌戈爾巴喬夫是當代民主史上一位關鍵性人物。
她認為,戈爾巴喬夫在差不多七年的執政時期(1985年~1991年)取得了兩項最偉大的成就。其一是,“到1991年的時候,他領導的俄羅斯是其千年歷史上最接近真正民主的;戈爾巴喬夫在1989~1991年在當時的蘇聯制度內所實行的議會選舉和總統選舉至今仍然是俄羅斯最自由和最公正的選舉。”其二是,實行了70年之久的書報檢查制度被廢除。
但是,戈爾巴喬夫所取得的這些民主成就卻被遺忘或掩蓋了。原因何在?何弗認為,那是因為美國人在蘇聯解體后匆匆把“俄羅斯民主之父”的桂冠戴到了葉利欽頭上。按照華盛頓流行的說法,葉利欽是“俄羅斯民主之父”,是一位帶領俄羅斯脫離極權主義的領導人,在他領導下,出現了民主國家之光。這樣,“戈爾巴喬夫的兩項最偉大的成就便淹沒于這種歷史的曲解中”。
何弗指出,有關俄羅斯的去民主化是在普京2000年成為總統后開始的觀點,已經受到許多俄羅斯評論家和史學家以及一些美國專家的質疑。他們認為,去民主化在葉利欽時期就開始了,特別是葉利欽總統在1993年10月出動坦克解散和搗毀俄羅斯經自由選舉產生的議會。從那時起,俄羅斯杜馬不再是戈爾巴喬夫時期選舉產生的充滿反對派的喧囂的立法機構。何弗的意思很清楚,戈爾巴喬夫才是真正的俄羅斯民主之父,美國人把“俄羅斯民主之父”桂冠戴到葉利欽頭上,實乃張冠李戴。
與何弗上述觀點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安妮·艾普爾鮑曼對戈爾巴喬夫的嚴厲批評,在2011年7/8月號一期的美國《對外政策》雜志上發表的題為《戈爾巴喬夫漫長的瘸腿般的后世生活》一文中,艾普爾鮑曼似乎決意要破除西方對戈爾巴喬夫的崇拜。
她寫道,在倫敦和華盛頓,戈爾巴喬夫常常被視為和平的象征和冷戰結束的象征,但是,對他的恭維常常是乏味和過分的。在倫敦的戈爾巴喬夫生日晚會上,一首二重唱歌曲唱道:“總有一天我們會想起,他為我們大家改變了世界。”主持人莎朗·斯通贊揚說:“如果俄羅斯沒有收獲自由民主的果實,它會怎么樣?”艾普爾鮑曼認為,這都是不真實的,因為俄羅斯并沒有真正收獲自由民主的果實,甚至戈爾巴喬夫自己最近還批評俄羅斯的民主是虛假的:“我們有民主機制,但是它們沒有效果;我們有法律,但是它們必須得到執行。”
她認為,“戈爾巴喬夫是一個改革者,但不是革命者;當他在1985年3月成為蘇共領導人的時候,他是想要復興而不是要瓦解蘇聯。他知道體制已經沒有活力,但是他不理解為何沒有活力。他不是去廢除中央計劃或要求價格改革,而是發起了猛烈的禁酒運動,結果是,蘇聯預算損失巨大,像食糖之類的產品嚴重短缺,人們開始在家里非法釀造伏特加酒。”
根據艾普爾鮑曼的分析,公開性原本是為了促進經濟效率。戈爾巴喬夫相信,公開討論蘇聯的問題將會加強共產主義,他肯定從來沒有想過制定對蘇聯經濟政策進行根本改革的政策。所以,作者這樣揭露戈爾巴喬夫:他決心挽救中央計劃經濟,才要求人民公開討論它;他決心挽救共產主義,才讓人民批評它;他決心挽救蘇聯帝國,才給予東歐國家更多的自由。
(摘自《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