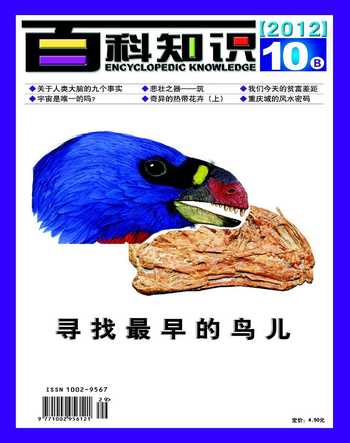悲壯之器——筑
宋蕾

“筑”是古代的一種擊弦樂器,這種樂器似乎在兩千年前非常流行。《戰國策·齊策》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戰國、秦漢時的古籍中多有對這種樂器的點滴記載,但據傳宋代時這種樂器就已經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今天的人們在閱讀史料時也只能見其影,而無法聞其聲了。
關于筑的起源,大約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打擊樂器起源較早,早期先民們在生產、生活中,偶然發現身邊的某些材料可以發出悅耳之聲,能激發起人們某種聽覺上的快感,久而久之,這些身邊的工具就漸漸演變為專門用來娛樂的樂器。例如石罄就是由古代的勞動工具石犁或石鋤演化而來的。筑這種擊弦樂器也許最初就是人們用一截木頭繃上弦后拿來擊打發聲的樂器,由于其聲慷慨激昂,非常適合人們和歌時擊打節奏,因而得以流傳廣泛。
中國有著十分深厚的禮樂傳統,古代樂器相當發達,據記載,周代的樂器就有數十種之多,周人根據其材質的不同,將樂器分為8大類,即金、石、土、革、絲、木、瓠、竹等。這些樂器或留傳至今,得以發揚光大;或早已不存,湮沒于歷史的長河之中。筑這一古老樂器的傳承則屬于后者。
對于這種樂器的描述和使用方法也見于文獻記載。東漢許慎所著《說文解字》對其有注:“筑,以竹擊之成曲。五弦之樂也。從竹,從鞏。鞏,持之也。竹亦聲。”這條注釋告訴我們,筑是一種擊弦樂器,用竹尺擊打其上的5根弦發出不同的聲音,演奏時一只手持筑,一只手拿著竹尺擊打。《漢書·高帝紀》應劭注:“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筑。”顏師古則云:“今筑似瑟而細頸也。”
這種呈棒狀的擊弦樂器雖今已失傳,但在先秦兩漢時期卻是一種流行的敲擊樂器,不少史籍中為我們留下了與它有關的只言片語。
易水悲歌
《史記》載,荊軻本是衛國人,游于燕都,與擊筑師高漸離交好。荊軻嗜酒,酒酣時,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相與為樂,或相泣而對。后荊軻被太子丹奉為上卿,命去刺秦。燕太子丹到易水邊送行。這時,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著筑聲而歌,當筑擊出“變徵”的凄涼音調時,送行的人都掉下了眼淚。當筑擊出“羽聲”時,慷慨激昂,送行的人聽后都怒發沖冠。于是,荊軻頭也不回地踏上了不歸路。詩人阮瑀評價此事道:“燕丹養勇士,荊軻為上賓。圖盡擢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
以筑刺秦
荊軻失敗后,高漸離便更名改姓藏匿起來,為某大戶人家當起了酒保。一日,主人家發現他會擊筑,便叫他到堂前為賓客演奏。高漸離取出匣中的筑,換好衣服,改變妝容來到堂前。當他擊筑而歌時,滿座皆驚,無不為他的歌聲感動而流下熱淚。高漸離是擊筑高手,不久就名聲大噪,城里的人相繼請他去作客擊筑。
這件事不久就傳到了秦始皇的耳朵里。 秦始皇召令進見,有認識他的人報告說:“這就是高漸離。”但秦始皇憐惜他會擊筑,就大赦了他的死罪,卻殘忍地熏瞎了他的眼睛,讓他專門為自己擊筑。秦始皇非常喜歡他的音樂,沒有一次不拍手稱好的。高漸離就想借為他演奏的機會再次刺殺嬴政以完成好友荊軻的遺愿。于是,他在筑的中空腔內填塞鉛塊,在演奏時憑著聽覺揣摩秦始皇的位置,預謀在秦王靠近他時以手中灌了鉛的筑猛擊秦王頭部,不料因為他眼瞎看不見秦王的具體位置而沒有砸中。秦王大怒,殺掉了高漸離。
唐朝詩人李白在他的《結襪子》一詩中為此歌詠道:“燕南壯士吳門豪,筑中項鉛魚隱刀。感君恩重許君命,泰山一擲輕鴻毛。”
劉邦擊筑高唱《大風歌》
直到漢代,筑依然保持著它的生命力,最有力的證據就是漢高祖劉邦曾擊筑高唱《大風歌》。英布是西楚霸王項羽麾下的一員猛將,后倒戈與劉邦結盟,擊敗項羽,為漢王朝的建立曾立下赫赫戰功。劉邦明令“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 后,他先后誅殺韓信、彭越等異姓諸侯王,英布唯恐自己也將遭受同樣的命運,便先起兵反叛。公元前195年,劉邦親自率兵征討,英布大敗。漢高祖劉邦在擊敗英布后回到故鄉沛縣,在慶功宴會上親自擊筑高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威振海內兮回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在場的120名沛縣少年和歌,群情激昂。這種樂器演奏出的樂音悲壯慷慨,用于軍中鼓舞士氣、壯軍威。另據《西京雜記》載:“漢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即說劉邦的姬妾戚夫人善于擊筑,他常要戚夫人擊筑,自己高歌。
其影重現
筑這種樂器失傳了近千年,有關它的形制和演奏方法,今天的人們已經茫然不清了。20世紀70年代,湖南長沙市東郊馬王堆漢墓的發掘終于讓人們有機會一睹兩千多年前漢代的這種樂器。考古學家在馬王堆共挖掘出3座墓葬,分別屬于西漢第一代轪侯利倉及其夫人和兒子。中國古人“事死如生”,為了讓死者在另一個世界里繼續享受“現世”的繁華,他們生前所使用、所喜愛的各種物品都被埋入地下,筑這種樂器作為死者生前喜歡的樂器也被埋入地下,雖為隨葬明器,但依然為我們揭開了筑這種樂器的神秘面紗。
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即利倉兒子的墓中出土一件通體髹黑色漆明器,器長31.3厘米,寬2厘米,厚2.6厘米,形如四棱長方木棒,首部的蘑菇形柱上還殘存著纏繞的弦絲,尾部細長,為柄狀實心木,應該是手握持的部位。頭部有5個弦軫,尾部有一個弦柱,能張5根弦。當時,在挖掘現場的考古專家都不認識它,據參與挖掘的傅舉有先生說,在編寫《長沙馬王堆漢墓挖掘簡報》時它都沒有被提及。后來,根據隨葬品清單的記載:“筑一,擊者一人”字樣,音樂家終于辨認出它就是早已失傳的古代樂器——筑。
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黑地彩繪漆棺上還繪有這樣的圖景:在漫卷的流云中,一種頭上長著鹿角的神獸,也就是漢時人認為一種能夠延年益壽、名為“虛”的神獸,左手執筑,右手擊弦,它時而雙臂張開,時而用力擊筑,該畫面仿佛在告訴我們這種早已湮沒不存的古代樂器應該如何使用。
消失的秘密
關于筑是如何消失的,我們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漢末傅玄(217~278年)在他的《琵琶賦(序)》中的一則記載似乎隱隱約約道出了一絲隱情。據傅玄的記載,漢公主遠嫁烏孫時曾命匠人參考琴、箏、筑、箜篌等多種古代樂器制成了一種新的樂器——琵琶,帶到西北少數民族中去,后來這種樂器又回流到了中原,可是人們就以為它本是西域的樂器了。無論怎樣,筑這種擊弦樂器也許就是在這種融合中漸漸消失了吧。
【責任編輯】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