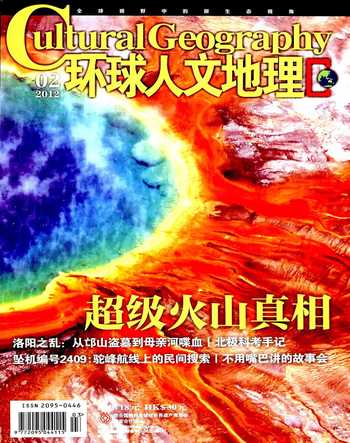一個民間科研機構的小城故事
龔靜染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從書中看到“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的時候,并沒有把它跟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也沒有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去尋找它的蹤跡。但后來我才知道,正是這個民國時期的著名科研機構,離我的童年生活并不遙遠,因為“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舊址就在川南的五通橋,距離我家還不到300米遠,而它曾經所在的那個老院子是我以前經常玩耍的地方。
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是中國著名實業家范旭東先生于1922年8月創辦的。當時,他以久大精鹽公司化驗室為基礎,在天津塘沽正式成立了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并開始圍繞鹽堿化工進行科研活動。但抗日戰爭一爆發,“黃海”就被迫遷至川南五通橋,同它一起遷來的還有當時中國最大的鹽化工企業——永利化學公司,“黃海”在五通橋繼續存在了十多年,直到解放初期才搬到北京,被中國科學院接收。
范旭東為什么要把“黃海”和“永利”遷到五通橋呢?還是因為鹽。當時五通橋是中國內陸重要的井鹽產區之一,能為鹽堿化工提供豐富的資源,所以他將這里作為建設“新塘沽”,重振民族工業的大后方基地。
小城里的科學之光
五通橋是座位于川南的古鹽城,清咸豐以前一直是四川最大的鹽場,所以到了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鹽務總局、永利化學公司、黃海化學工業研究社紛紛搬到了這里,五通橋的鹽業地位空前高漲,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戰時鹽業“陪都”。“黃海”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了它新的歷史,然而,這段歷史至今殘缺不全,影像和文字的記述少之又少,以至于在后面的歷史表述中處于被遮蔽和缺失的境地,作為豐厚的文化遺產,它正漸漸流失在時光中。
為什么要叫“黃海”?范旭東說:“我們深信中國未來的命運在海洋”,故名“黃海”。我的理解是,它是中國的一批文化精英懷著民族復興理想,追求科學和學術的自由精神。我從很多年前便開始陸續走訪相關人士,翻閱檔案資料,搜集整理素材,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追蹤歷史記憶,真實地再現那段歷史。
1939年“黃海”西遷后,在社長孫學悟主持下,根據客觀條件修改了黃海社章,決定從事西南資源的調查、分析與研究,輔助西南化學工業開發,他們所做出的很多努力都濃縮在了一本叫《海王》的雜志里。這本雜志是我國最早的企業刊物,對中國近現代科學界有著深遠的影響。雜志從1928年創刊到1949年停刊,其間21年,總共辦了300多期,其中從1937年后均是在五通橋編輯出版的,所以它的每一期都注明了出版地:樂山五通橋四望關。
“黃海”在五通橋期間,大力普及科技知識,啟蒙民眾,舉辦科學展覽,對當地人民的生產、生活都大有裨益。比如在方心芳、肖永讕等生物化學家的精心研究下,將在當地“德昌源”豆腐乳中發現的毛霉成功地命名為“中國五通橋毛霉”,并成為了教學和科研的標準發酵霉;又如,“黃海”工程師負責犍樂鹽場電力吸鹵的安裝試驗工作,將大順井由牛力吸鹵成功地改變成了電力吸鹵,實現了千年鹽井技術的大躍進;再如,1939年樂山地區突然出現了一種當地人談虎色變的“疤病”,而“黃海”專門對此病進行研究,得出病因就是食鹽中含有氯化鋇所致。在他們的努力下,這個曾經困擾人們多時的病魔很快就被消滅了……
當然,“黃海”不僅給地方帶來了厚重的文化積淀,還一直從事著更為高端的科技研究,其中有兩件事堪稱偉大,可以彪炳史冊:一是以侯德榜先生命名的“侯氏制堿法”在五通橋研制成功,震驚了世界,打破了國外對制堿技術的壟斷,開創了世界制堿技術的新紀元;二是在“黃海”的支持下于1943年在五通橋楊柳灣打出了全國最深的鹽井,井深超過了玉門油井,被稱為一時之盛。
當時的“黃海”是個開明的民間學術機構,不僅在科技方面走到了國人的前列,而且成了中國科學界的一面思想旗幟,他們主張“工業的基礎在科學,科學的基礎在哲學。”因此在1946年夏天,時年62歲的國學大師熊十力應邀來到五通橋,他此行的目的就是想在中國創辦一個真正具有“民間意味”的哲學研究所,而“黃海”就給他提供了這樣的機會,讓他主持“黃海”的哲學研究部,并將之看作是中國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之思想發軔。在“黃海”的那段時間里,熊十力先生不僅領略了橋灘的旖旎風光,日日與茫溪相伴,還陸續發表了《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等文章。那是一段寧靜的時光,熊十力曾經想用他的余生在這里完成他宏大的哲學夢想,但歲月倥傯,這個遙遠的夢想已經散落在了時間的塵埃之中。
“黃海”人在五通橋的光陰
如今,健在的“黃海”老人已寥寥無幾。2009年冬天,我曾去北京走訪了已92歲高齡的著名漫畫家方成先生,他曾經就是“黃海”的助理研究員,在五通橋度過了4年難忘的時光。當年“黃海”就坐落在四望關附近一個地主大院里,也就在那座簡陋的老房子里,先后聚集了當時中國化學界最優秀的人才:范旭東、候德榜、李濁塵、孫學悟、陳調甫、任可毅、黃漢瑞、方心芳、謝為杰、魏文德……周恩來后來曾說,那是中國的一個“技術簍子”。
方成先生談起過往的歲月也很幽默,他說他在“黃海”沒有成為“化學家”,卻成為了“畫學家”——那是因為一段愛情,而那段愛情就發生在五通橋,雖然這其間多少還是有些慨嘆,但我更愿意相信,這是在為當時極其艱難的生活留下的一段生動記憶。
“黃海”人的生活是清貧的,但充滿了生機,他們的故事要用一本專著來記載。“黃海”社長孫學悟當時信佛,工作之余經常一人跑到五通橋菩提山上的洞里去打坐靜修。有一次,他一如往常到那里去靜坐,等打坐完后才發現身后有一頭豹子,盡管那頭豹子并沒有傷害他,他出洞后還是被嚇出了一身冷汗。孫學悟雖然是科學家,每天同數字、圖表、試驗瓶打交道,但他的生活依然忘情于山水。這個小故事沒有因歲月久遠而消弭,這說明“黃海”精神永存,在時空中還留著它沒有散失的氣場。
當然,“黃海”的影響是巨大的,無論是在科技界還是文化界,它都影響過很多人,讓他們的思想、境界甚至人生道路都發生了改變。我曾經走訪過一個叫曾國鈞的老人,他早年以優異的成績考進“黃海”學習,并留下了他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時光。正是這一段經歷,讓他見證了“黃海”,見證了中國危難時期一個貧窮而純粹的民間學術組織,見證了那些理想崇高、無私而坦蕩的謙謙君子……我見到曾國鈞老人的時候,他已經躺在病床上,他緊握著我的手,為我講述的那些歲月中的人和事,時間只有短短一小時,然而這是讓我永遠難忘的一小時。十多天后,曾國鈞先生便去世了,我跟他在臨終前的一面,讓我看到了他心中那個永遠的“黃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