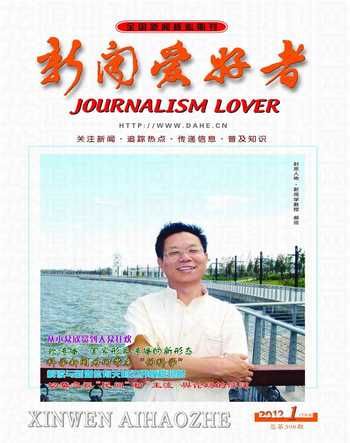辛亥革命時期張元濟的出版活動與出版思想
余顯仲 徐恒飛
【摘要】辛亥革命時期,張元濟本著“以扶助教育為核心”的出版理念,主持并參與了眾多的出版活動。他在經營商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出版經營思想。張元濟以教育和文化為重任的改良主義救國立場,使他在時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條獨特、成功的個人道路,也為中國近代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張元濟;辛亥革命;出版家;出版思想;改良主義
張元濟(1867年~1959年),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1902年受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務印書館,歷任編譯所所長、經理、監理、董事長等職。在加盟商務后的半個多世紀里,張元濟將出版事業和教育理想結合在一起,孜孜不倦地經營出版事業。商務印書館在諸多方面引領了中國出版界的潮流,并確立了一系列標準,成為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一切都與張元濟的出版理念及經營思想分不開。張元濟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改良主義者,他進入商務時,正值近代中國社會和政局由維新改良向民主革命過渡的動蕩時期,而且身處中西交流頻繁、革命思潮活躍的上海。但他卻一直遠離政治潮流,全心經營出版,并且大力推動了近代中國出版和教育事業的發展。
張元濟的出版理念:以扶助教育為核心
張元濟作為維新運動的參與者,與許多主張“變法”的知識分子一樣,渴望通過改良來尋求中國的富強。“戊戌變法”失敗后,他更加堅定了自己對于培養人才、開啟民智的認識,認為只有改進和擴展國民教育,才能為變革和發展提供適宜的文化環境與精神人格。他的這一意識在辛亥革命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肯定。
1902年初,張元濟正式加入商務印書館后,與夏瑞芳約定“吾輩當以扶助教育為己任”。作為商務印書館的掌門人,張元濟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這使得他在經營商務印書館時要努力地去平衡文化性和商業性,力求使二者達到統一。張元濟的雙重身份也使得商務印書館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經營原則:不出不賺錢的書刊,不出與時事政治相沖突的書刊,不出品格低下的書刊。
辛亥革命時期張元濟的出版活動
張元濟的出版生涯前期與辛亥革命時期①有較多重合,這段時間是張元濟出版活動和出版思想從萌芽走向成熟的階段。在社會思潮泛濫的上海,他既未輕易調整自己的改良立場,也未因革命潮流而忽左忽右地變化,而是根據自己對社會發展與文化需求的理解來確定出版方向。其帶領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圖書和期刊,既符合時代變化的需要,又能經受住歷史的檢驗,具有持久的知識和理性價值。這也正是張元濟堅持溫和的文化和教育改良理念的結果。
教科書出版。張元濟在加入商務印書館后,首先就是抓新式教科書的出版。他力薦蔡元培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由蔡元培牽頭開始編纂新式教科書。蔡元培擔綱國文、歷史、地理三種教科書的編纂體例工作,聘請愛國學社的教員蔣維喬任國文編輯,吳丹初任歷史、地理編輯。1903年蔡元培離開商務印書館后,張元濟親自擔任編譯所所長,聘蔣維喬為常任編輯員,并由蔣介紹莊俞編地理、徐雋編算學。而國文教科書的編輯則由張元濟、高夢旦、蔣維喬、莊俞等討論決定。《最新國文教科書》包括初等小學10冊,高等小學8冊。《最新修身教科書》包括初小用者10冊,供高小用者8冊。[1]此外,為了使教科書能夠被有效地應用,還編輯了十種教授法、三種詳解、十三種中學校用書以及師范學堂用書等。除了小學教科書之外,張元濟直接參加組織編校的教科書還有供女子學校使用的女子教科書、共和國新教科書以及單級教科書等。
報刊出版。張元濟積極主持和參與各類報刊的出版活動,從早期對于《時務報》的關注,到后來主持參與出版《外交報》、《繡像小說》、《東方雜志》等旨在開啟民智、提高國民素質的一系列報刊,都體現了他通過普及知識提高國民素質來實現變革的革命意識。
在南洋公學期間,張元濟與蔡元培、溫宗堯、趙從蕃等開始創辦《外交報》。張元濟在該報的《敘例》中提出了“文明排外”的理論,稱:“……蓋人之生也,無不以自利為宗旨者;國之立也,即無不以自利其國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奪之事。凡以凌侮劫奪人為事者,例不以見凌侮劫奪為怪,是以彼我之間,蕩蕩然無界畔、無契約,緣隙生事,罄竹不勝書。及其迭經自然、人為之兩淘汰而殘存于茲者,漸趨知力平等之勢,又以經歷既多,識見漸澈,知前者凌侮劫奪之為兩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兩利之術,于是人與人有倫理,而國與國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權,不受凌侮劫奪為界說,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2]該理論還被張元濟定位為《外交報》的辦報宗旨。他認為當時的中國在過去的數十年中盲目排外、野蠻排外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所以要提倡文明排外。《外交報》共有論說、諭旨、文牘、譯報等8個欄目,主要介紹各國的動態等國際知識,是當時社會了解國際的一個重要窗口。《外交報》最初由杜亞泉的“普通學書室”發行,隨著張元濟、杜亞泉加入商務印書館后,該報也轉由商務印書館代印和經銷。《外交報》停刊于1911年1月15日,前后歷時9年,共計324期。
張元濟十分重視報刊等大眾傳媒在傳播知識、開啟民智、引導輿論等方面的作用,他的國民教育思想在商務印書館所創辦的各類雜志中也都有所體現。1903年創刊的文藝半月刊《繡像小說》,每期刊載長篇連載小說或單篇小說10種左右。在創刊號上,創辦者就稱該刊將借小說以針砭朝政之積弊,為國家危險立鑒,以此喚醒民眾。1904年編輯發行的《東方雜志》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悠久的大型綜合性雜志,按月刊載中外大事記、中外時事匯錄和各類匯志,內容涉及中外重大政治、經濟、文化事件和要聞。張元濟在執掌《東方雜志》期間,始終以宣傳立憲政治主張為主,確立了《東方雜志》“啟導國民、聯絡東亞”的辦刊目的。辛亥革命時期的《東方雜志》注重對西方政治思想、民主觀念、新式教育、新文學以及西方自然科學的傳播。《東方雜志》雖為選錄類雜志,但從其所刊載的文章中亦可見其辦刊目的。
張元濟的出版經營策略及其經營思想
唯才是舉的編輯用人觀。張元濟與發起人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等人在知識結構和從業經歷上的差異,使他一加入商務印書館,就承擔了編書的重任;而夏、鮑、高等人則主要負責印刷與發行。張元濟的翰林出身、維新思想以及與眾多學術界、文化界名人的良好關系,為其在出版業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張元濟在擔任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期間,商務編譯所得到了迅速發展,從成立之初的幾個人發展到1908年的64人、1921年的160人左右。張元濟本著“唯才賢與新進是求”的重才觀念為商務印書館延攬了一批知名學者,組成了一支非常優秀的編譯隊伍。在與日本金港堂合資運作后,張元濟也不忘網羅人才,充分利用機會,挖掘日方專家的經驗,為商務印書館出版教科書所用。
發行人員的職業教育觀。隨著商務印書館發行業務的蒸蒸日上,張元濟意識到發行隊伍較低的文化素質已不能滿足圖書發行的需求。他主張對發行人員進行培養,于1909年開辦了商業補習學校,力圖培養自己的發行骨干。他要求所有的圖書發行人員在熟悉各種書的基礎上,還要清楚所推銷書籍的優點和特點,以提高圖書推銷的有效率,擴大圖書銷售,增加利潤。從1909年到1923年,商業補習學校共舉辦了7屆,畢業學生達318人。由于補習學校較強的教學針對性,較多的實習機會,大多數學員畢業后都能逐漸成為發行業務骨干,這進一步推動了商務印書館的發行業務。
身兼文人與商人雙重身份的張元濟,在經營商務印書館的過程中,逐步探索商務印書館的近代企業發展之路。張元濟的這種經營探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商務印書館的多元化經營,二是商務印書館的資本運作,三是商務印書館靈活多樣的發行方式。
以文教為核心的多元化經營思路。商務印書館除出版社之外,還擁有編譯所、發行所和印刷所,并在全國各地設有分館、支館。張元濟在穩定出版主體地位的同時,積極將商務印書館向橫向進行拓展。早期創辦通藝學堂為張元濟積累了辦學的經驗,在商務印書館步入穩步發展階段時,張元濟開始創辦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機構,如幼兒園、小學以及商業補習學校等。除此之外,張元濟也涉足工商領域,創辦電影廠、玩具廠等一系列的工商企業,為當時的出版業提供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張元濟為商務印書館所考慮的橫向拓展業務的經營思路并非率性而為,這從商務印書館所創辦的一系列企業的經營范圍和經營領域中可以看出,這些企業都是緊緊圍繞“文教”這一核心展開的。這些企業的創辦,進一步擴大了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影響力。
強調主權的資本運作意識。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期間,得到了夏瑞芳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他在掌握編書大權的同時,還在經營策略上具有一定的決策權。商務印書館吸收日資的經營之舉在當時可謂一大創舉。作為一名商人,張元濟敏銳地洞察到雄厚的資金對于經營一家企業的重要性。在張元濟“實業首重資本”理念的指引下,商務印書館在1903年和日本金港堂約定各出資10萬元,組成股份有限公司。商務印書館的股本從創業初期的3750元迅速增加到20萬元。但張元濟并沒有被此沖昏頭腦,在與日本金港堂合作的過程中,他對雙方的合作進行了詳細的約定,以確保商務印書館的經營主權。
重視發行渠道建設。張元濟在商務印書館期間,十分重視圖書的發行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發行措施。就拿商務印書館與日本金港堂的合資運作來說,張元濟充分利用此次合資的機會,在各地設置分館、支館,進一步擴大了圖書的發行范圍,自合資當年建立第一家分館起,到1932年,商務印書館在天津、北京、沈陽、香港等地共建立36處分館、支館。商務印書館還推出了“送書上門”和“郵售”等發行形式。這里的“送書上門”指的是商務印書館針對教科書銷售的季節性特征,在學校春秋兩季開學前,有針對性地設點推銷教科書,學校、個人甚至其他教科書銷售機構、銷售商均可以非常便利地從特設銷售點購買教科書。而“郵售”業務則有利于偏遠地區的教科書銷售,大大開拓了教科書的銷售市場。通過構建這種多元化、立體型的發行網絡,張元濟進一步強化了商務印書館為讀者以及教育工作者服務的功能。
結語:政治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改良
張元濟雖是清末翰林出身,其人生的青壯年時期卻經歷了晚清的改良運動和辛亥革命,與許多主張變法維新的晚清知識分子一樣,他也渴望通過變法改良來實現中國的富強。但他并不熱衷于政治,性格上也不具有激進色彩。同時,在他的意識中,輸入新知培養人才是實行社會變革的基礎,而這些目標是政治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他雖不贊同革命,但也沒有清末遺老的保守和腐朽氣。當他投身出版界后,所作所為并不因時而變,更沒有輕率地趨從革命,而是中道而行,堅持以教育和文化為重任的改良主義立場,苦心經營商務的文化出版事業,并兼顧報刊出版和服務教育,在時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條獨特但很成功的個人道路,也為中國近代出版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本文為浙江省社科規劃專項課題“辛亥革命時期的浙江報人與報業研究”(項目編號:10WHXH05)的階段性成果]
注 釋:
①辛亥革命的歷史分期在中國的歷史研究領域向來有幾種寬窄不同的說法,狹義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發的武昌起義;而廣義的辛亥革命說法也有二:其一是從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開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凱鎮壓為止的革命活動;其二是將起點算到1905年同盟會的成立。本文遵從第一種廣義的說法。
參考文獻:
[1]張學繼.出版巨擘——張元濟傳[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3:99.
[2]張樹年.張元濟年譜[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41-42.
(作者單位:浙江萬里學院文化與傳播學院新聞系)
編校:張紅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