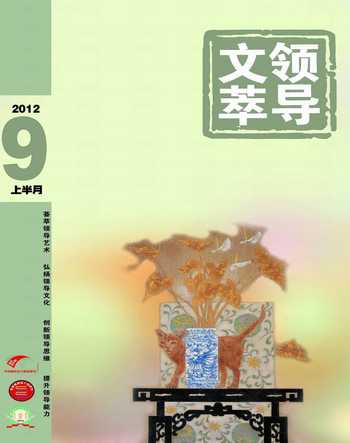資本國家化還是資本社會化:國企體制改革的選擇
秦曉
國企體制是我們當前面對的各種經濟問題中最需要突破而又最難突破的問題。說它最需要突破不是因為在國企經營層面上存在治理和管理、效益和效率方面的問題,而是因為國企在體制層面上造成“國進民退”、壟斷、民間資本外流等社會問題,這個問題能否及時、妥善處理關系到黨和政府的執政正當性。說它最難突破是因它涉及到對社會主義本質,憲法中關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表述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觸及到已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
陳清泰文章(見《財經》2012年第13期“國企改革再清源”)最大的亮點是揭示了國有企業只是一個載體,它的本質是國有資本。所以國企的進、退實質上是國有資本的流動和重新配置。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將這個命題再推進一步,即什么是國有資本?我以為國企積累的國有資本應該是資產形態的財政盈余,因為財政只有現金流量的收支賬,沒有資產負債表,如果建立了“國家資產負債表”,這個問題就更加清晰了,它應列入“國家資產負債表”中的資產方,同時國企的負債應列入負債方,其凈資產即是國家作為股東的權益。國企資產形態的國有資本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產,也是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后發展積累形成的。無論是財政的盈余還是國家作為股東的權益,它都應被視為公共財政的資源。國企制度的改革,國有資本的流動和重新配置就是要還其屬性,將其運用到與民生相關的公共產品上,如社保、醫療、教育、住房等。所以,這個轉化的實質是國有資本的社會化和國企的民營化。當然,這一過程應是有序的、有效率的、公平的、通過市場運作的。
國有資本社會化是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表現,它可以推動投資型的財政向公共財政的轉變,加快社保體系的建立、改善公共產品短缺的狀況。與此同時,它也有利于建立一個公平、有效、自由的市場體制。
目前要建立這樣一個認識,實施這樣一套改革在觀念上、利益上存在較大的障礙。
一是所謂公有制和私有化的問題。列寧、斯大林在前蘇聯沒有實現共產主義的情況下將這一制度付諸實踐,形成了全民所有制,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也相應建立了全民、集體兩種形態的公有制。實踐證明這種體制約束了生產力的發展,剝奪了現代社會個人應有的權利和自由。前蘇聯的解體、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對這種體制的否定。在市場化轉軌過程中,中國的國家體制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公有制;在微觀層面上的國企不能被視為公有制企業,它的本質與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如新加坡航空公司及各種主權基金公司一樣,都是政府財政投資的企業。將國企視為公有制企業,并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公有制為基礎的概念和邏輯都是不成立的。
二是國企的屬性和功能。即國企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商業機構,它除了要承擔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外,還要承擔政治、經濟、社會的特殊功能,如“國企是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國企應控制關系國家戰略和國計民生的產業”等。
從政治上講,權力來自人民,執政黨的基礎歸根結底是取決于它們倡導的理念、建立的制度、推行的政策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擁護和贊同,而不是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從國家發展戰略、國計民生的保障來講是科學、民主決策和市場經濟活動互動的過程,而不是政府通過控制企業、替代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對具有自然壟斷和公益特征的行業,前者如電網、鐵路,后者如管制價格下的能源,水、電、氣等大多數都可以通過頒發許可證、確定價格和收益、公開招標由私人部門承擔。
政府的職責是制定規則和監管運行,而不是通過所有權來實施,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價格管制的行業不能一概被視為公益性行業。
什么是以公有制為基礎?我認為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潮它所追求的是社會的公平、正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制度所應保障的也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這在鄧小平的“三個有利于”、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中已有了充分的、與時俱進的體現。關于公有制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股份制是公有制體現的主要形式”在上世紀90年代已寫入了黨的決議。
現在有些人在國企制度改革問題上重提姓資姓社,公有私有,這是對30年改革開放中形成的共識的顛覆和倒退,也是對市場化轉軌取得的成就的否定。這不僅反映出觀念的陳舊,更值得警惕的是特殊利益集團的掣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新一輪改革不僅需要觀念的更新,還需要克服特殊利益集團的阻撓。(摘自《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