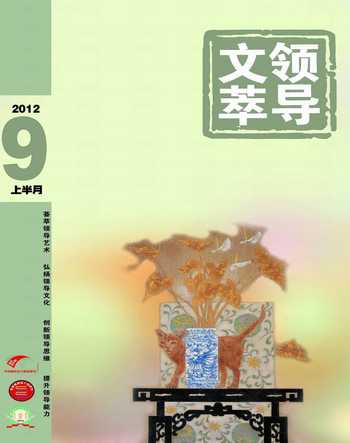龍應臺:角色轉換之間
李立
關于龍應臺的新聞,總是能夠吸引人們的眼球。今年2月,這位著名作家正式上任臺灣“文建會主委”。5月20日,該部門改稱“文化部”,她是“文化部”第一任負責人。
從文化人“變臉”成為政府文化官員,又還原為文化人,最近又再度為官,龍應臺的角色轉變讓人充滿想象空間。寫《野火集》、《百年思索》的作家龍應臺,當文化局局長、“文建會主委”的龍應臺,究竟哪一個才是真正的龍應臺呢?
馳騁文壇的“龍旋風”
對于大陸民眾來說,龍應臺最重要的身份是作家。以名作家與人文學者的身份游走兩岸三地的龍應臺并不乏爭議。有人批評她總以“外省人式”的眼光看世界,甚至有些“緬懷威權時代”。龍應臺自己說,她過去經常被臺灣輿論政治性地解讀為“獨派”,現在又經常被解讀為“統派”。喜歡她的人稱她是“女魯迅”,不喜歡她的人稱她是“女希特勒”。褒貶任憑人說,龍應臺還是龍應臺。
1952年,龍應臺出生于臺灣高雄大寮。由于父親是職業軍人,小時候經常搬家,而在不斷的搬遷中,也養成她站在心靈邊緣冷眼觀看世界的個性。
1969年,龍應臺進入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后赴美攻讀英美文學博士,畢業后任教于紐約市立大學。出國十年之后,由于想念“臺灣夏日里四處漂漾的茉莉花香”,1983年8月,龍應臺偕同德籍夫婿回臺,任教于“中央大學”英文系。
龍應臺以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與勇氣,從《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開始,走上了以雜文批評社會的寫作路線。她的文章猶如一把燎原的野火,燒痛臺灣社會已久的陳疴,也為臺灣社會提供一個反思的空間。1985年,龍應臺寫的系列文章集結成《野火集》出版,一個月內再版24次,在臺灣掀起了一陣“龍旋風”。
1986年,龍應臺離開臺灣,與夫婿旅居瑞士,后到德國定居,此時她告別了《野火集》的寫作方式,同時,也拓展了視野。這時候的作品有《人在歐洲》、《從東歐看臺灣》、《寫給臺灣的信》等雜文集,與此同時,她也在為人妻、為人母的成長歷程中,寫出了一系列關心女性問題的書。
龍應臺思索問題的深度與廣度集中體現在《百年思索》一書中。這本書上下縱貫百年時序,論述涵蓋東西文化,除了延續其銳利的觀察之外,也蘊含了歷史的滄桑與無奈。龍應臺的文章也從犀利的批判轉為同情的了解。
雖然旅居海外十多年,龍應臺仍保持了對臺灣的持續關注。1999年,龍應臺出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提出“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觀點。
“學而優則‘事”
龍應臺曾經說過,她是儒家的信徒,總是想著“學而優則仕”。不過,她認為那個“仕”不是要謀官,而是要做事。
1999年11月,時任臺北市長的馬英九專程前往德國,邀請旅居法蘭克福的龍應臺回臺北市當文化局長。
龍應臺接到邀請后,她的思緒很多。龍應臺說她之所以接受邀請擔任此職,一個重要的考慮就是,臺北市設立文化局是第一次,史無前例,她害怕這個部門會變成市長的宣傳機構、御用單位或政治的附庸。她心里是帶著這些恐懼“下海”的。“說實在話,當時我答應這件事時,沒想到去做官,只想到去做事”,龍應臺如是說。
的確,對龍應臺來說,“偶然”當官只是帶職下放,好像進行一次田野調查,只是跟讀者暫別而已。
當有人問她當作家與做官有什么不同時,她回答說:“剛開始涉足官場時,我覺得作家是荒野里的一匹狼,沒有羈絆,不需要與任何人相處。官員是猴子,猴子是族群社會,母猴要給小猴撓癢,小猴與小猴要打架,公猴之間要互相爭奪地盤。從狼變成猴子容易嗎?我覺得非常非常困難,困難得不得了,覺得身心俱疲。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產生了另一個比喻。我覺得作家是綿羊,官員是狼。綿羊純潔、天真。官員在權力的運作里頭,做成一件事往往要突破無數障礙,這就要有狼的戰斗性,看準別的動物的喉嚨就咬。從羊變成狼也是很困難的。最近,我覺得當作家和當官的區別是人變狼的過程。我現在屬半人半狼,也是蠻難受的。有人說龍應臺是否在抱怨?我認為不是的。因為什么都是咎由自取。講得好一點,是知識分子的任重道遠,是自己的性格取向而落了這么一個結合,這都是活該。從另一個角度看,我不后悔。臺北市的馬(英九)先生給了我這么個機會。我覺得自己從前的作品是在思索。現在是我在驗證自己的思索對不對。所有的羊啊、狼啊都有痛苦,都在給自己上課,使自己變得更深刻、更成熟。因此,我還是要感謝社會的寵愛。”
從文化人“變臉”為政府官員,日后必然會再從官員回歸為文化人,起初不少友人對龍應臺角色變換的成功感到疑惑,朋友們都擔心以龍應臺的文化人性格去當臺北市首任文化局長,怎么承受得了政治舞臺上諸多不可承受之重?有人預測,文人性格如此強烈的她,不出三個月就會陣亡下臺,李敖則比較“樂觀”,預測她只能做六個月。
“剛開始的過程真的很苦,不足為外人道也。那時候,自己一個人回到房間里痛哭一場的機會是很多的。”她幾乎已經忘了自己為公務哭了多少回,數都數不清。
政治人的思維和文化人到底不同。政治是不同利益群體的一種協調,要思考如何一碗水擺平,經常需要妥協,需要讓步,不可能什么都堅持。
以工作成果去任人批判
龍應臺剛入政壇時,幾乎整個臺灣都在看。情況也確實很艱難,臺灣有一句話叫“官不聊生”,當官越大越痛苦,臺灣現在民意高漲,官員實實在在是仆人,誰都可以指著鼻子罵。尤其是議會非常強大,每個議員都代表一大批選民,他們對官員簡直是頤指氣使。
龍應臺這樣描寫她接受市議員質詢時的情形:
就在這樣的一個陰冷寒濕、焦灼不安、而且荒謬透頂的冬夜凌晨3點鐘,我突然發現“龍應臺局長”被喚上了質詢臺。一個議員,剛從外面進來,似乎喝了點酒,滿臉紅通通的,大聲說,“局長,你說吧,什么叫做文化?”
對著空蕩蕩的議事大廳,臺北市文化局長說:
文化?它是隨便一個人迎面走來,他的舉手投足,他的一顰一笑,他的整體氣質。他走過一棵樹,樹枝低垂,他是隨手把枝折斷丟棄,還是彎身而過?一只滿身是癬的流浪狗走近他,他是憐憫地避開,還是一腳踢過去?電梯門打開,他是謙抑地讓人,還是霸道地把別人擠開?一個盲人和他并肩路口,綠燈亮了,他會攙那盲者一把嗎?他與別人如何擦身而過?他如何低頭系上自己松了的鞋帶?他怎么從賣菜的小販手里接過找來的零錢?
文化其實體現在一個人如何對待他人、對待自己、如何對待自己所處的自然環境。在一個文化厚實深沉的社會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茍且,因為不茍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別人——他不霸道,因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奪,因為不掠奪所以有永續的智能。
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積累的總和。
那微醺的議員事后告訴我,他以為我會談音樂廳和美術館,以為我會拿出艱深的學術定義。
我當然沒有,因為我實在覺得,文化不過是代代累積沉淀的習慣和信念,滲透在生活的實踐中。
這就是龍應臺,當作家時,心里有什么想法乃至委屈,還可以找文友宣泄一番,但當上文化局長后,最令她感到痛苦的是,即使有滿肚子的心里話,也找不著人傾訴。歸根結底,許多話都是不能和別人講的,痛苦和眼淚只能往肚里吞。
“真是非常苦。”提起這三年多來的酸甜苦辣,短短的五個字,道盡了龍應臺內心錯綜復雜的思緒和感受。
做政務官三年多的時間里,龍應臺封筆不作,停止評論。不是因為行程太忙,而是對權力另有思索。
三年筆不出“鞘”,是因為龍應臺希望謹守民主的游戲規則。她認識到:權力越大,責任越大,所可能辜負的人越多。權力大,而又不知謙卑的必要,一不留心,就是一個“以萬物為芻狗”的結局。
龍應臺說,作為知識分子,像是裁判;做掌權者的時候,像是球員。知識分子可以是瀟灑的,可以去批判,職責在于以文字影響思想、指出方向;當成為體制內握有實權的執行者,就完全不同了,必須是默默工作的人,而不是指點江山。一旦知識分子進到機制內做執行者,必須暫時放下知識分子的身份。如果想要用權力達到個人理想的話,必須變成一個忍辱負重、有耐心協調的
人。不能靠文章去宣揚自己,必須要以自己工作的成果去任人批判。這是必須的角色轉換。如果想兩者得兼,那就容易錯亂。
探出頭來的這個人
今年2月15日,一身黑衣點綴著橙色絲巾的龍應臺,正式上任臺灣“文建會主委”。龍應臺說這是“失去自由的第一天”。
生肖屬龍的龍應臺說,這次接任新職務前,曾反省當年擔任臺北市文化局局長時,沒能和市議會、媒體搞好關系是最大的敗筆。她反思自己曾經的“知識分子的傲慢”,自嘲“不食人間煙火,自視清高”。她說,此番重回江湖,一定會以最堅定的信念,用最溫柔的態度來達成目標。“為了讓文化建設回歸文化本質,我可以彎腰、低頭,甚至趴在地上。”
“做官,要達成一件事情,80%在于與人的協調上,這個基本道理我快到50歲才認識到。”龍應臺感慨。這次重出江湖,她的身段變得柔軟,她對“文建會”同仁說辛苦了,對歷任主委說謝謝啦,對其他部會說請幫忙,她拜會好姐妹、新晉“立委”張曉風,惜別時不忘送去飛吻……
對于未來工作重點,龍應臺說:“我最關心的是臺灣最基層、最草根的民眾,是否能和臺北市民一樣享有同樣的文化權。未來將穿著臟球鞋,全臺走透透。”
是的,龍應臺又回來當官了。龍應臺能否當好一個文化官員,有人樂觀,有人悲觀,就像龍應臺的文章和言論,有人喜歡,有人厭惡。
當然,也許更多的人喜歡龍應臺。龍應臺說,每個時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有些人追求時尚,不談政治,只關心自己的事情。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滾動著的車,總有人在里面自顧自地行樂。所幸的是,總有人探出頭來看看這輛車究竟跑在哪里。
而龍應臺,就是探出頭來的這個人。
(摘自《世界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