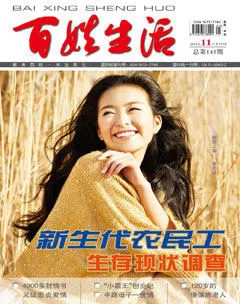社區的紅袖標
盧漫

1997年秋天搬入景陽胡同,第二年開春兒就戴起了紅袖標。景陽胡同1號院院長、胡同長、民間調解隊隊長……如今,77歲的陳祖蔭在北京東城區鼓樓苑社區身兼數職。
2012年6月的一天,記者跟隨陳祖蔭體驗了一回胡同巡邏。
巡邏:分辨小偷,一看眼神二看鞋
陳祖蔭77歲了,腿腳依舊利索。可一到治安巡邏時,他手里卻多了一根拐杖。他說:巡邏的時候萬一遇上壞人,這拐杖可以防身。
這天是星期一,又輪到陳祖蔭值班。吃完早飯,他戴上紅袖標,伴隨著拐杖“咔噠咔噠”的聲響走到胡同口,記者也來到這里,與陳祖蔭一道“站崗”。
景陽胡同的東口與南鑼鼓巷相連。早上8時的南鑼鼓巷,老北京味兒在巷子中彌漫。遛彎兒歸來的大爺大媽坐在胡同口,搖著扇子目送出門上班的兒女們。陳祖蔭站得筆直,不時和街坊們打聲招呼。
在胡同口值守了十幾分鐘后,陳祖蔭開始“巡查”胡同的每個角落。景陽胡同全長二三百米,共12個院子,整條胡同有250多戶人家。除了治安巡邏,陳祖蔭還要注意看胡同的衛生死角、院內堆放的雜物有無易燃物。
2號院一戶人家在院子里堆上了紙箱子、碎木頭,陳祖蔭敲響這戶人家的窗戶,半天沒人應。“這些都是消防隱患,這個事要記下來,回頭要給他們提個醒。”陳祖蔭說。
“分辨小偷,一看眼神二看鞋。”陳祖蔭邊走邊傳授起他的心得,“小偷眼睛亂轉,不穿皮鞋,愛穿跑著方便的平底鞋。”
陳祖蔭在景陽胡同生活了十幾年,這里的每一個角落都留下了他的腳印。身為胡同長,陳祖蔭熟知這里的每一個人,就連剛進駐負責裝修的工人,也和他熱情地打著招呼。
盡責:清掃垃圾,更新黑板上的提示語
兩個半小時的治安巡邏接近尾聲,陳祖蔭回屋拿起掃帚,清掃巡邏中發現的垃圾。在一個轉角處,他一手執掃帚掃地,另一只手快速地拔掉地上的雜草。
一個大院住著24戶人家,陳祖蔭每天都會清掃前院,隔幾天再給整個院來個大掃除。
放下掃帚,陳祖蔭沒有休息的意思,盯著院門口的黑板思索。作為院長,他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在黑板上寫些提示語或社區的通知,“這幾天附近的社區有治安事件,得給大家提個醒。”隨后,他從家里找來抹布和粉筆,將黑板上的字擦掉,拿出一根紅色粉筆,寫上“提高警惕”4個字。“紅色表示警示,這才能起到警醒作用。”陳祖蔭說。正文第一行,第一個詞是“防火”,紅色的;第二個詞“防盜”,陳祖蔭換上一根綠色的粉筆;第三個詞“防意外事故”,又成了黃色。“每個人感興趣的顏色不一樣,滿足各種人的習慣,才能給每個人都起到提示作用。”他說。
調解:大事小情已經記到第四本
大院對著大街的后門總是敞開著,陳祖蔭說,在社區居民的共同努力下,胡同很少發生治安事件,平日白天他家幾乎不曾閉戶。幾年前,景陽胡同還被街道評為“平安胡同”。
吃過午飯,鄰居范大姐上門反映情況。大院里的廁所還是老式公廁,離范大姐家最近。這兩天范大姐家裝修,女廁又沒有門,弄得如廁的女鄰居和裝修工人都很不方便。“這個廁所太老舊了,我打算開個居民會,大家投個票,決定這個廁所還留不留。”接待完范大姐,陳祖蔭從抽屜里掏出小本將這件事記下。
陳祖蔭說,他自從2006年當了民間調解隊隊長,時常有居民來家里反映情況。這些情況和事件處理進度,他都會記在本子上,已經記到了第四本。5年來,他處理過2000多件居民反映的情況,其中不乏鄰里矛盾糾紛。
“處理這些事會不會得罪人?”記者問道。“家里的玻璃被人砸過好幾次!”陳祖蔭的老伴兒李玉蘭大媽打開了話匣子。她說,老伴兒是個急脾氣,無論對誰說話從不拐彎抹角,有時處理問題時脾氣上來了,還和別人吵過架,不過后來和這些人都成了朋友。
背地里,李玉蘭當過好幾次“和事佬”,“不能人人都當大老虎,總得有人做綿羊,這日子才能過得好。”李玉蘭說。“我也知道自己有時有點沖,話要好好說,吹胡子瞪眼不管事。”陳祖蔭做起了“檢討”。
背景:退休前的工作經歷讓他愛上社區“那些事兒”
即使在家,陳祖蔭也不摘紅袖標。趁著午后小憩后的閑暇,陳祖蔭接過老伴兒懷中的小孫子,疼愛地輕拍著孫子的后背,對記者講起了自己年輕時的故事。
退休前,陳祖蔭曾在東城區某街道管委會當主任,主要負責所轄范圍內的交通、治安、衛生,這段工作經歷使他愛上了社區“那些事兒”。1997年,他家從樓房搬出住進景陽胡同,第二年他便加入了治安巡邏隊伍。
“大雜院,關上大門都是一家。”陳祖蔭說,人退休了,但心閑不住,總喜歡在胡同里轉轉看看。通過這幾年在社區里“摸爬滾打”,他原本內向靦腆的性格也變得外向了。每天走街串巷,忙忙碌碌,身體倒硬朗起來了。
又到了下午的巡邏時間,記者跟隨陳祖蔭來到另兩條他負責管理的胡同。黑芝麻胡同13號院,推門進去,四四方方的四合院,兩株參天的臭椿樹。陳祖蔭手扶樹干,抬頭仰望樹梢,深情地說:“多美的院子,多好的樹!”
從13號院后門出去,直走,又進入南鑼鼓巷,陳祖蔭繼續巡邏。此時,小巷人潮涌動,巷子里的小店鋪,樹陰下納涼的老人,騎著摩托的老外,在陳祖蔭巡邏的步伐下漸漸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