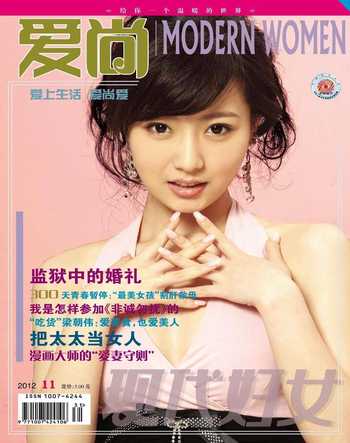22年辦學路
秦珍子
李小棚,鄉村免費幼兒園創辦者,1971年生,2012年8月27日逝世。
整個上午,我的電話一直在響。遠在西安的家人們罕見地集中打電話給我,他們張口便問:“還記得你寫的那個辦幼兒園的老師嗎?他死了。”
我怎會不記得。事實上,就在剛剛過去的端午節,我還收到了他發來的短信。和一年來一樣,這位陜西老鄉感謝我的報道讓幼兒園得到關注,祝我“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比起他,我離這個詞還很遙遠。
2008年,陜西藍田的山溝里,一家幼兒園掛牌成立。該園免費提供課本、學習用品,冬季免費供暖,不收取任何費用。全鎮13個村,這是唯一一家幼兒園。登記在冊的40多個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兒童。
在很多同鄉看來,創辦這家“藍橋幼兒園”的李小棚簡直“瘋咧”。他當代課教師,每月工資200元,拖著上學的女兒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妻子。家里3間土坯房,沒有粉刷,裂縫在墻上蜿蜒。
“咱窮,但精神很富有。”他始終在卑微的生活中努力昂著頭,仰望理想。這唯一的理想,便是讓村里娃和城里娃一樣上幼兒園,在4到6歲的“黃金年齡”接受早教。他說孩子們不一定要“成才”,但一定要“成人”。
我采訪李小棚時,40歲的他頭發花白,鞋上全是泥巴。見到我,他靦腆地笑著,帶著鄉音問:“路上還好走不?”
我與這個質樸的西北漢子對坐于幼兒園一角。粉藍相間的小桌子、小椅子包圍著我們。我順手往桌兜里一摸,摸出一把彩色蠟筆和幾冊印著童謠的課本。
他很想款待我,便拿出一袋核桃,叮叮當當地砸著,親手剝去硬殼。而我實在不忍,抓起一把塞入口中。他立刻面露喜色,仿佛受到了莫大鼓舞一般,講起自己的故事。
這不是李小棚第一次辦學。1989年高中畢業回鄉后,他痛心村里70多個學齡兒童無學可上,就要來村委會的3間倉庫,創辦了“六郎官小學”。
眼見校舍風雨飄搖,他又跑慈善機構,拉來資助幫學校蓋起了新教室。2010年藍田縣合并鄉村小學之前,他已輾轉4所學校,拉募捐、蓋校舍,而他的身份始終是一名“代課教師”。
省里慈善機構的辦事人員“怕了”這個在大雨里站上幾個小時的“愣頭青”。而許多裝車卸貨的打工者們也對“苦力老李”再熟悉不過。為了補貼幼兒園的支出,李小棚每到寒暑假就在西安打工。他凌晨開始干活,每天十幾個小時,累了就一頭倒在市場的水泥地板上。
“老師們的工資不能欠,”李小棚對我說,“城里娃們有啥,咱娃也要有啥。”他帶我參觀幼兒園活動室里的滑梯、蹦床,臉上閃現出難得的豪邁。
我想象不出,在這些色彩明麗的玩具背后,是多少個李小棚用肩膀扛起的暗夜。我更想不到的是,一年之后,這個媒體口中的“苦力教育家”,戛然停止了自己跋涉的腳步。
8月27日,剛從煤礦打工返鄉的李小棚早早便出發去縣城,給孩子們采購課本。他一整天沒舍得吃飯,跟同伴念叨著一周之后的新學期。
然而,在帶著課本返家的途中,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令他倒在了血泊中。
姐姐在領取他遺物時,拿到一紙染血的清單和一捆新書:語言、數學、拼音、常識、美術、音樂游戲。那是他給孩子們最后的饋贈。
車禍前,他曾打電話回家,山中秋意先濃,這個瘦弱的漢子“只想吃碗熱湯面”。
許多人前去送他最后一程,不少明星和無數網友在微博中轉發他的事跡:“人追求的東西決定了靈魂的高度,李老師一路走好。”藍田縣慈善會長也承諾,將設立“李小棚幼兒助學基金”。
而那個曾握住他粗糙雙手的我,只是呆立著,腦海里不斷浮現他剝著核桃的情景。在我看來,他就是一顆山里的核桃,身上布滿苦難留下的溝壑,卻仍用堅硬的殼,守護著豐盛的精神內核。
記得采訪結束時,我與他在山中走著,他捻一片草葉,癡癡望著公路盡頭。“我也有機會上大學。”他對我說。他喜愛《平凡的世界》,讀了好幾遍,直到“被書里的思想境界籠住了,再也轉不過來了”。
這便是他從未回頭、直至最后一刻的理想主義道路。
(摘自《中國青年報》)(責編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