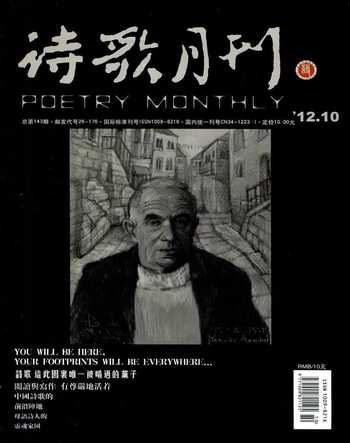刀的想法(外五章)
白月,女,1975年生,貴州人,現居重慶。作品散見于《詩刊》、《詩選刊》、《詩潮》、《青年文學》等,著有詩集《白色》。
說真的,蘑菇長得太故意了。
很難敘述它一條腿的意思和永遠戴著高帽子的心情……
這些動植物,它們,和我從未有過往來的它們,案板上的它們……
將在我的引導下作出讓人敬畏的事情,它們將在沉睡中蘇醒,接受現實的洗禮。
它們將變成段和片或是粉末……
不,它們已經變成段和片了。在我看到它們的時候……
我將用力地看著它們。用我全身力氣和精神。
我守在這里的目的,寸步不離的目的,睡和吃都在這里的目的……
就是等待它們。不,應該是等待段和粉末的成立。我渴望速度。我不喜歡停留、觀望和折磨。
盡管我這樣的存在就是一種折磨。
是在什么時候有了“段”和“粉末”的想法呢?饑餓一到就有了?
應該還要早,饑餓到來之前?不對,還要早。
對了。在早上,那時我比較清醒。我本來想好好休息一天的……
雖然我總是一副懶洋洋的樣子。我那沒心沒肺的樣子。我那副只作為工具而存在的樣子……
我的樣子就是讓它們變成段和粉末的樣子。
我在早上,更早時,甚至夢里……
不不不,我沒有夢。如果有過夢,我可能會改變想法。
即使不能改變我也會因為夢的存在而不樂意那么清醒:我是刀。
天生我材必有用。那么無論我做什么都是對的。
而我怎么就只能做“破壞”的事呢?
鍋里的油啪啪啪地響著,嘲笑起來:刀啊刀,多情的刀啊,應該自豪的刀。
我面無表情,像冰塊那樣躺著。假裝與它不認識。它懂什么呢?
它什么都不懂。什么都被我處理過了。
中午
狼吞虎咽后正經起來的中午
最后進入游戲的中午
什么也解決不了,早上解決不了,我解決不了,逃避解決不了,正視解決不了
反正解決不了,就不解決,我們就趴在地上
果然,太陽就趴在了地上
玩什么呢?什么都玩過。他玩過了,我玩過了
玩的不一樣最后都一樣了
都有氣無力了,水銀了;針尖了,毛孔了
緊張了。無人知曉啊
相信我吧,他說
什么證據都沒有,能不相信你嗎?
只剩下我了,能不相信你嗎?
找不到理由的中午,狂躁的中午,將自己打倒捆綁示眾的中午: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他說
我是他的助手,走在前頭:那是地獄么?
他板著午后的面孔說:啰嗦!
踏青歸來
美麗者占有了美麗。
快樂者占有了快樂。
幸福者占有了幸福。
興奮者占有了興奮。
忘我者占有了所有。
我牢牢記住的是自己,我回來,好像撿到了丟失的碎片。
好像這失而復得的碎片不是我的。我看到我像一堆待命的零件散落著。
沉默是一臺機器,正被運過來。
我聽到笨重的滾動聲——
我已逃避過。我不再逃避。那是空虛。
我愿活著但我已死去
現在去你那里的都是死了的我。
你還把我當活人看。我非常感激。
但我很清楚我已死去。
你無所謂我是活的還是死的,你要我陪著你。
于是我想我應該是活著的。
于是我使勁地想活過來。我笑了笑,發現臉上有塑料袋,想把它摘下。
但總是摘不下。
你說我的樣子是怕羞的樣子。
我更不好意思了,這樣的半死不活,又使勁笑了笑。
但又不能總是笑,塑料袋里空氣有限。
我就在塑料袋里看你吧。你又說我不好意思。
我是不好意思。卻不是你說的那種不好意思。
我本來已經死去卻要像一個活人,我已經很好意思了。
我是一點點一點點地死去的。我很不情愿一點點一點點地死去。
我是被迫死去的。第一次見你時我活著,第二次也活著,第三次第四次……
死之前我都活著,但一次比一次活得倉促。
我不知道我慌什么。
我活著,卻正在死去,從第一次到這一次。
回想一下,如果是真的,那一次次痛快就是一次次死。那么我是幸福地死去的。
那么我死得其所。
知道死不好玩,死去了就活不過來,可我還是心甘情愿地交出了我不好意思的心跳和不好意思的軀體。
活著多可愛啊,可以死去,而死,不能再活過來。死不好玩,死是哲學的。
活是受害者。我愿做個受害者,心怦怦的跳著,受害著,活著——
這應該是生命的意思。
也是你的意思,你不要不好意思。
活著吧,你活著,嘲笑我的死,即使我已死去。
徘徊的可怕
為了避免在夢里大喊大叫,我出來。
我出來了。翻過千山萬水般,翻著意識的跟斗。
但我發現夢外更適合大喊大叫,明晃晃的,到處都是鏡子和漏洞。
面對不真實的反光,更想去破壞。
但我不想與自己搏斗。
怎么辦呢?
蒙頭睡回去吧,但睡不回去。
要么在這邊要么在那邊。但兩邊都一樣。
兩邊都一樣,干脆我騎在墻上。
騎在刀刃之上。
我不叫喊,裂縫喊什么才好呢?讓裂縫兩邊去叫喊吧。
我親歷著,我沉默。我就是裂縫。
無聊者的繩索
我是在那些漂亮的花下面遛狗的。
大朵大朵的,一樹一樹的,紅的白的,那春天的花啊在我頭上開著。
落著,俯視著。
也在狗的頭上開著落著俯視著。左右都是花,我們被花圍著。
有鳥騰起小翅膀,“撲”一下,“撲”,黑一下就不見了。
飛,太快了。飛是一種可能,也是一種不可能。花也會飛。
可憐了會飛的花,變成了落。
我不會飛,狗也不會,就談不上可不可憐。
繩子可放三米長,也可只放兩米或半米。距離體現出一種尷尬美:
我抖一抖手,繩子也抖一抖,信息傳遞出去,狗兒就回來看我一眼。然后又跑開。隨便也將我拖出去。
昨天落過雨,沒用,今天又晴了。今天晴了,也沒用,明天又會落雨——
遛狗遛到無聊處,就自言自語起來。
我是在這些花兒朵朵們下面遛狗的。我穿過他們柔軟的手臂,繞過芳香的裙邊。
是的,我有點殺風景,大聲喊:回來回來。
繩子細細的身子奔跑著,使我和狗的距離奔跑著。
我真想抬頭認真看看那些花,白里透紅的,白里透紅著。冬天剛剛過去,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呵——
我忽然被猛醒的狗拉去撞了一棵樹,不好受。
忽然又被拉去撞了一下青色的瓷磚,這次很猛。我感覺更無聊了。但花兒們照樣開著。開在上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