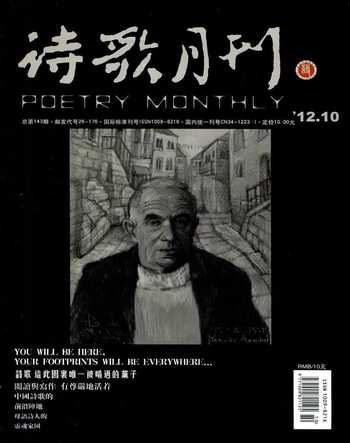用詩歌傳承伶仃洋畔的浩然正氣
廖令鵬
文化是流動的,包括歷史文化的縱向流動和地理空間的橫向流動,流動的文化是開放的文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談論地域性寫作,不難發現它除了具有內生性,而且還有外延性和共生性特點。西鄉處于伶仃洋畔,是深圳寶安區的一個具有悠久歷史和深厚文化積淀的海濱城鎮。改革開放以來,西鄉成為深圳經濟最發達、最富庶的強鎮之一。該鎮現居住150萬人口,其中大部分為外來人口,有很多作家在這里生活和工作。著名愛國詩人文天祥一曲《過零丁洋》,使伶仃洋畔揚名天下,浩然之氣、愛國之情、文采風流歷久彌新,西鄉,也因此具有了文化和歷史的厚重感,它為西鄉地域性寫作提供源源不斷的精神乳汁,這可謂其內生性文化。
在西鄉的地域性寫作中,詩歌占據了重要的分量。這里居住著眾多不乏在全國知名的詩人、作家,如精湛于中華古詩詞的鄒合全;現代詩歌創作與文藝評論俱見功底的著名詩人作家樊子;一直默默耕耘的艾樺、徐東、薛景山、黃剛;還有大家熟知的80后詩人李雙魚、在國內詩壇嶄露頭角的80后詩人蔣志武等等。他們融合共生,交流傳承,詩歌多元化特質明顯,人文底蘊濃厚,既傳承著中國古典文化血脈,又透露出開放、寬廣的海洋文化氣息。
鄒合全從80年代初到現在,在30多年間寫下大量詩詞作品,出版作品集《心履集》、《未遠齋吟稿》兩部。鄒合全的詩詞崇尚自然,主張有感而發、率性而為,反對刻意為之。他的身份是國家公務員,雖游走官場,疲于公事,慨嘆光陰虛度,但他內心堅守的是曇花那種韻格堅貞的高貴品質,以積極、真誠、陶然的心態面對人生。他游歷四方,抒發對祖國大好河山的贊美之情,寫下《謁布達拉宮》、《聽濤》《點絳唇·九寨溝觀瀑》等優美詩詞,其中“民安政教合,姻睦漢蕃融。日月知興替,千秋頌大同。”表現了詩人高尚的民族精神和渴慕祖國千秋大同的美好愿望。《五十虛度》則歌以詠懷,流露出來的是詩人秉本修齊、平和泰然的超脫境界。這些作品有漢詩風骨,一個最大的特點是真性情,熨合了現實生活中詩人的本真形象,所謂“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白居易《與元九書》)
雖然所選數量不多,但我們仍然能窺見鄒合全的詩詞,既重視內容之高雅,又講究形式之優美,努力在賦、比、興參酌使用上下功夫。古往今來,探討詩詞藝術美的著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鄒合全認為古典詩詞的魅力得益于藝術表現的形式美,如格律美、意境美、辭采美、含蓄美。大詞學家王國維說:“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可以看出,鄒合全的詩詞觀點與王氏一脈相承。因之,鄒合全能自如地運用古典的形式來表達其對現實生活的體驗與思考。他的很多詩詞,可以說既是古體的,同時又是現代的。
當今現代詩歌由于各種原因倍受詬病,有人認為是詩人自動放棄了詩歌。深圳是詩歌重鎮,涌現了許多實力詩人,他們并沒有放棄詩歌,相反,更加親近詩歌。樊子的詩歌近幾年引起詩歌界的矚目。他從2008年夏天 “移民”至深圳,對深圳的詩歌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是深圳詩人公認的事實。樊子步入中年,詩心濃烈,熱情好客,而對于詩歌,一直采取嚴謹的態度和內斂的姿態。他偏居西鄉,一邊經商一邊寫作。樊子的詩個人特質非常明顯,人生價值取向、精神風骨、氣質等很好地融入到詩歌當中。《身體特征》、《毒》這兩首詩歌采用嫻熟的排比、隱喻、象征等藝術手法,內斂冷靜的敘述節奏中,跳躍著灼人的火焰,讀后讓人熱血沸騰,如鳳凰涅槃重生。樊子的詩歌無論在布局形式和結構形式,還是在文本向度,都充滿某種內在、正直、獨立的精神力量。
艾樺的詩敏銳,練達,質地堅硬,這與他長期從事媒體工作是分不開的。《夜半回家》這組詩像紅外線燈光一樣,準確地向讀者傳達了詩人與所處社會環境的熱度與距離,以及詩人的內心準則,這何嘗不是一個時代、一群人的普遍生活狀況與生存理性之思。70后詩人徐東以小說著稱,從某種意義上說,徐東是一個詩人,他的小說是詩意的小說。這并非一個牽強附會的說法,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徐東就以詩人的身份,在《詩歌報》等主要詩歌刊物發表詩歌。徐東的詩自然灑脫,仿佛是“說”出來的,但并不妨礙詩歌的文本厚度。薛景山、黃剛兩位詩人非常低調,追求生活的質量與心靈的享受,他們的詩作數量不多,手法偏于傳統,意象經典,詩風輕逸,常常閃耀出哲思與人性的光輝,為西鄉詩歌的多元化增添了許多亮色。
西鄉詩歌創作團隊中,80后詩人是比較活躍的一群人。他們無不承擔著生存的壓力,但西鄉良好的文學氛圍極大的激勵著他們的創作,激發他們用詩歌的方式對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言說。李雙魚的詩歌安靜內斂,是西鄉詩歌一面獨特的旗幟。《黃槐》、《飛蛾》、《螢火蟲》這三首詩歌顯現出隨心所欲,真誠坦然的精神世界。從《黃槐》、《飛蛾》中的最后部分可以約略發現,詩人的慈悲和清凈就像飛來飛去的飛蛾、螢火蟲和蝴蝶,佛家的真諦和道家的超脫交相映襯,構成他詩歌中舉重若輕的古典山水詩特色,清新、唯美、飄逸、超脫。李雙魚把這種風格發揮到極致,感受深細,隨物賦情,使得詩歌彰顯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道家清靜世界,或者 “落花逐流水,騎驢過小橋”的超然脫俗的蕭散世界。
當然,蔣志武的詩歌也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他每年都有數量可觀的詩作在各雜志報刊上發表。他的詩歌鄉土氣息濃厚,感情飽滿,抒發了漂泊在深圳這座移民城市的那種眷戀故土的情懷。從他這組詩歌可以看出,蔣志武的詩歌文本仍然固守傳統,表達略顯生澀,還需進一步彰顯個性,彰顯伶仃洋畔的多元、開放、創新的文化特色。
地域中的寫作者必須強調自己語言中的個性與特性,文學創作必須融入異質獨特的東西,僵化的寫作并不可取。我們不能將簡單的地理特征、民俗風情、方言俚語、城市格局視為地域性的內涵,而應該真正理解地域與個體生命的關系,把握當地人們的性格與情感,所承載的歷史與文化等內容。西鄉文學是新都市的新海洋文學,西鄉詩歌也應有對應的文本特色,這就需要鄒合全、樊子、艾樺、徐東、李雙魚、蔣志武等詩人,以及其他眾多文學創作者,堅守個人詩歌特色的同時,發揚包容、開放的精神,在西鄉的地域版圖上樹起面向海洋,體現西鄉海洋文明、現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相融合的文明旗幟,律動時代的脈搏,飛揚生命的價值。
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