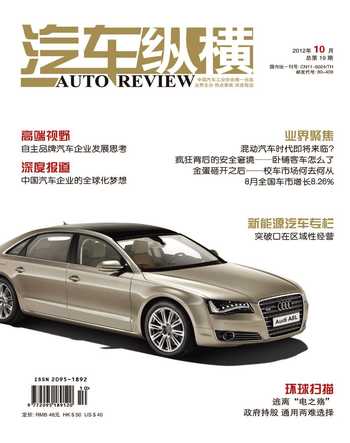親歷·轎車中國30年節選八


如果時光倒流,穿越回到2004年,你會做些什么?
李安定這段文字,讓今天的汽車人看到一些頗感眼熟的字眼:好日子走到“拐點”、銷量大幅下滑、降價競爭、庫存積壓……也因此文章結尾處提出“非得換個活法了”,企業應該苦練內功。今天看來,2004年的競爭似乎遠不夠“血腥”,至少其后中國汽車市場仍有五六年時間的高增長。
八年過去了,有些企業終于破繭成蝶,一些企業仍然被市場、被價格戰牽著鼻子走。
讀史使人明志。在悲觀、迷茫的時候,回望歷史,有助于明確自己的位置,找到前行的信心和方向。畢竟,還有明天。
盡管媒體和消費者像迎接節日一樣,涌進2004 年北京國際車展的展館,但是在剛剛過去的5月份,卻讓中國所有汽車廠商愁眉不展。在連續兩年增幅保持50%以上的中國車市,2004 年5 月份的總銷量下滑20% ,有的企業銷量下滑竟在30% 以上。全國轎車的庫存占到總產量的20% 以上。
當時,從央媒汽車版主編轉行汽車銷售經理人的孫勇最早對我說:“是‘牛市蓄勢盤整,還是好日子遭遇‘拐點,今天作出判斷似乎為時尚早;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不管什么樣的汽車,只要生產出來就能賣掉、就能賺錢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新車上市半年前,廠家的公關部門策劃一種概念,再經媒體一忽悠,消費者就揣著錢到專賣店排隊訂購,該是多甜美的好日子!中國人接觸汽車文明,被人為地推后了一百年,市場勢頭真是厚積薄發。有人統計,在第一批買車的老百姓中,60% 的人沒有打開前艙蓋看過發動機是什么樣子。
一個從零到“爆發”的汽車市場,各生產廠家饕餮著市場幾乎無盡的增量,從三五萬元的吉利、夏利,到應該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的1000 萬元天價賓利、勞斯萊斯,沒有一種車不是賣得火火的。坊間一則笑話說,您什么都不會干,那就賣車去吧。
正在遭遇全球“寒流”的國際汽車大廠商看得眼睛發綠,拼死拼活要擠進中國市場,合資生產,建銷售網絡,中國市場也給了他們超常規的回報。上海通用、廣州本田在規劃建廠之初,曾被外國媒體和投資分析家視為瘋狂之舉,今天卻成為國外母公司的搖錢樹;最早進入中國的大眾集團,在中國的盈利與產量竟支撐起大眾在全球的半邊天。國內過剩資本又何嘗沒有搭車發財的渴望,靠賣酒、造家電,生產手機電池發了財的企業,紛紛進軍轎車,來得早的也大都站住了腳,未來的規劃更是大得沒譜。
然而中國汽車市場的膨脹并非沒有盡頭,增量很快被吃盡,跑馬占地很快沒有了空間。
市場滑坡直接的原因似乎并不難找:經濟軟著陸帶來的購車貸款緊縮,擋住了一部分購買力;加入世貿組織六年的保護期臨近結束,老百姓持幣觀望車價和國際接軌;大城市轎車的購買力已經逐步釋放,而新一輪中小城市市場沒有未雨綢繆地得到開拓……
車市正在“拐點”來臨的恐慌中。6 月16 日夜,大眾在中國車市突然扔下一顆“重磅炸彈”,大眾中國公司攜手在華的兩個合資伙伴--一汽大眾、上海大眾,對其大眾品牌產品全系降價。一場殘酷的、你死我活的價格戰在中國全面打響,競爭從此變得血腥。
大眾那兩年自持于自己的產品好、市場大,曾經高舉“絕不降價”的大旗,為此在中國消費者中間變得不受待見。大眾的高層接受中國媒體采訪,一聽降價的問題,就斷然頂住,因此“免談降價”成了大眾中國市場的一個“死結”,北京話叫“認死理兒”。盡管大眾在中國市場一度占到半壁江山,當時也還占31% 的市場份額,有幾分“死扛”的資本。然而,加入世貿組織后,跨國公司全進來了,不再是當年大眾一花獨放的時代,別人的車便宜、質量好,老百姓自然舍你而去,“死扛”豈不必然“扛死”。大眾腦筋終于活絡了,覺悟得還算及時。尤其,借成為北京奧運會合作伙伴的契機,“回報消費者”這個臺階也下得不錯,又搶占了先機。
大眾此次降價聯合了兩個合資伙伴,形成了集合優勢,且不是單個產品的單打獨斗,系列全線降價,如此大的市場份額,對市場的沖擊力不可低估。中國車市真正意義上的“價格戰”從此翻開新篇章。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中國汽車存量市場的爭奪,從此進入“你死我活”的新紀元。什么叫“大鱷”?什么叫“殘酷”?恐怕將會給所有中國汽車廠家上一課。
新掌門和新產業政策
2004 年前后,中國汽車企業的領軍人物已經全面實現年輕化。三大集團的一把手,分別由一汽的耿昭杰、東風的陳清泰和馬躍、上汽的陸吉安和陳祥麟交棒給竺延風、苗圩、胡茂元,當時三人都是不惑之年,被稱作“三少帥”。其他國企集團也分別由奇瑞的尹同躍、長安的尹家緒、廣汽的曾慶洪、北汽的徐和誼接掌。八大合資企業接手中方總經理的分別是上海通用的陳虹和丁磊;上海大眾南陽和陳志鑫;一汽大眾秦煥明和安鐵成;神龍的劉衛東;東風和日產任勇;廣汽本田符守杰;長安福特鄒文超;北京現代郭謙和李洪爐。
加入世貿組織和鼓勵轎車進入家庭,催化中國汽車產業加速了結構調整,從過去計劃經濟的“活化石”,轉化為一個最深度競爭的市場化產業。十年前的一版《汽車工業產業政策》已經明顯跟不上形勢。2004 年 6 月1 日,由新組建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布了新一版的《汽車產業發展政策》,頗有許多與時俱進的地方。
新產業政策取消了與世貿組織規則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所做的承諾不一致的內容,比如取消了外匯平衡、國產化比例、出口實績等要求;大幅度減少了行政審批的規定,轉而依靠法規和技術標準引導;首次提出了品牌戰略、鼓勵企業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提出引導企業兼并、重組,促進企業集團做大做強;要求企業改變過去銷售上的粗放方式;鼓勵發展能源環保型汽車和新型燃料汽車。
這些條文,外行人看上去有些籠統、有些枯燥,但是對照其后數年的實踐,中國汽車業發展的大方向和大事件,大都沒有跳出這些條文的框架。一個好的城市規劃,恰恰在于不用年年改、月月改,如同美國芝加哥的城市發展還在嚴格執行50 年前的經典規劃一樣。
存量競爭:非得換個活法兒了
2004 年中國汽車產業增長將近20%,轎車增幅只有13% 。雖然在全世界也算獨占鰲頭,但是大多數汽車廠家、經銷商、零部件供應商的實際感受卻是另一番滋味。尤其到了第三季度增幅跌到1.9 %。
火爆的車市還會再來嗎?有研究報告預測,下一輪熱銷行情可能出現在兩年后的2006 年。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在專欄中提醒企業:要健康地成長,恐怕得苦練內功,換個活法兒了。
全球汽車大集團蜂擁而至,轎車生產能力空前的大增長,迅速超過市場的消費能力。雖然“買方市場”突然到來,生產廠商仍然在大干快上。中方壓產量為政績,外方壓產量為彌補全球虧損。
爭奪有限的市場,各品牌普遍的對策就是降價,而且降價的頻率和幅度越來越大。汽車降價本來是中國老百姓最企盼的事情,可是許多人在剛剛買車的第二天,就趕上新一輪降價,一夜喪失一兩萬,懊惱窩火可想而知。廠家都想用降價擠占別人的蛋糕,一輪輪價格戰打下來,蛋糕還是那么大,利潤減少了,服務跟不上,消費者愈發不買賬,市場信心喪失,形成惡性循環。
對所有中國汽車廠商來說,真正的挑戰不是誰的降價幅度更大,而是要以更快的速度降低制造成本。在中國生產轎車創造的驚人高利潤,當時并非來自低成本。大眾汽車進入中國20 年,最輝煌的時候每輛桑塔納掙得2 萬元,相當于大眾集團全球平均利潤的兩倍,這顯然得益于中國關稅壁壘保護下,遠遠高于國際市場的轎車價格。如今,各廠家價格一跌再跌,高利潤還能維持多久?中國汽車業也開始討論起零利潤競爭了。
加入世貿組織的“保護期”行將過半,中國汽車業嚴酷的現實是,降轎車價格易,降成本難。在勞動力成本上,盡管中國要比日本等國便宜80% ,但是,采購、生產、管理的成本居高不下,合資企業在中國造車要比國際平均成本高出兩三成。其中,零部件采購成本比國際平均高出50% ,制造成本是國際的兩倍,日常運營成本是國際平均水平的八倍!
此外,明顯滯后的汽車消費環境,如能源、道路、停車場承受能力被壓得喘不過氣,哪能容得轎車“狂飆突進”式的增長單兵突進。如果一個城市的道路擁堵得如同一個大停車場,難道還會有人去買車嗎?
就像有經驗的老農種麥子,不是一開春就讓麥苗大水大肥地瘋長,而得有一個“蹲苗”的階段,讓麥苗長得更健康、更壯實。經過這次“蹲苗”,聰明的汽車廠家開始從上產能、拼價格,轉而向重市場、降成本求生存。但是好日子再也不會不加選擇地落在每一個汽車企業身上,“跑馬占地”式粗放的增量競爭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此消彼長”的存量競爭將變得無情。在不斷優勝劣汰中,有進有出,有死有生,競爭從此成為一種常態。
2005 年,中國轎車年產量276 萬輛,增幅為20%;2006 年,轎車產量387 萬輛,增幅為40% 。中國汽車產業終于安然度過加入世貿組織后的緩沖期,站穩了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