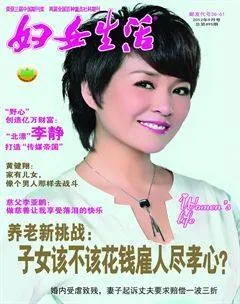養(yǎng)老新挑戰(zhàn):子女該不該花錢雇人盡孝心?
編者按:
孝敬父母是子女的義務。然而,隨著獨生子女越來越多、人口流動越來越頻繁,空巢老人也不斷增多,做兒女的要想在老人跟前盡一份孝心,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有些人身在外地或工作忙碌,難以抽出時間回家看望父母,甚至過年過節(jié)也不能回家和老人團聚。無奈之下,有的人別出心裁,花錢雇人代替自己盡孝心。于是,在一些地方興起了一種所謂的“代孝”業(yè)務——子女出錢,請人上門服務,為老人提供陪吃、陪聊、陪過節(jié)等各種“孝心”服務。對父母進行精神贍養(yǎng),既是道德的要求,也是應盡的法定義務。可做子女的不親力親為,而是用金錢雇請他人代替盡孝心,這種買賣方式老人們心理上是否接受,是否符合情理法理?現(xiàn)代人又該如何應對精神養(yǎng)老難題?
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飯
趙本山、宋丹丹合作的小品《鐘點工》,說的就是兒子花錢請人陪父母聊天的故事。這樣的故事并非杜撰,在現(xiàn)如今的生活當中,就真有不少人由于工作忙,或者沒跟父母住同一個城市,很難做到經(jīng)常回家探望老人,不得不花錢雇人陪老人聊天。
張旭是湖南益陽人,多年前離開老家來長沙做生意,經(jīng)過艱苦打拼,如今家底殷實、生活富裕,在長沙安了家。為此,張旭把年邁的母親從益陽鄉(xiāng)下接到長沙一起生活。可是,由于張旭和妻子要忙生意,無暇陪伴母親。老人每天除了看看電視,到樓下的花園里散散步,其余時間就只能獨自守著空蕩蕩的房子發(fā)呆。老母親多次鬧著要回老家。無奈,張旭只好去家政公司雇了一個人來陪母親聊天。
張旭雇的陪聊人員譚大姐,是一位來自長沙市郊的中年婦女,她性格溫柔,善解人意,能說一口地道的長沙話,與張旭的母親交流起來十分投緣。除了陪聊天,譚大姐還負責為張旭的母親做飯、料理家務,張母很滿意,從此再也不像過去那樣唉聲嘆氣,鬧著要回老家了。
記者了解到,像張旭這樣由于工作忙沒時間,或是在外地工作離父母太遠的子女,有不少出錢請人陪父母聊天的。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代孝”需求,一些家政公司除了提供月嫂、保姆、護理工及家教以外,還多了一項“陪聊”服務。長沙某家政公司趙經(jīng)理說,他們推出“陪聊”服務以來,已占到老人家政服務量的三分之一,“陪聊”的服務對象基本上都是身體健康、日常起居不需要幫助的老人,“陪聊”人員月工資1500元左右,雇主還管吃住。
俗話說,人多吃飯自然香。一個人吃飯,哪怕是山珍海味也會感到索然無味。現(xiàn)實中,很多子女不在身邊的單身老人,經(jīng)常是一個人吃飯。為此,有的子女就想了一個辦法:請人陪老人吃飯。
徐大伯的兒子兒媳在廣州工作,老伴去世后,他一個人獨居長沙。作為大學退休教師,他每月有養(yǎng)老金,還有醫(yī)療保險,生病住院可以報銷,可以說是衣食無憂。可是物質(zhì)生活上的富足卻怎么也填補不了徐大伯精神上的空虛。“我最希望的是能有人陪我一起吃飯。”徐大伯跟兒子兒媳說出了心里話,他說一個人吃飯沒意思,再好的菜,他每餐也只能吃半碗飯。聽了父親的話,兒子兒媳覺得自己不能經(jīng)常陪父親一起吃飯,心里有愧,于是就找到家政服務人員小汪,請她在為父親提供家政服務之外,再陪他一起吃飯,每月增加500元工資。小汪滿口答應。小汪的飯菜做得可口,還陪著徐大伯一起吃,邊吃邊聊天。這樣一來,徐大伯每餐飯都吃得很香,心情也開朗了不少。
雇人陪父母過節(jié)
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春節(jié)期間,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會回家陪父母過年。可對于哈爾濱市的李玉老兩口來說,這個愿望多年來都成了奢望。李玉老兩口70多歲,兩個兒子都在國外,已經(jīng)有三四年沒回家過春節(jié)了。左鄰右舍過年都是團圓歡喜,只有李玉家沒有任何歡樂氣氛,老兩口四目相對,茶飯無味。雖然兒子兒媳每年從國外寄回的錢物不少,可是老兩口還是悶悶不樂,感到生活沒有意思。
今年春節(jié)前,兩個兒子給李玉老兩口打來電話,說再也不能讓爸媽像過去那樣孤單寂寞地過年了。雖然他們?nèi)圆荒芑貋恚尲依餆狒[起來,說要雇人到家里來陪爸媽過年。盡管兩位老人嘴上推辭,其實心里還是很希望有人來陪他們一起過年的。
果然,兩個兒子委托朋友幫父母物色了人選。前來陪伴李玉老兩口的是一對來自農(nóng)村的張姓中年夫婦。張姓夫婦平時就在李玉家附近的農(nóng)貿(mào)市場做點小生意。由于父母都不在人世,他們也不需要回老家過年了。張姓夫婦從臘月二十九就帶著孩子搬到李玉家。兩家商量好,從臘月二十九到大年初六,一直在一起過,價格1000元,正月十五另算。大年初三那天,張姓夫婦陪李玉老兩口玩撲克,他們3歲的孩子在旁邊不停地叫李玉老兩口爺爺奶奶。李玉說,好幾個春節(jié)家中都沒有笑聲了,今年春節(jié)過得最高興。
除了工作繁忙,現(xiàn)在的獨生子女結(jié)婚成家,逢年過節(jié),夫妻雙方要面臨回哪個父母家的兩難選擇。遼寧大連的章岐夫婦,雙方父母都70多歲。過去幾年,雖然夫婦倆輪流在兩個家過年,但每年總還是有一方父母沒有人陪伴。去年春節(jié)前,想到老父親又是一個人,章岐早早就到家政公司雇了一個保姆——48歲的楊女士,請她在春節(jié)期間幫父親做飯,陪他聊天說話。
除夕前一天,楊女士就來到章岐的父親家,幫他拖地、擦桌椅。看到天氣晴朗,楊女士又主動幫助章岐的父親把床單、衣服洗了曬干,將床鋪鋪好,還根據(jù)老人的喜好,幫他準備了年貨。
除夕那天,楊女士早早來到老人家里準備飯菜。傍晚時分,一盤熱氣騰騰的餃子端上了桌,同時,還有各種豐盛的菜肴。平日里,章岐的父親都是自己湊合著吃飯,很少吃到這樣色香味俱全的可口飯菜。老人一邊吃一邊夸楊女士的手藝好……
吃完飯,楊女士洗刷完畢,準備離開。章岐的父親說:“等會兒看完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再走,你陪我聊聊天吧。”楊女士點頭答應了。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開始了,他們邊看邊聊,就像一對父女。不知不覺就到了零點時分,楊女士連忙雙手作揖,向章岐的父親拜年。老人連聲道謝,心里樂開了花。此時,章岐和妻子以及他們的小兒子也打來電話拜年、問好。老人手握電話,滿臉堆笑地回答:“有人陪我過年,我一點也不寂寞,高興著呢!”
子女該不該花錢買孝心?
子女雇人代替自己給父母盡精神贍養(yǎng)義務,雖然是無奈之舉,但這種孝心買賣會不會異化孝道的原意,顛覆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道德?花錢能不能買來真正的孝心?
支持方
呂慶懷(男,報社退休編輯):當今社會,無論從時間、空間還是個人精力上來說,都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子女對父母盡精神贍養(yǎng)義務。子女要忙工作、創(chuàng)業(yè),還要養(yǎng)育年幼的孩子,加上沒有和父母住在一起,能否花很多時間去照料陪伴年邁的父母,這得打一個問號。盡孝心是中國的傳統(tǒng)道德和法定義務,但到底該怎么做,沒有一個統(tǒng)一的標準。子女花錢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飯、過節(jié),這種“孝親代理”,不失為一個解決精神贍養(yǎng)難的好辦法,應當支持。
陳春仁(男,湘潭大學社會學教授):子女花錢雇人陪父母聊天、吃飯、過節(jié),雖然把精神贍養(yǎng)商業(yè)化了,有買賣孝心之嫌,但這樣的“代孝”確實給兒女提供了方便。我認為,不管采取何種形式,只要事實上盡了孝心,即便不能親力親為,也未必就會影響親情傳播。恰恰相反,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里,公眾選擇表達孝道的方式也需要多樣化。多樣化的表達方式,讓不同的人群以最適合自己的方式來表達孝道,既是對孝道最有效的傳承,也是社會的進步。如果拘泥于迂腐的、單一的孝道,譬如死守“父母在不遠游”的古訓,反而讓自己勉為其難,使盡孝成了一種負擔,更不利于孝道的發(fā)揚光大。
李芳(女,家政服務公司經(jīng)理):“常回家看看”,唱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在忠孝難兩全的情況下,請人“代孝”也未嘗不可。其實,“代孝”自古就有。古代將士征戰(zhàn)沙場、秀才赴京趕考等外出較久時,常常委托至親好友代為盡孝。過去請人代為盡孝,大家多少都有些時間,而且這種禮尚往來還有助于增進感情。現(xiàn)在,你忙,我忙,大家忙,且大部分人都是獨生子女,在左右為難的情況下即便想請親友代孝,也勉為其難。商業(yè)化的“代孝”,恰恰滿足了這種需求。花錢雇人代替自己行孝,其實也是與時俱進的體現(xiàn)。
反對方
張艷(女,律師事務所律師):子女花錢雇人代替自己行孝,固然是無奈之舉,但這種用金錢買來的孝心,并非長久之計。有個眾所周知的廣告:下班時分,一位老太太做了一大桌飯菜等待兒女們回來,結(jié)果接到兒女們一連串電話,每個人都在電話那頭說忙,不能回來。最后老太太只能面對一桌熱氣騰騰的飯菜,孤單地拿起筷子……這時,如果有一個代孝公司的人上門陪老太太吃飯,也許能夠暫時緩解一下老太太的心情。然而,陪吃飯的人一走,老太太還是會陷入孤單寂寞。這說明花錢雇人代孝只是臨時之舉,親力親為才是兒女盡孝的本分,孝心無人能夠代替。
楊洲(男,某托老所經(jīng)理):子女因各種原因,花錢請人陪父母聊天、吃飯、過節(jié),未嘗不可。但這種“代孝”模式一旦升級為產(chǎn)業(yè),孝心成了可以用金錢買來的商品,親情將被異化。常聽說在一些高檔的養(yǎng)老院里,設施齊全,護理精心,價格不菲,但老人被送進去之后,卻再也不見兒女來探望。也許兒女們認為,自己花錢請人代為照顧父母已經(jīng)是在盡孝,但他們真的懂得老人的心嗎?老人們最期待的時刻就是兒女探望之日,那種快樂是別人無論如何也給不了的,哪怕是一分鐘,他們都會滿足。
劉軍紅(女,老齡化問題專家):當代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物質(zhì)繁榮,老人們溫飽不愁。在這樣的情形下,孝心的內(nèi)涵更多的應該是子女對父母的尊敬、關(guān)心和體貼,更多的應該是精神意義上的給予。子女花錢請人陪父母聊天、吃飯、過節(jié),雖然解決了行孝的一時之難,分擔了一時之憂,卻不能完全代替兒女對父母心理上的慰藉。老人需要的是兒女的陪伴和問候,而不是金錢買來的替代品。
劉一禎(女,中國敬老形象大使、空政文工團青年歌唱家):可憐天下父母心。撫養(yǎng)兒女,做父母的總是忘我地付出,而兒女報答父母,則很難做到忘我。哪怕是兒女對自己不孝,父母也總是處處為他們找說辭,不愿兒女背上不孝的名聲。其實,許多做父母的,并不需要兒女天天守著自己,只盼望兒女一個關(guān)愛的電話、一句暖心的問候,來溫暖他們的心靈。但是,今天有許多做子女的總是以“忙”為借口來推辭盡孝的本分,孝之美德往往被一個“忙”字遮掩。雖然時代在變,但流淌在炎黃子孫血液里的孝道不能丟,它呼喚每一個做子女的孝心至上,“常回家看看”。
精神養(yǎng)老難題如何破解?
老齡化、城市化、獨生子女、空巢家庭……各種社會現(xiàn)實使得老年人的精神養(yǎng)老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這個社會難題,并非簡單地花錢就能解決,而是需要家庭、社會以及老年人本身共同努力來解決。
其一:進一步完善社會養(yǎng)老體系建設。老年人的生活狀況如何,直接反映一個國家、一個地區(qū)和一個城市的綜合發(fā)展水平和文明進步程度。解決空巢老人的精神養(yǎng)老問題,不能單靠子女,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進一步完善各種社會養(yǎng)老體系,減輕家庭養(yǎng)老的負擔。
一方面,要拓展養(yǎng)老服務業(yè)務范疇,要從空巢老人的實際需要出發(fā),更多地發(fā)展醫(yī)養(yǎng)結(jié)合和有心理慰藉服務的養(yǎng)老院、托老所以及建立社區(qū)老年食堂,由政府出資建設或采取民辦政府財政補貼的方式。這樣,既滿足了老年人的精神養(yǎng)老需求,又能減輕子女的經(jīng)濟負擔。
另一方面,要加快為老組織建設。雖然有的家政公司有陪聊、陪吃飯、陪過節(jié)等為老服務項目,但收費不低,子女負擔較重。建議街道、社區(qū)統(tǒng)一建立陪聊隊等義工組織,免費上門陪空巢老人聊天、吃飯、過節(jié),給他們送去歡樂,幫他們排解孤單寂寞。
再一方面,要建立鼓勵子女對長輩盡精神贍養(yǎng)義務的規(guī)章制度。目前,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將孝道作為衡量公民價值的標準之一,一條條措施正不斷制定,比如《老年人權(quán)益保護法》修訂草案規(guī)定,子女必須“常回家看看”。開建公務員信用檔案中,尊老將成為公務員晉升評先的重要依據(jù)。有的地方政府規(guī)定,每逢父母、岳父母過生日,黨政干部必須休假一天陪伴長輩。
其二:空巢老人需充實自己的精神生活。健全的社會化養(yǎng)老體系,給空巢老人提供了精神養(yǎng)老的條件。但要想晚年不再孤單寂寞,還得培養(yǎng)自己的興趣愛好,積極參與社會活動,老有所樂,老有所為,充實自己的晚年生活。
其三:子女應多抽時間陪伴父母。“衣食無憂,內(nèi)心孤獨;兒女雙全,無人交流。”有人用16個字概括當今老年人的尷尬處境。不少兒女在外地甚至海外工作學習,因為客觀條件限制,回家陪伴父母的時間非常有限。即使一些與父母住在一起的兒女,也因為工作忙而無暇照料父母。有一位白領計算了自己每年回老家陪伴母親的時間:以每年只能在春節(jié)回一次家為例,7天假期,真正在家時間不超過5天,除去聚會、應酬、睡覺、吃飯、購物的時間,真正陪伴父母的時間大概只有24小時。假設母親今年55歲,能活到85歲,以后30年在母親身邊的時間最多也就720小時,不超過一個月的時間。統(tǒng)計資料表明,目前全國有2340萬名空巢老人需要照料,只有10.39%的子女能滿足老人的精神需求。
面對如此殘酷的現(xiàn)實,有的子女花錢請人為父母盡精神贍養(yǎng)義務,也許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但這并不意味著子女只要花了錢就算是盡了孝心。社會化養(yǎng)老做得再好,老人再想辦法充實自己的精神生活,也比不上兒女的一聲問候和近在咫尺的陪伴。精神養(yǎng)老作為家庭養(yǎng)老的一項重要義務,子女無論如何也不能以各種借口放棄。
濃濃的親情是老人們晚年生活的快樂良方,精神養(yǎng)老不可能完全被金錢取代。在外拼搏的游子,不管工作有多忙,也要擠出時間回家看望一下父母,或抽空給父母打個電話,報個平安,不要借口忙而忘記盡孝。其實,老人并不需要兒女有多少錢,當多大官,有多大名氣,他們只希望自己的兒女能夠平安、幸福。
〔編輯: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