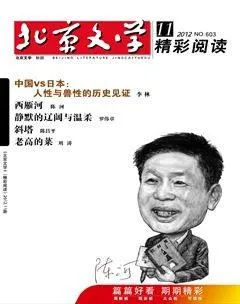風景里的記憶創傷(創作談)

我的家鄉溫州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最有名的風景地大概算是雁蕩山了。在本地人的眼里,雁蕩山其實有好幾座。除了天下聞名的樂清北雁蕩山,在甌海、平陽等地還有南雁蕩和西雁蕩山。那幾個山氣勢略小一點,但風景同樣秀美,有清澈的溪流匯流成河穿行其間。80年代的中期,我有一次前往平陽的水頭鎮,那里就是西雁蕩山所在地。令我想不到的是,這個傳說中的風景地籠罩在一股濃重的臭氣之中,河流成了制作皮革的漂洗池,河水發黑,河灘和路邊灌木上到處晾曬著皮張,小鎮上是一間間的皮革加工場。那一次的經歷像是一個噩夢,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那個時候,商品經濟的改革剛開始起步,整個社會都在無序中痛苦地嬗變。那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變革年代,無序而令人激動。一部分人開始了原始的資本積累,長期建立的生存平衡被打破了,包括人和自然的關系。在差不多的時間里,我在報章上看到一宗父親槍殺兒子的案件,父親是個老革命,因為看不慣兒子退伍回來后不務正業而槍殺了他。這件血案并不是發生在西雁蕩,但我無法遏制地把它和西雁蕩受傷的風景聯想到了一起。而且,還扯上了西雁蕩的歷史背景,這里原來就是紅十三軍的活動地盤,算是革命老區。在后來的很多年的時間里,這個故事在我的腦子里揮之不去,我以那個峽谷為背景,讓那血案里的人物逐漸復活。那是一次真正的虛構,我沒有山區的生活經驗。我把一個當兵時的戰友想成是主人公,把自己的想法、感覺、幻想和欲望都加到了他的身上。我把父親的角色當成了樹木河流自然權威的象征,那個漂泊的女孩子白雨萍則象征了一種渴望獲得改變和前進的力量。我覺得這個封閉的山區故事里,似乎包含著一種古希臘神話般的寓意,我企圖把這寫成一個寓言式的故事,有一段時間腦子里整天想著這件事。但是這個故事還沒寫成,我就在90年代初出國了。
我在海外一晃就將近20年了。這是個漫長的時間。我還記得剛出國時還從CNN電視里聽中國的三峽水庫論證問題,而現在有的小孩都以為三峽水庫是古老建筑了。中國在這段時間里變得很工業化了,同時在環境上也付出了巨大代價。我現在每次回國都遇到很大問題,會因空氣不好導致氣管過敏嚴重咳嗽。因此,對于國內的環境保護問題我會深切地關注。
2009年在西安開筆會時參觀了浐河灞河的新開發區。在一個水清林秀白鷺紛飛的三角洲,聽講解員說這里原來是堆積垃圾的地方,曾經是臭不可聞。現在在我們的腳下還是一些永久性的污染土地,他們是用一種先進的德國公司技術對這些土地進行了永久性的封閉。那一次的參觀讓我印象深刻,覺得中國隨著經濟實力加強,早晚會去治理環境。只要投入足夠的金錢,那些被破壞的自然環境是可能恢復到原來的模樣。外國的經驗也是這樣,倫敦原來就是被煤炭的煙霧籠罩,現在不是也藍天白云了嗎?然而,有些東西是無法復原的。就像浐河灞河邊那片土地下面的污染,只能封存,不能徹底清除。
雖然生活在森林和淡水資源特別豐富的加拿大,我當年曾經寫過的西雁河故事一直還潛伏在心間,今年某一天又浮上了心頭。我再次回到那段記憶,有恍然隔世之感,但覺得西雁河山谷發生的故事還是讓我激動不已。于是,我終于把這個老掉牙的故事寫出來了。故事的結尾我讓西雁河重新變得清澈如昨,只是記憶的創傷是永久存在的。
責任編輯 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