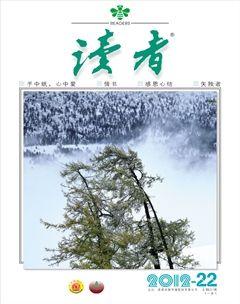手中紙,心中愛
劉宇昆
當我用英語說“愛”字的時候,感受到的是聲音,但是當我用中文說“愛”字的時候,感受到的是真情
一
我最早的記憶是兒時的一次哭泣。那次,不管爸爸媽媽怎么哄,我就是不搭理,一個勁兒地哭。
爸爸拿我沒辦法,只好任由我在臥室里哭。媽媽卻把我抱進廚房,將我安置在餐桌旁坐好。她從冰箱上面抽出一張彩色包裝紙,想吸引我的注意:“瞧瞧,這是什么?”
每年圣誕節過后,媽媽都會將各種圣誕禮盒的包裝紙小心翼翼地裁剪下來,整齊地疊放在冰箱頂部。幾年下來,包裝紙積了厚厚一沓。她拿出其中一張,正面朝下反面朝上,平整地攤在桌上,給我疊小玩意兒。折、壓、吹、卷、捏……不一會兒,這張紙就在她指尖消失了。她輕輕一吹,一個被壓得扁扁平平的紙模型瞬間變得栩栩如生。
“瞧!小老虎!”她邊說邊將手中的紙老虎放到桌上。它個頭不大,和我兩個拳頭加起來差不多,白色虎皮上點綴著紅色糖果和綠色圣誕松。
我接過媽媽手中的小老虎,既驚又喜,用食指摸摸它的后背,小東西連蹦帶跳。
“這叫折紙。”母親用中文告訴我。
那時我對折紙一竅不通,但我知道媽媽的折紙術神奇無比。只要她輕輕一吹,這些紙玩意兒便可借助她的氣息活蹦亂跳起來。這么神奇的折紙術只有她一個人會。
爸爸是從一本冊子里挑中媽媽的。記得有一次,正在讀高中的我向爸爸詢問其中經過時,他很不情愿地說起。
那是1973年的春天,爸爸想通過婚介所找個對象。他漫不經心地翻閱著介紹冊,每一頁都瞟上一眼,直到他看到媽媽照片的一剎那。
“我從未見過那種照片。”爸爸說。照片里,一位女子側身坐在藤椅上,她身著絲質的緊身綠旗袍,雙眸視鏡,一頭秀發優雅地垂在胸前,依于肩側,孩童般的雙眼透過照片,盯著爸爸。
“自從看到她的照片,我就不想再看別人的了。”爸爸說。
冊子上說,這名女子芳齡十八,愛好舞蹈,來自香港,英語流利。但這些個人信息沒一個是真的。
后來,爸爸開始給媽媽寫信。在那家婚介所的幫助下,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系。終于,他決定親自去香港看她。
“她根本就不會說英語,我收到的信也都是婚介所以她的口吻代寫的。她的英語完全停留在‘你好‘再見的水平。”
究竟什么樣的女人會把自己的信息像商品一樣放到冊子里,并期待別人把她們買走呢?那時我還是個高中生,輕蔑鄙視之情油然而生。
爸爸沒有因為受騙而闖入婚介所要求退費賠償,相反,他帶媽媽去了餐廳,找來服務生給他們做翻譯。
“她怯生生地看著我,眼神中透著幾分害怕和期待。當服務生開始翻譯我的話時,她臉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爸爸回到康涅狄格,為媽媽辦了入境手續。
一年后,我出生了。那一年,是虎年。
只要我想要,媽媽就會用彩色包裝紙給我折各種各樣的小動物——山羊、小鹿、水牛等等。在我家客廳,這些小動物隨處可見,而老虎則咆哮著四處追趕它們,一旦追上,就會用爪子將其摁倒,擠壓出身體里的空氣,讓它們變回一張扁平的折紙。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我就只好往小動物的體內吹口氣,讓它們重新活蹦亂跳。
某天,我在電視上看了一集關于鯊魚的紀錄片,便要媽媽給我做一只鯊魚。鯊魚做好了,見它躺在餐桌上悶悶不樂,我便將洗手池放滿水,把它放進去。在水里,鯊魚快樂地游弋著,但沒過多久,它的身子變得濕軟、透明,慢慢沉入池底,折疊的部分也慢慢在水中展開。待我回過神要救它時,已經來不及了,躺在我手中的只剩一張濕紙片。
后來,媽媽用防水紙為我重新做了一只鯊魚,它快樂地游弋在金魚缸里。
二
十歲那年,我家搬到了鎮上的另一頭。兩個女鄰居跑來串門,爸爸趕緊拿出飲料招待客人,但他還得去水電部門一趟,因為前任戶主的水電費沒結清。爸爸臨走時連聲向兩位鄰居道歉:“你們自便啊。我太太不大會講英語,所以不能陪你們聊天,千萬別見外啊。”
那會兒我正在餐廳里學習,媽媽在廚房里收拾東西。我聽見鄰居在客廳里講話,她們沒有特意壓低聲音。
“他看上去挺正常的,怎么會干這種事?”
“混血兒都怪怪的,像是發育不全。瞧他那張白人面孔配上一雙黃種人的斜眼睛,簡直就是小怪物。”
“你說他會不會英語啊?”
兩人不再說話了。過了一會兒,她們來到餐廳。
“嘿,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
“杰克。”
“不像是中國名字哦。”
媽媽也來到餐廳,用笑容問候了兩位客人。接著,我就在她們組成的三角包圍圈中,看著她們面面相覷一言不發,直到爸爸回家。
三
馬克是鄰居家的孩子。一天,他拿著《星球大戰》的歐比旺·肯諾比玩偶來我家玩。玩偶手中的光劍不但能發光,還能發出尖叫聲。我和馬克一起看著這個玩偶在咖啡桌上翻來覆去地比畫了五遍。
“它能換一個動作嗎?”我問。
馬克被我的話激怒了,說:“你有什么玩具?拿出來給我瞧瞧!”
可我除了那些折紙外,什么玩具也沒有。于是,我把那只紙老虎帶出臥室。
“小老虎!”我用中文說,隨后,我停下來,用英文又說了一遍。
小老虎沒有輕舉妄動,只是做匍匐提防的姿態,雙眼怒視著馬克,用鼻子嗅他的手。
馬克上下打量了一番這只用圣誕禮盒包裝紙做的紙老虎:“這哪是什么老虎啊?你媽用垃圾做玩具啊?”
馬克用手碰了碰歐比旺的頭,光劍又舞動起來,手臂上下搖擺不停。
小老虎轉過身,向歐比旺撲去,將那塑料小人狠狠推下餐桌,摔了個骨頭斷裂、腦袋搬家。我笑了。
馬克狠狠地把我推向一邊,說:“這玩具很貴的!沒準兒你老爸買你媽的時候都沒花這么多錢!”
我愣住了,癱倒在地。紙老虎咆哮著,徑直朝著馬克的臉猛撲過去。
馬克哇哇大叫。倒不是因為他被老虎弄疼,而是因為眼前的景象讓他既害怕又驚訝。畢竟,這只老虎是紙做的。他搶過我的紙老虎,鉚足勁地蹂躪,連撕帶咬,我的紙老虎瞬間就被肢解成兩半。他把揉爛了的兩團碎紙狠狠地扔給我:“拿去!愚蠢的破玩意兒!”
馬克離開后,我一個人哭了很久。
四
兩周后的星期五,我放學回家,一進門媽媽就問:“學校好嗎?”我悶不吭聲,不想答理她。我把自己關在洗漱間里,凝視著鏡中的自己——我不像她,根本不像!
晚餐時,我問爸爸:“我是不是長得很像中國佬?”
爸爸停住了手中的筷子。雖然我從未跟他提過學校的事,但他似乎早已猜到發生了什么。他雙目緊閉,摸了摸鼻梁:“不,你不像。”
媽媽不解地看了看爸爸,又看看我,問:“啥叫中國佬啊?”
“英語!說英語!”我爆發了。
她努力尋找著會說的英語詞:“你怎么了?”
我啪地摔下筷子,推開面前的飯碗,看著桌上的青椒爆炒五香牛肉,用命令式的口吻說:“以后不準做中國菜!”
“孩子,很多美國家庭也吃中國菜啊。”爸爸試圖幫媽媽辯解。
“問題就出在我們不是美國家庭!”我怒視著爸爸的眼睛說,“美國家庭里根本就不會有我這樣的媽!”
爸爸沒有回話,只是將手搭在媽媽的肩膀上說了句:“我回頭給你買些做菜的書吧。”
媽媽轉過頭來問我:“不好吃?”
“說英語!說英語!”我急了,扯著嗓子大喊。
媽媽伸出手想摸我的額頭,問:“你發燒了嗎?”我用力推開她的手,說:“我很好!不要你管!我只要你給我說英語!”
“以后多和他說英語吧,”爸爸對媽媽說,“你知道遲早會有這一天的,不是嗎?”
媽媽看著爸爸,用手指摸著嘴唇說:“當我用英語說‘愛字的時候,感受到的是聲音,但是當我用中文說‘愛字的時候,感受到的是真情。”說著,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爸爸無奈地搖了搖頭:“但你現在是在美國啊。”
爸爸給我買了一整套《星球大戰》玩偶,我把里面的歐比旺·肯諾比賠給了馬克。然后,我把那堆折紙動物一股腦兒扔進了一個廢鞋盒,并用膠帶把鞋盒封得嚴嚴實實,扔到閣樓上。
如果媽媽和我說中文,我就拒絕回答,久而久之,她只好和我說英語了。但是她蹩腳的口音和離譜的語法讓我覺得很丟人,她出錯,我就挑錯,終于,她不在我面前說英語了。
如果她想要對我說什么,就會像打啞謎一樣地對著我比畫。她會學著電視里的美國媽媽,擁抱親吻我,但她的動作總是那么夸張、別扭、滑稽,讓我覺得丟人。知道我不喜歡她這樣后,她就再沒抱過我了。
媽媽開始學著做美式餐點,我則在家里玩著電游,在學校學著法語。有時候,我看見她坐在餐桌旁,望著手中的包裝紙發呆。不久,就會有一個新做的小動物出現在我的床頭柜上,或依偎在我身邊。不過我照樣會把它們壓扁,然后扔進閣樓的盒子里。
上高中后,她再也沒給我做過紙動物。有時回到家,望著她瘦弱的背影,聽她哼著中文歌,在廚房忙前忙后,我還是難以相信她竟是我的親生母親。我不會走過去和她說話,我把自己關進臥室,獨自追尋美國式的幸福生活。
五
醫院里,母親躺在病床上,我和爸爸分守在病榻兩側。她不到四十歲,看上去卻老得多。
多少年來,她身體有病卻堅持不去醫院,每當被問及身體時,她總說自己沒事,直到有一天她被救護車送進了醫院。醫生診斷,她已是癌癥晚期,手術都救不了她的命。
但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母親的病情上。那時正值校園招聘會的高峰期,我滿腦子裝的都是簡歷、成績和面試,整天琢磨的都是怎樣在招聘主管面前美化自己,讓他們聘用自己。
在她失去意識之前,對我說:“我知道你還得回學校。去吧,不要擔心我,我沒事兒。在學校好好表現。”
父親靠在她嘴邊聽她私語了些什么后,點了點頭,然后離開房間。
“杰克,如果……”她咳個不停,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氣,抓緊機會對我說,“如果我不行了,不要難過,這對身體不好。你要好好生活。閣樓上的那個鞋盒要留著,以后每逢清明,把它拿出來,你就會想到我。我永遠都在你身邊。”
我記得我很小的時候,媽媽會在清明那天給她死去的父母寫信,告訴他們她在美國生活得怎么樣。她會把信紙折成一只紙鶴,放飛到空中。但這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盒子你要存著,沒事的時候打開看看。記得……”她又開始咳嗽起來。
“知道了,媽。”我不自在地撫摸著她的手。
“孩子,媽媽愛你……”她再次猛咳不止。我不禁回想起多年前的那個場景,媽媽捂著自己的胸口,用中文說著“愛”字。
“好了,媽,你歇會兒,別說話了。”
爸爸回來了,我跟他說我想早點去機場,因為我不想誤點。
在我搭乘的飛機飛過內華達上空的時候,母親離開了人世。
六
母親的過世讓父親立馬老了許多。對于他來說,房子太大了,他決定賣掉。我和女朋友蘇珊趕來幫忙收拾東西。
蘇珊在閣樓里發現了那個鞋盒。“這么漂亮的折紙,我還是頭一次看到!”蘇珊顯得十分驚訝,“你媽媽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藝術家!”
是啊,但此時,我眼前的這些折紙動物卻一動不動,毫無生氣。也許在母親去世的那一刻,它們也隨她一起去了;或許遠去的不是它們,而是我童年的記憶,而童年的記憶大多不真實。
母親去世兩年后,四月的第一周,蘇珊被公司外派出差,家里只剩我一人。我懶洋洋地躺在沙發上看電視,不停地換臺,一檔關于鯊魚的紀錄片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一刻,我似乎感覺母親又回到了我身邊,用防水紙給我折著紙鯊魚,而我和我的小老虎圍在她旁邊,出神地觀看著。
刷的一聲!我驚訝地抬起頭,只見一團纏著膠帶的包裝紙滾到了地上,慢慢舒展開來。原來這是那只被我遺忘多時的小老虎啊!肯定是媽媽想辦法把它粘回了原樣。
我蹲下來,趴在地板上,伸出手指想摸摸它。小老虎搖著尾巴,調皮地左撲右跳。我開心地笑了,撫摸著它的后背。小老虎停止撲騰,它的身體開始肢解、舒展,最后,留下的是一張皺巴巴的包裝紙,白色的紙面上點綴著密密麻麻的中國字。
我趕緊跑到電腦前,打開網頁——今天正是中國的清明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