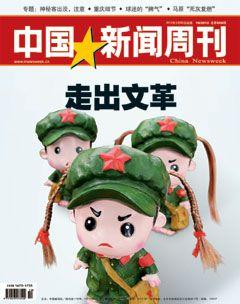社會組織將有更多作為
申欣旺

“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中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3月19日舉行的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談到建立“構建政府管理與社會自治相結合、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體制”時如此表示。
曾長期在民政部擔任司局級干部、后轉任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的王振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以前從未有主要領導人在如此高規格的會議上清楚地表達這樣一種導向,總理的講話意味著政府對社會組織的認識有一個重要的轉變,意味著對社會組織的‘身份認同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非政府組織研究所所長王名亦認為,“政府事務性的職能交給社會組織去做,將為社會組織提供資源和發展空間,而這正是長期以來困擾社會組織發展的體制障礙之一。”
改革社會組織登記模式
王名所說的體制性困境從社會組織的成立一開始就會碰到。要成立一家社會組織,首先面臨的難題是,先要給自己找一個“婆婆”。
根據現行雙重管理,雙重負責的登記管理體制,社會組織的申報者到民政部門申報登記之前,還需要有業務主管單位的批準,沒有找到這個“婆婆”就意味著無法進行登記。
此舉本意是通過一個較高的門檻建立嚴格監管制度,但客觀上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社會組織游離在監管之外。
王名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由于現行的雙重管理體制,很多社會組織難以獲得合法身份。民政部登記的各類社會組織將近46萬家,但他們估計登記率不到一半,如果包括沒有登記的,全國的社會組織在100萬家左右。而我們自己長期的觀察是,沒有登記的應該在300萬到400萬家。”
王名認為,“不管是哪一組數據,都說明有相當一部分社會組織沒有登記注冊,一方面,這些社會組織的生存因為沒有合法身份,無法提供更好的服務;另一方面政府的監管也是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改革登記注冊模式,放寬準入門檻。”
早在2004年的全國兩會,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王名就提交了“關于改革我國民間組織雙重管理體制的建議”的提案。王名說,“對這個提案,民政部很重視,做了很多工作。”
一些地方在悄然試點。上海浦東新區民政局副局長莊大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民政部與上海市民政局的支持下,浦東率先開展區級行業協會登記管理模式改革試點,突破行業協會登機的政策瓶頸。
具體的做法是,在新區同業企業集中、具有一定規模和發展前景、有區域經濟特色的行業中實行登記行業協會。同時配套開展管理模式的改革,將行業協會的業務主管單位轉變為業務指導單位,實行行業組織自發組建、登記機關依法登記、政府相關部門業務指導。
深圳也進行了類似的改革。早在2004年深圳成立行業協會服務署,統一行使行業協會業務主管單位的職責,行業協會的人、財、物與政府部門全面脫鉤。2006年底,組建深圳市民間組織管理局,實行行業協會直接由民政部門登記的管理體制。這是中國最早也最徹底地實現行業協會民間化。此后2008年9月,深圳將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直接由民政部門登記,為推進社會組織民間化作出制度性安排。
據了解,從“雙重管理”變“一元管理”后,深圳社會組織數量顯著增加。2002年,深圳市社會組織有1486家,截至2010年6月,已增長到3862家,涵蓋工商經濟、科學研究、社會事業、慈善等各個領域。深圳每萬人擁有社會組織數量達4.2個,大大高于全國每萬人擁有2.7個社會組織的整體水平。
盡管如此,在全國范圍內,目前采用的仍然是雙重管理模式。王振耀認為,無論是滿足社會需求還是監管需要,放寬準入門檻,改革登記模式都勢在必行。
知情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在此次全國民政工作會議上,溫家寶總理還提出“要加快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的改革,簡化登記管理的程序,對一些社會組織采取直接登記的形式”。
實際上,涉及社會組織生存發展的“三個條例”(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條例)早已進入修改日程,法規修改的內容之一就是社會組織的登記模式改革。
王名介紹說,三個條例的修改準備工作在民政部環節已經完成,并被提交到國務院法制辦,等待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早在2010年3月在安徽黃山召開的“軟法與善治研討會”上,國務院法制辦副主任袁曙宏就透露,《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有望在當年出臺。但此后并未如期面世。
王振耀認為,制度改革的艱難,緣于長期對社會組織的定位和認識的不明確,“過去習慣于把社會組織定位于非政府的、有摩擦意味的,這就把社會組織和政府對立起來,一說到社會組織就想到階級斗爭、社會穩定”。
購買公共服務應當納入財政預算
實際上,早在2004年,中央就認識到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意義。當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提出“????發揮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范行為的作用”,“形成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的合力”。
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也提出“健全社會組織,增強服務社會功能”。
此后,各地陸續開始了包括改革社會組織相關制度在內的探索。
《中國新聞周刊》了解到,浦東新區民政局在2011年提供1800萬元的預算向社會組織購買了從居家養老、生命關愛、公益民生甚至包括社會組織培育本身這樣的服務。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上海浦東新區民政局副局長莊大軍說:“這些工作涉及社會各個領域、方方面面,政府不能不管,但要有效介入又力不從心,政府沒有辦法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去處理。我們的辦法是,由社會組織服務社會。”
王振耀對這樣的改革表示贊賞,“我們的社會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變化,比如說老齡化社會的來臨,對老年人的關懷,這些事情幾乎無法依靠政府完成,最好就是依靠社會組織完成。”
老齡化社會需要專業服務,這些專業化的需求都細分了,比如臨終關懷、空巢老人的照顧等等,需求很大。“我們現在一所老年護理學校都沒有,德國一個老年護理員要上三年課,你說誰專業?”說到這里,王振耀不無遺憾。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狀況,在王振耀看來,“主要是因為政府仍然沒有意識到,一個常態的社會,做好社會服務、回應社會需要是最大的政治,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公共政策仍有問題。”
“仍以老齡化社會為例,這些工作顯然政府做不了,因為這些問題單靠錢解決不了,現在不是缺吃少喝,最好的辦法是讓社會組織去做,擴大政府預算,購買社會組織提供的個性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務。”
王振耀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無論是在國外,還是我國香港地區,社會組織的經費很大一部分都是來源于政府財政預算,香港社會組織的經費60%來自政府購買服務,社會組織的發展并沒有引發社會穩定問題,反而很好地解決了社會矛盾。
這個理念亦為王名認同。盡管地方的探索中購買公共服務的經費并未納入整個財政預算,比如北京購買公共服務資金來源主要是彩票款,但王名對未來的發展表示樂觀,“既然總理提到了,購買服務就不應當是空的,中央財政可能有更大的舉措。”
無論是改革登記模式還是購買公共服務,王名提出,首先要做的仍然是回到法治的軌道上來,“總理此番表態,很可能意味著‘三個條例出臺的障礙已經消除。
“登記模式的改革與政府購買服務到位之后,監管問題需要提到更高的層面上來。”王名提出,“應當由過去的入口管理改為過程監管,加強登記監管部門的權力和職責,以確保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