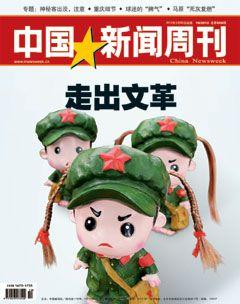無處安放的碑
韓曼曼

一場陰雨,上海的天氣一下又回到了冬天。迪文· 巴爾加早早來到龍華殯儀館參加一位好友的葬禮。生離死別巴爾加這些年來見的多了,然而這天他卻不太能控制自己的情緒。
葬禮結束后,巴爾加沒有馬上離去,而是一個人走到位于殯儀館五樓的上海殯葬博物館。他對這個才開放兩年多的地方有著復雜的情緒。
為了全方位展現上海的殯葬文化,博物館去年從近郊青浦區一所墓園的停車場附近運來兩塊猶太人墓碑。
“事先沒有經過我同意就把墓碑帶到這里。最重要的是,把猶太人墓碑放置在中國的殯儀館內是對猶太信仰的不敬。因為中國的殯葬傳統是焚燒遺體,而猶太傳統則要把完整的遺體埋葬在地下。猶太人認為死亡不是生命的終點,而是一種升華。如果有一天救世主彌賽亞出現,墳墓下的死者就能死而復生。”巴爾加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巴爾加輕輕撫摸著一塊有殘缺的墓碑,這塊墓碑在他2003年發現的時候并不是這樣。墓碑是完整的,只是中間有一道裂縫。不知道是搬運中出現問題還是其他原因,現在缺了一塊。
但巴爾加并不想去跟博物館把墓碑要回來,起碼不是現在。畢竟以他目前的能力,沒有辦法很好地保存這些墓碑。與其讓它們繼續被堆放在無人看管的郊區,時刻面臨著丟失的可能,還不如讓它們躺在這個干凈整潔的地方。
自10年前在上海一家古董店里看到一塊待售的猶太人墓碑后,巴爾加就將尋找散落在上海各個角落的猶太人墓碑作為自己的一項使命。至今,他已經找到105塊墓碑,并與30多個墓碑主人的親人取得聯系。
他的夢想是將來能夠在上海建立一個專門的墓碑紀念地,作為對上海猶太人歷史的見證并供人們去緬懷。然而這個夢想似乎并不容易實現。
停不下來的尋找
巴爾加現在已經是上海猶太人圈中一位小有名氣的導游,平均每周能接兩三個外國團,其中很多團都對上海的猶太人歷史有特別的興趣。忙不過來的時候,他也會讓妻子幫忙帶團。
妻子是俄羅斯人,兩人2005年在上海相識相愛并在第二年決定結婚。在丈夫的影響下,原先對猶太文化基本無任何了解的妻子現在儼然已成為一位猶太歷史“專家”。
巴爾加總是在想,如果不是因為十年前發現那第一塊墓碑,也許自己現在依然在做電視記者或者早已離開中國。然而人生的改變有時僅在一瞬間。
那個時候,巴爾加還是以色列一家電視臺駐上海的攝影記者。一天,一個做導游的朋友告訴他,上海的一家古董店正在出售兩塊猶太人的墓碑。
巴爾加起初對這個發現并不感興趣。他知道作為遷徙民族,猶太人墓碑可能出現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相比較于當時以色列電視臺最關注的國際政治形勢與不斷升級的各種戰爭,這個不能給觀眾帶來緊張與刺激的事情,顯然不可能成為頭條。
然而,當逐漸了解到在上海的猶太人歷史,以及猶太后裔一次次來到上海想瞻仰先人的墓地卻再也找不到任何遺跡后,他意識到這將會是一個非常棒的故事。
資料顯示,曾經在上海居住的猶太人有三種類型。第一批是鴉片戰爭后,上海作為一個開埠城市吸引到來此拓展商業貿易的猶太人,包括赫赫有名的沙遜、哈同、嘉道理等賽法迪猶太家族。第二批就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為了躲避俄國內戰和國內出現的反猶浪潮逃到上海的俄國猶太人。最后一批也是最大的一批就是1933年到1941年間,為了躲避希特勒的屠刀逃亡到上海的猶太人。據統計,最后一批人最少有2.3萬。
解放初上海共有4個猶太人公墓, 近3700座墓碑,分別坐落在今天的惠民路、定海港路、黃陂北路和番禺路。1958年,上海政府將所有外國人的墓地重新安置到位于上海西郊的青浦區徐涇鎮的一個國際公墓里。但這個公墓在文革期間遭到嚴重破壞,墓地蕩然無存。
古董店老板并不愿意向巴爾加透露任何有關墓碑來源的信息。不得已,他花了800元買下了兩塊墓碑。古董店老板意識到做生意的機會來了,后來把巴爾加帶到原先國際公墓所在地徐涇鎮的一個小村子。
那一次,巴爾加在村子里發現了四塊猶太人墓碑。后來幾天又陸續在徐涇鎮的其他村子里發現了幾塊。
巴爾加意識到如果他不做些什么,隨著這些地方的城市化進程,散落在此的墓碑很有可能就會慢慢消失,而這些猶太人曾經存在的歷史也就隨之被抹滅。盡管這些猶太人的尸骨永遠無法找到了,但巴爾加不想讓他們的墓碑淪落到此番結局。因為在猶太文化中,墓碑被看作紀念逝者的神圣之物。
這些年來,巴爾加踏遍了市郊所有可能會發現墓碑的村子。在農家的石槽中,田間小路的基石下,臭水塘的黑泥里甚至是水溝里,他努力地讓一塊塊墓碑重現原貌。
“很多中國人都覺得我收集墓碑的做法很奇怪,包括我雇來幫我搬運墓碑的人。他們邊干活邊都在議論說我一定是要靠這些墓碑發大財。”巴爾加說。
用于向村民購買墓碑和雇傭人搬運的錢他已經記不起總共有多少。雖然在這期間也得到了一些機構和私人的資助,但大部分的費用還是他自己承擔。
悄悄搬進停車場
每找到一塊墓碑,巴爾加都會在自己的網站上登出墓碑的照片,并注明找到墓碑的時間、地點,墓碑上的文字以及墓碑的保存情況。網站確實幫助了很多猶太家庭找到屬于他們的墓碑。最近一個,就是現居住在美國馬里蘭州的布萊恩·哈普德教授一家。
祖父這個詞對于布萊恩·哈普德來說其實有些陌生。他并沒有見過祖父,僅有的模糊印象也都是從父親那里聽到的。布萊恩·哈普德記得父親生前曾對自己說過,祖父為了躲避納粹屠殺,帶著年幼的父親從柏林逃到了上海。然而幾年后,就因為營養不良死于上海。
“以前每當父親感傷的回憶祖父的事情時,我都像聽故事一樣,內心并沒有受到很大觸動。畢竟那已經是一段年代太久遠的歷史了。然而當我站在祖父的墓碑前,撫摸著他的墓碑時,我卻難以抑制自己的情緒。那一刻,我強烈地感受到我和祖父的血脈相連。我突然特別想念他。”布萊恩·哈普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由于巴爾加找到的墓碑一直沒有一個合適的安放地,在以色列駐上海總領事館以及朋友的幫助下,105塊已被發現的墓碑被暫時擱置在上海的三個不同地方,分別是青浦區徐涇鎮一所墓園的停車場,巴爾加猶太牧師朋友擁有的倉庫中,以及巴爾加以前工作過的莫干山路畫廊里。
存放在徐涇鎮的墓碑都是他在附近村子中找到的。在以色列駐上海總領館和上海外事辦的幫助下,墓園管理者曾答應免費把墓碑都暫時安放在墓園里。然而不知何時,這幾十塊墓碑就被集中遷移到墓園的停車場,直到現在。
巴爾加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能為墓碑找到一個永久的紀念地。“這些墓碑的價值只有在紀念地中才能得到最大的體現。紀念地呈現的形式并不是最重要的,面積的大小也不重要。”他的這一想法得到了所有已經聯系上的猶太家庭的支持。
布萊恩·哈普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關于祖父墓碑的安放,他和母親曾經有過爭論。母親也曾一度想過讓他把祖父的墓碑從上海帶回國。然而他們最終還是覺得上海這個祖父長眠的城市,才是最應該安放的地方。
布萊恩·哈普德表示他和家人都非常愿意為墓碑紀念地的落實提供一切可能的幫助。而他們也由衷地期盼能夠在不遠的將來到上海參加墓碑紀念地的揭幕儀式。
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科學處代表、總領事夫人凱茜博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德國總領事館也很支持巴爾加的想法。總領事館這些年也為保護上海猶太人歷史做出很多努力,包括現在正與以色列總領事館合作進行的一系列展現猶太人歷史的活動。然而她沒有透露會提供哪些具體的幫助。
誰來保管墓碑
巴爾加最希望把紀念地設在上海虹口區的霍山公園里。二戰期間居住在虹口隔離區的猶太人常在這個公園內休息聚會。1994年虹口區在公園里設立了猶太難民紀念碑,以紀念當年那段歷史。霍山公園現在已成為附近居民打牌下棋,遛鳥之地,也成為來到上海尋根的猶太人必去的地方。
而另一個理想之地就是同樣位于虹口區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曾經的摩西會堂舊址。摩西會堂原是一座供猶太人專用的會堂,二戰期間成為上海猶太難民的宗教活動中心。2007年虹口區政府對會堂進行了修繕,并改名為猶太難民紀念館。這里現在已經成為整個上海有關猶太難民文字和實物資料最多也最為完整的地方。
這幾年巴爾加曾跟猶太難民紀念館有過多次合作。這里是他帶團必參觀的景點之一,他也曾在這里舉辦過為期一個月的“上海猶太人紀念地概念設計展”。
然而讓巴爾加不解的是,明明虹口區政府和紀念館都曾表示對他的想法很支持,但每當他提出要把想法落到實處并希望尋求政府支持時,卻始終得不到答復。
“在中國生活十多年的經驗告訴我,中國政府如若一直不予答復某事,潛臺詞就是不同意某事。”巴爾加猜測。
巴爾加說,如果墓碑始終在上海得不到好的安置,也許他會考慮把墓碑運到其他更重視它們的國家。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時,虹口區外事辦主任、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館長陳儉表示,虹口區政府尊重并支持巴爾加收集墓碑的事情,同時也很重視猶太人在上海的歷史,否則區政府也不會對位于虹口的上海摩西會堂舊址進行修繕改造,作為“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供游客參觀。
“但巴爾加不是墓碑的所有者,他沒權力替他們做出建立墓碑紀念地的決定。巴爾加首先應該找到所有墓碑的家人并得到全部人的認可,才可以實施自己的計劃。” 陳儉建議,巴爾加把目前所找到的105塊墓碑交予虹口區政府代為保管。“如果他愿意把墓碑交予我們,區政府會成立專門小組來研究這個事情的具體落實。”
對于虹口區政府的回應,巴爾加說他從不認為墓碑屬于自己,而紀念地的計劃不僅得到猶太家庭的許可,也得到了上海猶太社團領袖的認可。
“其實由誰來保管墓碑并不重要。如果虹口區政府真心愿意幫助我們實現建立紀念地的愿望,我也非常愿意把我收集的所有墓碑交予他們保管。但交予之前,我希望區政府能夠做出一個讓我和上海猶太社團以及墓碑后人滿意的安置計劃。”巴爾加說。
巴爾加目前正在做一部關于猶太墓碑的紀錄片。在他還未完成的影片中,一個來到上海尋找祖父墓碑的年輕男子看著散落地下的墓碑留下了眼淚。“它們至少應得到一點尊重,被更多人紀念并為它們祈禱。”年輕人哽咽著說。面對他哭泣的臉,巴爾加沒有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