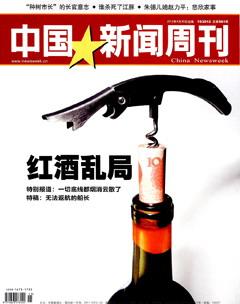機器人對中國的挑戰
薛涌
最近,德國勞動研究所所長克勞斯·齊默爾曼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撰文,稱機器人“正在見證中國工業戰略的重大轉變”,其中特別提到去年8月富士康宣布未來3年在組裝工廠中部署100萬臺工業機器人。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的數據,目前全球使用的工業機器人總數接近110萬臺。這意味著一家企業就幾乎將世界機器人的使用量翻倍。但是,中國在機器人的使用方面,大有潛力可挖。比如,中國的汽車產量已經超過美國。但根據2011年的一項報告,美國汽車業使用的機器人達77000臺,中國則僅為28000臺。另外,在危險的煤礦井下作業中,機器人也被大量使用,礦難頻發的中國,正亟須引進機器人來代替人力。
眾所周知,“人口紅利”,是推動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經濟起飛的重要動力。如今“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消失中,“民工荒”的危機幾年來不絕于耳。“中國模式”是否還能維持?這一危機感已經滲入公共的意識之中。齊默爾曼則給我們描繪了一個異常樂觀的景象:未來中國的勞動力短缺,可以通過機器人神奇地解決。
真是如此嗎?首先,從利益的角度看,這樣的前景被一位德國戰略家所描述出來毫不奇怪。在近年來百業蕭條的西方制造業中,德國制造業可謂一枝獨秀。這并不是僅僅靠著豪華車等民用產品,更靠所謂的“生產產品”,即制造業所必需的器械。這些生產機械的最大市場,就是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一套生產機械,少則幾百萬,多則可能上億。一位給德國公司做代理的朋友告訴我,現在德國貨已經成了賣方市場。中國的廠家訂購德國機器,下單后往往要等半年以上,而且不停地漲價。可見,“德國奇跡”和“中國奇跡”不分彼此。機器人屬于生產機械之極致,技術主要在德國、日本這些高端制造業國家手里。從德國的利益考慮,當然希望中國的工業盡快從人力向機械轉移。
那么,這種轉移的難度如何?我們首先必須面對機器人的成本問題。機器人當然有著多種優勢,但費用也相當可觀。一個六軸機器人本身價值6萬美元,安裝費用則高達20萬美元。其中給機器人編程的費用特別高。
另一方面是,雖然本世紀各國機器人的使用普遍增加,但在世界第一大機器人大國日本,機器人的使用從2000年的將近39萬臺降低到2008年的32萬臺多一點。而在人口老化的日本,不僅勞動力價格奇高,供應也嚴重不足。
要知道,國際制造業在過去幾十年之所以紛紛涌入中國,追求的就是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如果勞動力能夠完全被機器人取代,工廠為什么要設在中國?西方國家何不把同樣的機器人召回本國?可見,盡管中國可能面臨著一場機器人革命,靠機器人一舉解決中國的人力短缺和持續發展問題,絕非那么容易。
對于這一問題,我們需要從兩個方面看。第一,如果中國維持現有的制造業結構和發展模式,那么即使通過機器人解決了勞動力問題,也只能充當二流工業國家。齊默爾曼聲稱:“在iPhone或iPad的最終售價中,中國勞工成本估計僅占1%~3%。對這一極低比例進行大幅提升是中國的目標,也是其所有工業部門戰略抱負的核心。”但是,他所忽略的核心問題是,iPhone或iPad的生產組裝即使全用了機器人,這一生產成本在產品的最終售價中還只能占1%~3%,并不會提高。同時,機器人需要大量進口,這無異于中國制造業“外包”的開始。在貿易上,靠在iPhone或iPad的最終售價中的1%~3%,恐怕難以平衡進口昂貴的機器人的費用。
第二,中國雖然面臨著勞動力短缺,被機器人替換下來的勞動力還是要干活維生的。現在農民工的教育素質,除了從事“繁重低級的工作”外,是否能夠勝任更為高端的工作?比如,當精密的機器人在運轉過程中出現機械故障或程序混亂時,靠著每年五六百塊生均公用經費而讀完中小學的工人,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嗎?
俗話說,借來的拳頭打不了人。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科技,鑲嵌于人家的發展模式之中。中國要成功地面臨未來的挑戰,只能從根本上學習人家的模式和體制,而不是頭疼醫頭,腳痛醫腳。在這一關鍵的歷史時刻,我們不能忘記中國近代史的創痛:鴉片戰爭后中國突然意識到西方的船堅炮利,覺得學會了這些,問題就解決了。結果還是頻頻受辱。到了同治中興時終于明白了這船堅炮利背后有著一套工業體系,于是有了洋務運動。可惜,那時的結論也不過是中體西用,以為拿過來人家的工業體系就完事大吉,到甲午之后才意識到政治改革是個繞不開的門檻。但愿這些并不遙遠的創痛,會使當今中國人變得更加聰明起來。★
(作者系旅美學者,在美國薩福克大學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