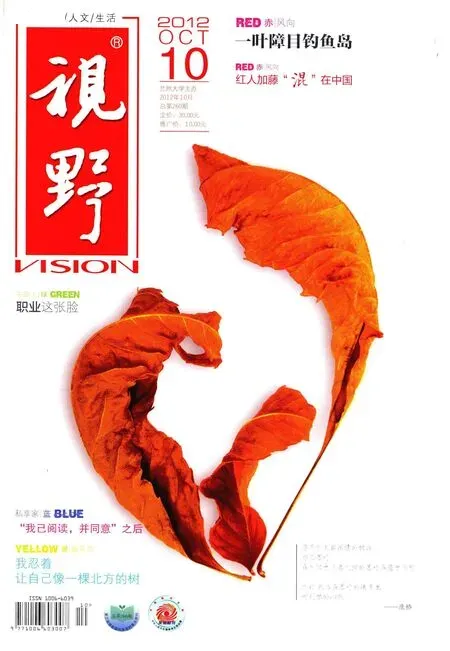我愿意生活的幾個時代
李 方
11 世紀的北宋
這個時代之所以高居榜首,我的想法很簡單,是因為這一百年里,五個姓趙的皇帝竟不曾砍過一個文人的腦袋。我是文人,這個標準雖低,對我卻極具誘惑力。
于是文人都被慣成了傻大膽,地位也空前地高。想想吧,如果我有點才學,就不用擔心懷才不遇,因為歐陽修那老頭特別有當伯樂的癮;如果我喜歡辯論,可以找蘇東坡去打機鋒,我不愁贏不了他,他文章好,但禪道不行,卻又偏偏樂此不疲;如果我是保守派,可以投奔司馬光,甚至幫他抄抄《資治通鑒》;如果我思想新,那么王安石一定高興得不得了,他可是古往今來最有魄力的改革家;如果我覺得學問還沒到家,那就去聽程顥講課好了,體會一下什么叫“如坐春風”。
當然,首先得過日子。沒有電視看,沒有電腦用,不過都沒什么關系。我只想做《清明上河圖》里的一個畫中人,又悠閑,又熱鬧,而且不用擔心社會治安……高衙內和牛二要到下個世紀才出來。至于這一百年,還有包青天呢。
本世紀60年代的美國
那是一個最紅火又最灰暗的年代。青年人在那時,幾千年來第一次打贏了反抗父母的一仗。父母代表了什么?他們供你吃供你喝,又為你安排了一個妥妥帖帖的前程,你怎能不當他們的乖寶貝?但是,兒子覺得,父母的愛已經窒息了他們的每一個毛孔。他們不得不大聲自問:怎樣才是一個真實獨立的我?
若我生在那個年代,我想我會和他們一起,開著破車沖上美國的每一條大路,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聽鮑勃的歌,聽披頭士和滾石樂隊的歌,大聲朗誦金斯堡的詩句。當然,我們還會遇到馬丁·路德·金博士,他正領著黑人兄弟向華盛頓進軍。他一遍又一遍地對他們大聲說:“我有一個夢想!”
我有一個夢想!讓你覺得血在燒。
杜牧時代的揚州
如果他肯,我愿意隨他去揚州。他能夠自請下放,我想我也能。
“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生在晚唐,盛唐國威不再,北方正是軍閥割據,朝廷里兩派又斗得不可開交,所以我們一起去揚州過過舒心日子。
這是一個小家碧玉的時代,揚州就是代表。還在早些時候,徐凝就在詩里寫道:“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無賴,就是天然的可愛,現在看看杜牧怎么說:“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有人說,這是亡國之音,可那些道貌岸然的興亡說教,和我們又有什么相干呢?顧炎武固然說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可如果人家連這個責都不讓你負呢?還是回來吧,回到這個精神上溫柔的家園。

名士時代的東晉
《世說新語》里講,王獻之居山陰,突然想念戴安道,便冒雪連夜乘船前往訪戴。天亮到了戴家門前,卻連門都沒敲,轉身就走。仆人很奇怪,問為什么。王說:“吾乘興而來,興盡而去,何必見戴?”
這就是名士風度,以心照不宣為特征。在人際關系復雜化的今天,我有理由懷念這個時代。當然,站在道德的立場上,我們有一萬條理由攻擊名士們都是廢物,但我們似乎并不理解他們對文化的感情。
我們都知道,對一樣東西感情太深,往往并不會總是掛在嘴邊。名士們也一樣,對文化愛得太深,反倒不談了。他們喝酒,穿奇裝異服,品評人物,在一般人眼里是放誕,但在他們心里,卻是用這些為文化筑起了一道籬笆,不讓別人輕易染指。甚至連他們自己,消費的也不再是文化本身,而只是它的觀賞價值。
宋襄公時代
春秋時,宋襄公與楚國打仗。部下勸他乘楚人半渡擊之,不聽,終遭敗績。宋人怨他,他卻說:“君子不困人于厄,不鼓不成列。”
與敵人講仁義道德,歷來,宋襄公被看成傻瓜。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他不過是在維護一種傳統軍人的榮譽感,只是行將過時罷了。
這種榮譽感,為貴族所獨有。當時打仗,大概不像后來殘酷,倒有點過家家的意思。戰斗的勝負,主要取決于雙方貴族的決斗,一般士兵,不過跟著搖旗吶喊而已。而貴族,往往又把榮譽感看得比生命還重。孔門弟子子路與人作戰,寧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說,就是這種榮譽感最后的閃光。另外戰斗中還有許多規矩,像“不殺二毛”,就是不傷害頭發花白的人,在今日看來也頗為不可思議。你盡可以笑他們癡,笑他們傻,但你不能不承認,那是一個充滿人格魅力的時代。當時大地上還很空曠,做人,必須頂天立地才能自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