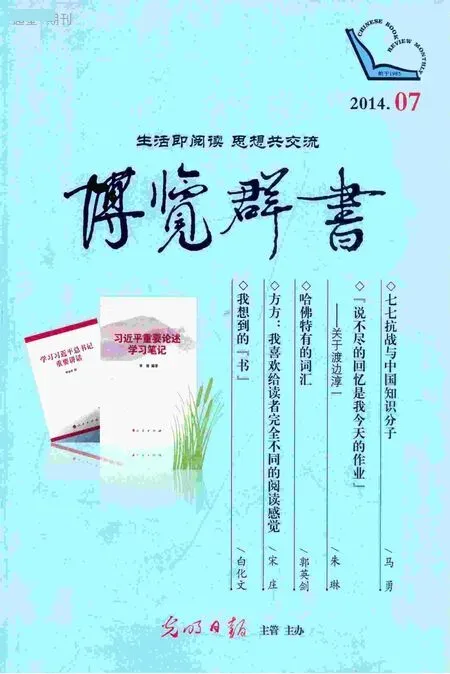如《世說新語》般有趣
○李國濤

《〈讀書〉十年(1986-1990)》,揚(yáng)之水著,中華書局2011年11月版,48.00元
揚(yáng)之水的《〈讀書〉十年》(一),是她當(dāng)年的日記,讀罷不勝感慨。創(chuàng)刊于1979年的《讀書》月刊,當(dāng)年的讀者多矣,我是其中之一。它最興旺的時(shí)期大約在1986年至1996年,也就包括揚(yáng)之水在那里的十年。現(xiàn)在讀一讀,很有趣味。回想起來,那真是一個(gè)創(chuàng)造性發(fā)動的時(shí)代,有奇跡出現(xiàn)的時(shí)代。就以《讀書》而言,主編沈昌文老先生帶著四位只有初中學(xué)歷的女編輯,編出在學(xué)術(shù)界以及在讀書界有聲譽(yù)且有好人緣的刊物,實(shí)在不易。以揚(yáng)之水來說,她本是知青,回北京開了幾年大卡車,而后考入文化系統(tǒng),進(jìn)了《讀書》;在進(jìn)《讀書》之前,已在那里發(fā)表了不少文章。這奇不奇?其他幾位女編輯,好像也多是知青。曾有一位男知青王焱,是公交車上的售票員,后來離開《讀書》,已成有名的學(xué)者。知青,是一個(gè)多么光榮,又多么令人心酸的稱呼。那時(shí),光榮和心酸,真是常常聯(lián)在一起。
揚(yáng)之水本名趙麗雅,用過許多筆名,后來確定了“揚(yáng)之水”。《讀書》十年之后,她調(diào)中國社科院專門從事研究,所著多矣,如《脂麻通鑒》、《詩經(jīng)名物新證》、《終朝采藍(lán)——古名物尋微》,洋洋大觀,揚(yáng)名海內(nèi)。從日記上看,當(dāng)年她沉醉于讀書,曾受到沈主編的批評。我覺得她那時(shí)瘋狂地讀書(當(dāng)然還有瘋狂買書),簡直就像掰開餅子狂嚼,幾天一部。她接觸的學(xué)者很多,自己勤奮好學(xué)又虛心并關(guān)心老專家,所以人人喜歡她,她也樂于跑腿,還替徐梵澄老先生抄過稿。她的書法,能入那些先生們的法眼已屬不易,何況得其欣賞和信任。
有趣的是難與交往的錢鍾書也在楊絳的信(1986)里附言曰:“你的文言相當(dāng)內(nèi)行,不可多得;但希望我這句話不要引得你去死鉆文言,變成‘女學(xué)究’。”后來,卻真是應(yīng)驗(yàn)了錢鍾書的話,她成了女學(xué)究,這是她自己說的。更有趣的是,楊絳就在那封信里說道:“你引了錢鍾書的話,他本人卻不知出處。你讀書用功,竟打倒了錢鍾書!一笑。”
那時(shí)的揚(yáng)之水何如人也?沈主編在此書的序里深情記道:“上天安排,讓我在二三十年前認(rèn)識了一位身材短小,名副其實(shí)的小女子:揚(yáng)之水。”那時(shí)她剛?cè)鲱^。過兩年去游華山,山高路陡,她見挑夫挑著八十斤重的擔(dān)子沿階而上,就要來試試自己當(dāng)年埋干過的活兒,現(xiàn)在還行不行。一試,上了幾十階,還行。她很高興。但也可見當(dāng)年的知青生活。
關(guān)于這本日記,作者在書的封底上說道:
這里記錄了不少月旦人物的“私語”,似乎不宜公開,不過想到這些評議其實(shí)很可以反映評議者本人的性情與識見,卻無損于被評議者的成就與聲名,時(shí)過境遷,這些“私語”便只如《世說新語》的故事,我們便也只如聽故事罷。
讀來,許多大學(xué)者們的評議,真的如《世說新語》般的有趣。恰好我近日還讀著一本黃裳的《來燕榭文存二編》,《谷林先生紀(jì)念》一文中說到名家議論《讀書》,不妨引下來供讀者讀一讀。黃裳引谷林的話:
說到《讀書》文風(fēng)的改變(不只一次),谷林在別一箋中有極為形象化的解釋。他認(rèn)為前期《讀書》作者,以“文苑傳”中人為多,后期則以“儒林傳”中人為主。真是片言解紛,大有“世說”趣味。
可說《世說》趣味,在這本日記里俯拾即是,更在早期的《讀書》里。揚(yáng)之水其人,也是由“文苑”而入了“儒林”。再舉幾件趣事罷,以見那個(gè)時(shí)代的“世說”風(fēng)。記在金克木家,“說起錢鍾書,金夫人說,這是她最佩服的人。金先生卻說,他太做作,是個(gè)俗人。”金先生愛同小女子揚(yáng)之水聊,他說:“老年人怕什么?最怕寂寞,現(xiàn)在幾乎沒有什么能夠在一起說話的人,而一看見你,就覺得很投緣。”金先生喜談話,揚(yáng)之水記曰:
他說,他曾經(jīng)有一次同友人一氣聊了二十個(gè)小時(shí),不吃不睡。怪道有人對他說:你一離開這兒,讓人覺得北京好像少了半個(gè)城。雋語也。
那年頭的生活,不但見到“雋語”,也有傷心語。1987年初,記及友人楊麗出國讀博士:“當(dāng)年在果品店,她是靠賣血以為學(xué)費(fèi),補(bǔ)習(xí)英語。”現(xiàn)在這種事已經(jīng)沒有了吧?有爸媽供著花錢,只怕你不想上學(xué),不想補(bǔ)習(xí)。說到這里,我想到該書里還記著一則揚(yáng)之水自己1989年獻(xiàn)血的事:“上午倪樂來送補(bǔ)助,血站發(fā)了54元,三聯(lián)發(fā)了300元!真讓我大吃一驚。”不知道那位楊麗自己賣血能得到如此優(yōu)厚的補(bǔ)助否,那在當(dāng)時(shí)是相當(dāng)于一位編輯一個(gè)月的工資呢。
揚(yáng)之水心地善良,在工作上是很求上進(jìn)的。1988年2月11日記“發(fā)稿一日,(從早上七點(diǎn)伏案至晚六時(shí)半)”。看來是相當(dāng)辛苦的。有一次,1988年春節(jié)時(shí),記她的老上級沈昌文:
過年對于我來說是加倍讀書的日子,對于老沈來說是加倍工作的日子。與之相對,不免生些慚愧。可又實(shí)在不愿放棄這最愜意的人生樂趣。可以自慰的是:他是三聯(lián)的總編輯、總經(jīng)理,已被情愿或不情愿地綁上戰(zhàn)車,而我不過是一介小卒,自可得些逍遙。
話如此說,她對沈總還是同情的,亦有自責(zé)之意。最使我感動的是她對女翻譯家、比較文學(xué)家趙蘿蕤的態(tài)度。趙氏是陳夢家的夫人。陳夢家是大詩人,大學(xué)者(考古學(xué)家),1966年去世。此后趙蘿蕤獨(dú)身孀居。揚(yáng)之水作為一名編輯到趙家去聯(lián)系,但卻動了真情。那時(shí)候趙氏近八旬高齡。1988年2月7日記:
又往趙蘿蕤老師家送《讀書》第一期樣書。她非常熱情,一再挽留我多坐一會兒,因告訴我,近來心境很有些異樣,不久前一位友人對她說,你無兒無女,晚年堪傷,眼下身子骨尚硬朗,一切可自己料理,一旦生出什么病癥,行止不便,當(dāng)作何處?聽罷此言,很受震動。
趙老師現(xiàn)與其弟同居一院,弟弟一家也是“牛衣對泣”,膝下并無子嗣,如此,只是三老了,年齡一般上下,誰也顧不了誰。從初次見面我就對這位老太太抱有好感,其實(shí)早先她也慮及此事,便沖口而出:“我可以照顧您,您把我當(dāng)女兒待吧!”趙老師當(dāng)即高興地應(yīng)道:“那我就認(rèn)你做干女兒!”
實(shí)際上,訪問,取稿,送稿費(fèi),是常有的編輯業(yè)務(wù),她對許多老專家都是如此。她記著:“訪趙老師,送她一個(gè)洋娃娃,以解她的寂寞。趙老師真是一個(gè)好人,做學(xué)問一絲不茍,待人也是一絲不茍。”我想這也不是作為干女兒做的事,她送點(diǎn)小禮品給老學(xué)人也不少見于日記,這可以說這是一位好編輯與作者的聯(lián)系。但也許是那時(shí)《讀書》編輯部的風(fēng)格吧,也是很動人的。我不知現(xiàn)在的報(bào)刊編輯部還有多少保有這種風(fēng)格。
日記本是私人性的。揚(yáng)之水的這本也是如此。誰寫日記時(shí)想到30年后發(fā)表呢?時(shí)代的風(fēng)云,或者說氣息,現(xiàn)在只能說是從日記中嗅到一點(diǎn)。也許作者曾考慮及此,她請她的好友、同事吳彬?qū)懶驎r(shí),就囑她多寫刊物的事,少寫作者個(gè)人的事。果然《序》里說到“讀書無禁區(qū)”的提法,當(dāng)時(shí)的確影響一個(gè)時(shí)代。如1989年7月29日記:
下午老沈到出版署聽取對《讀書》七、八期合刊的裁決,要我們在編輯部坐等。……五點(diǎn)又回到編輯部,老沈已領(lǐng)到上峰的指示;《讀書》從內(nèi)容上看,還沒有與中央精神相悖的地方,但馬列主義談得不夠,必須加強(qiáng),否則不能出版。于是我們立即找出談馬列的稿。
這樣的記載不只此一處,我想這就是時(shí)代風(fēng)云的氣息。不過,所記當(dāng)然不多。看到1988年7月有一處記:“《人民日報(bào)》頭版頭條發(fā)表本報(bào)評論員文章:《為政一定要清廉》,可知官僚政權(quán)已腐敗到什么程度。”那時(shí)的報(bào)紙文章,那時(shí)普通讀者感想,過了二十多年,似乎依然如此。這很使人難過。
這部《〈讀書〉十年》分三冊,現(xiàn)在還只出了一冊。我急著等待看第二、三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