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對《百花齊放》的自省
2012-06-07 02:08:50寧源聲
共產黨員(遼寧) 2012年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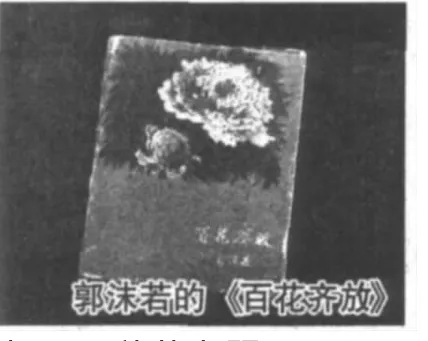
郭沫若在現代詩歌史上產生過廣泛深遠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后,他繼續寫了大量新詩,但真正的好詩卻極為有限。
1958年,為宣傳“百花齊放”方針,郭沫若用了10天時間,選擇100種花為題目,寫了101首的詩集《百花齊放》。此詩集在詩的結構上,表現為“形象描述——政治概念”的公式,即
從對花的形態、肌理特征的描述,上升為對政治命題的說明。
例如由水仙花的“只憑一勺水,幾粒石子過活”,而聯系起“總路線”的“多快好省”的口號,說這是“活得省,活得好,活得多”的“促進派”。
當時,詩集曾獲得高度的評價,但現在看來,它不但開了簡單化比附詠物詩的先河,而且乏善可陳。
但值得關注的是,郭沫若在1959年致陳明遠的兩封信中,對此曾作過誠懇的自我批評。他說:“我的《百花齊放》是一場大失敗!盡管有人做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為憾的。”又說:“盡管《百花齊放》發表后博得一片溢美之譽,但我還沒有糊涂到喪失自知之明的地步。那樣單調刻板的二段八行的形式,接連101首都用的同一尺寸,確實削足適履,倒像是方方正正、四平八穩的花盆架子,裝在植物園里,勉強地插上規格統一的標簽。”
“現在我自己重讀一遍也赧然汗顏,悔不該當初硬著頭皮趕這個時髦。”
這是郭老的悲哀,也是時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