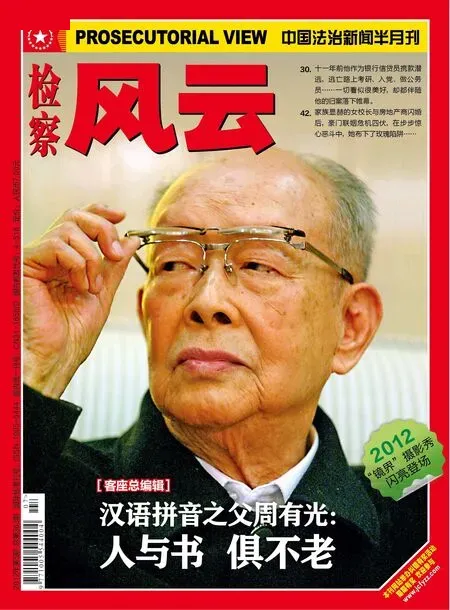“穩中求進”的詩外功夫
文/朱敏
“穩中求進”的詩外功夫
文/朱敏
“功夫在詩外”,經濟亦如是。不能忽視那些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進程的詩外真功夫。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讓中國經濟社會走上真正的現代化坦途。

朱敏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企業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經濟導刊執行總編,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首席經濟學家,著有《中國經濟缺什么》《轉型的邏輯》等。
對于2012年的中國經濟發展主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為四個字:“穩中求進”。這一表述不難理解,就是在實現宏觀環境保持相對平穩——經濟“軟著陸”——的前提下,側重于結構調整和改革突破即“調結構、抓改革”。有所巧合的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前夕,在對2012年中國經濟進行展望時,我也想到了四個字:“動中求變”。
值得一提的是,“動中求變”雖然乍看與“穩中求進”在字面上有所不同,實則基調與之并無二致:“動中”是對外部動態環境的客觀描述,“穩中”則是宏觀政策力求達到的一種取向;而“求變”與“求進”在此則是同一個意思,即變革、改革、轉型之意,意在重構規則。
其實,早在展望2009年的關鍵詞時,我就想到了“重構規則”,于是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經歷了經濟社會接踵而來的突發變故之后,格局的洗牌和規則的重構,更成為一種物極必反般的必由之徑。并斷言,“變革”定會是年度中心語,要變革現狀,就必須重構規則。由此,變革與重構,便成為經濟社會的精神內核以及商業創新的有力支點。
彼時正是國際金融危機發軔與蔓延之時。至今三年間,全球經濟從波瀾不興到驚濤拍岸,漸成動蕩之勢,“變革”之需益發迫在眉睫。正如2012年元旦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湖南調研經濟運行時所強調:“穩中求進”的“穩”不是不動,而是要穩定增長,保持物價總水平基本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同時還要實現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進步、技術改造的進步、管理和效益的進步、改革開放的新突破。
地方競爭模式主導的經濟怪相
2009年中國經濟率先走出低谷,開始復蘇回暖;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然而,這些停留在速度和總量層面上的利好數據,只是由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制造的數字神話,不但對提升國家經濟競爭力、改進民生沒有更為實際的意義,且與高層倡導的科學發展觀、包容性增長(共享式發展)也是非兼容的。

關于地方政府競爭的模式,可以通過類比的方式來理解:如果說,土地交易是房地產業的一級市場、房地產開發建設只是二級市場,那么政府競爭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一級市場,而市場競爭只是二級市場。這種政府競爭模式和凱恩斯語境下的宏觀調控有著本質的區別。凱恩斯的宏觀調控本來只是反危機的一系列強有力措施、一時的應對之策,但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卻把它常態化了。
在此競爭模式下,各級黨政機關不但直接決定經濟發展的大方向,而且形成一個以黨政一把手為核心的強制運行體系,直接參與微觀層面的操作,而立法、司法、輿論媒體、社會公眾的有效監督往往“被缺位”,市場的自我修復功能往往“被缺失”,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微觀企業,只能跟著一只“看得見的手”(或被這只“手”牽著)走。
地方政府競爭模式有兩個層面的邏輯解釋。一種是由官方理想主義意識形態延伸出的“用發展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另一種是“數字出官,官出數字”的官員升遷規則,但兩者導致的結果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以“短、平、快”為特征的掠奪式發展。在實踐中,地方政府官員之所以沒有做到科學發展,并非因為官員本身存在認知上的缺陷,事實上,官員如何會不明白土地財政、產能過剩等問題的危害或“后勁”呢,只不過,在決定他們命運的選官體制下,只好“知其不可而為之”。
盡管在法律上官員是由人大選舉產生的,但實際中,人大往往只在組織部門做出任命決定后履行一個法律程序,更何況不乏有些地方的人大常委會主任和黨委一把手本來就是同一人。因此,每屆地方政府都喜歡搞“三高一低”、“鐵公基”這些皆大歡喜而又立竿見影的工程,根本沒有動力去發展科、教、文、衛這些“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長期事業,豈能不知改變一個國家命運的乃是科學與教育?特別是基于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創新型國家建設等多方面的愿望和渴求迫切之下,推進教育體制改革尤為重要。
在此過程中,土地、財政、工商、稅務等部門往往較為強勢,而教育、文化、衛生等部門則被冷落。與此相應,在全國范圍內,每個地方政府的思路都大同小異,有自然資源的地方通過企業改制招商引資,沒有自然資源的則從歷史上找文化資源,歷史上實在找不到正面形象的,“西門慶故里”之類,居然也爭先恐后地要打造為旅游文化品牌。在自然資源或文化資源之外,還可以先制造出類似于“經濟圈”的概念,先通過概念抬升土地價格,然后順理成章地大興土木。可見,在政府競爭模式之下,中央調控房價變成“空調”、節能減排變成“拉閘限電”、拉動內需變成“屢拉不動”等現象,其實不難解釋;而資源賤賣、環境污染、產能過剩、安全隱患、土地財政、形象工程、貪污腐敗等問題頻頻發生,也就不足為奇。
地方政府競爭模式造成兩個非常嚴重的后果:一個是生產要素價格被制度性強制扭曲后的貧富懸殊問題,以及對環境資源的破壞;另一個是對社會矛盾長期的“封堵”,為大規模社會矛盾爆發埋下隱患。
土地、資源、環境、勞動力、技術是發展經濟最主要的要素,經濟要素的價格應由市場按照各自的稀缺程度決定。但在現實之中,土地和行政資源因政府壟斷而價高不下。產業結構直接由政府決定,導致勞動力和技術價格無法反映市場需求。土地在一級市場的招拍掛制度,從表面看似由市場定價,實則這種單一供給模式抬高了土地價格并制造出巨大的尋租空間。這種一級市場政府壟斷,二級市場、三級市場則市場化的模式,不但是官商結合的直接誘因,也是政府競爭的直接動力。
可以說,這種以地方政府競爭模式為基本形式、以土地開發和城市建設為中心的發展戰略,潛藏著極大的風險,不僅威脅到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也必將嚴重威脅到社會穩定。
在地方政府競爭模式下,資源和環境經常被作為地方招商引資的砝碼廉價出售(甚至無償使用),當這種掠奪式開發的后遺癥開始顯現時,從中受益的官員很可能早已高升,如此一來,問責制也只能停留在紙面上了。
由于政府直接決定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其實相當于間接決定了要素價格。但是,教育的結構調整和市場的自發調整機制往往趕不上政府改變政策的步伐,從而導致就業市場的大起大落和要素價格的畸形。全國的現狀是,低附加值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過剩、政府投資的“鐵公基”項目過剩、高附加值的服務業嚴重不足。因此,一方面是白領過剩導致的工資水平偏低和嚴重的大學生失業,另一方面是藍領短缺引發的“用工荒”;一方面是掌握資本和技術的人才留不住,另一方面是國內的廉價勞動力出不去。其背后深層次邏輯,正是經濟社會活動中的行政干預所造成的非兼容問題之冰山一角……
“官進民退”造成改革的倒退
與此同時,在近些年的“官進民退”背景下,政府通過行政壟斷,將銀行、石油、電信、電力等真正值錢的產業都掌握在手,私人企業要么經營鞋、服裝、電器等低附加值,且無須權力資源的日耗品;要么依附于權力,與政府官員或者國企領導編織一條“食物鏈”,比如經營房地產,或者石化、金融等壟斷行業的下游產業。
然而,低附加值的行業不但不易賺錢,而且備受需求市場影響,相反依附于權力卻能獲得無風險的暴利。比如,2008年受國際金融影響,江浙粵等地大量虧損的實業資本轉入房地產后,在接下來的房產大牛市中賺了個盆滿缽滿,其實就是從地方政府土地財政中分到了一杯羹。權力不直接創造財富應是常識,市場經濟按要素分配也是常識,但權力通過壟斷能讓自身成為最“貴”的要素,這種權力造成的財富逆向分配反過來強化了官商結合的模式。
“官進民退”造成國企改革的倒退,這也是權力越過界限,導致市場經濟與強權政治產生非兼容問題的明證。現在許多人寄望于通過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來深化改革,但有一點不可忽視:事實上,國企改革的首要問題,并不是國企作為一般意義上的企業的改革,而是國企經營管理權的改革,亟須解決國企的定位與監管問題。
不妨以通過發生在過去一年里的兩件熱門事件說明這個問題:2011年初,前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涉嫌違紀被免職,隨著他的落馬,中國高鐵“大躍進”熱潮開始降溫。劉志軍無疑只是中國落馬的腐敗官員之一,不同的是,他不但是堂堂一國鐵道部的行政首長,還是政企不分的“鐵老大”的大老板。雖然這樣的雙重身份也意味著他有雙重目標:既要提高鐵路的運行效率和服務質量使全民享受交通便利,又要為鐵路企業法律上的主人(全民)努力保值增值,但事實上,由于國有資產本身存在的所有人缺位,加上運行過程中的監督缺位,這兩個目標他都可能無法實現、也不必實現,轉而追求個人短期利益目標。
另一件事,則是中石化廣東分公司的“天價酒”事件。換個角度看,此類事倘若發生在私企會是怎樣,無論私企發生這種事情概率多么小。如果是中國一家上市私企,為不影響股價也可能會做內部處理,但對當事人絕不可能降職留用,對“泄密者”則一定會有所獎勵,無論泄密者出于何種目的;如果是一家未上市的企業,一定會通過司法途徑追回損失,并將當事人繩之以法。但這種邏輯在中石化卻變成了自查自清和嚴懲泄密者。更奇怪的是,這樣的公司竟然能以每天上億元的利潤躋身“中國五百強”之首,同一個市場,不同的游戲規則、不同的利潤回報,究其原因,當然應該看到,國家將具有巨大經濟價值的資源無償或低償授予了壟斷國企,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很少的資源稅和資源使用費。然而,除此重要因素以外,更深層次的原因應在于:權力集團為了完成對超級利益的瓜分,并形成權貴資本和家族壟斷。
事實上,官商結合模式有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是政府本身就是“商人”,直接經營企業;另一個是,政府雖不直接經營企業,但卻越過市場,直接決定資源與財富的分配。因此,從廣義上看,“官進民退”不但指國企和私企的進退關系,也包含公權力膨脹、私權利萎縮,這是一種結構上非兼容造成的問題。在官商結合的模式下,無論企業還是個人,最大的動力不是發揮自己才能和積極性去創造財富,而是通過接近權力、綁上官員直接食利,這種與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非兼容的模式難以造就優秀的企業家,但卻會形成一個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的權貴資本集團。它不但破壞市場規則,而且逐漸成為一股能夠左右歷史走向的強大勢力。
“功夫在詩外”,經濟亦如是
對中國經濟而言,最讓人擔心也最引人深思的,乃是可能面臨著一個關于速度與方向的哲學問題——有這樣一則寓言:在一架高空飛行中的飛機上,機長向乘客們宣布了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好消息是,飛行速度超過先前的預計;壞消息是,飛行迷失了方向。現實之中,擺在中國經濟面前的最大考驗,正是如何通過“安全飛行”實現科學發展的嚴肅命題。
今天,我們仍然要補市場經濟的課。所謂計劃經濟的本質,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的名義,通過權力的層層干預,追求經濟增長的規模與速度;而市場經濟的要義,則是在保障私有產權的前提下,通過市場的充分競爭,實現財富創造的持續與共享;但凡市場競爭充分、產權結構清晰的國家,必是市場成熟、社會多元、權力受限的國家,而集權傳統濃厚的國家則會通過權力干預的途徑壟斷社會財富。
只有建立在自由平等、公平競爭、權力制衡基礎上的政經體制,方可適應日益開放和多元化的大勢,激發企業家、管理者、技術精英、生產者們的創造才能,并通過基于自愿、協商的“動態和諧結構”(朱敏,2011),協調該體系內人們各種才能和積極性,也就是“企業家精神”或者叫企業家才能。今天,中國正在大力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絕不能忽視“企業家精神”對真正意義上的創新的價值。
然而,依然存在的林林總總對企業的制度性強制或管制,以及如前所述的地方政府競爭模式和官商結合模式的愈演愈烈,正是抑制和阻礙“企業家精神”正常發揚的主要因素。這無疑需要引起我們足夠的警惕和重視。
可以斷言:對中國經濟而言,不論是短期的2012年實現“軟著陸”,還是中期的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十二五”綠色轉型,抑或是長期的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無不有賴于激發“企業家精神”,無不有賴于營造一個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而要從根本上達成這一目標,必須重啟改革,進行大刀闊斧的頂層設計和制度創新,通過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以壯士斷臂的決心告別由來已久的政府競爭模式和官商結合模式,讓中國經濟社會走上真正的現代化坦途。這是我思考“動中求變”的應有之義,也可視作對“穩中求進”一種心懷期許的解讀。
回到這期專欄的題目上來。究竟怎樣才能順利躲過眼下的經濟寒流,安然捱過這場寒冬?放大到整個中國經濟,對于哪怕是略顯悲觀的論調,也應予以足夠的重視,畢竟這早已不是簡單的樂觀或悲觀的情緒之辯。必須承認一些正在發生的趨勢,避免諱疾忌醫。
所謂“功夫在詩外”,經濟亦如是。中國經濟想要在日益復雜的內外環境中“穩中求進”,不能忽視那些詩外的真功夫。
編輯:陳暢鳴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