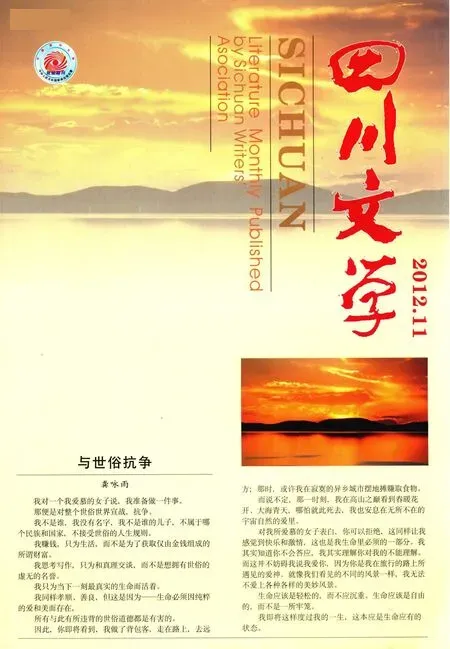給你嫂子捎個菜
□尚純江
星期天,我正在同幾個朋友說話,老家鄰居張寶給我打電話說,我的發小兼好友李建被抓了,被判了刑。我一點也不感到驚訝。在我眼里,李建進監獄,只是早晚的事兒。這是我前年回家時得出的結論。
那次探親,幾個鄰居到我家串門。換上便衣拖鞋,說話喝酒聊天,我很高興。鄰居關系處得好,說明我不在家的時候妻子很會處事。
一天晚上,鄰居張寶來我家看我。張寶現在一家民營企業打工,日子過得很拮據。夜里十一點了,張寶還沒有走的意思。我知道,張寶一定有事向我說。他這人就這樣,求人的事兒從來張不開口。
有事兒?我說,別扭扭捏捏的,只要哥能辦成的,哥不說二話。
有點事兒。這事你保管能辦成。是你侄兒改名字的事兒。孩子的名字在入電腦時派出所給入錯了,去了幾次人家不給改。
那不是小菜一碟?明天我就去辦!我答應得爽快。
我想,本來這名字輸錯就是你派出所的責任,發現錯了你原本就該給人家改過來。何況那所長李建是我的發小,從小到大,一塊上學,一塊當兵,像親兄弟一樣。他轉業后分配去了公安局。這小子能干,幾年功夫就當上了城郊派出所的所長。
但我發現,一向熱心腸的妻子卻狠勁剜了我一眼。
張寶聽了我的話,小眼睛樂成了一條縫,樂顛顛地回了家。
他走后,妻說,別看你和李建是發小,老伙計,這事不定好不好辦哩。聽說,李建眼里認得錢不認得人。
這算個啥事呀,咋?憑我倆的關系,他不給辦?再說,這事本來就應該給人家辦,作風好一點的話,辦了還得給人家道個歉!你看著,我去了,事得辦,酒還得讓他管!我說。
你就吹吧你!妻子說。
第二天,我給李建打了個電話。李建說,你看看你看看,你回來了也不打個招呼。那好,等會我去你那,請你吃飯。
我說別,我有事找你,到時我請客。
他說,哪能讓你請客?改個名字,多大一點事兒,你就來吧。
我在妻子詫異的目光中騎上電動車,去了派出所。
果然,李建在辦公室里等著我。等我把張寶孩子改名字所需要的有關手續交給了李建,李建就把內勤叫到辦公室,說,把這事辦了。
這事辦得才叫爽!我高興地拍了拍李建的肩膀,說,謝了啊,今天我請客。
你是打我的臉吧?也不看這是在誰地盤。在這里我是哥你是弟,得聽我的。再說,你輕易不回家,讓你請客,笑話!
行!今天你請,明天我請。我給妻子打了電話,說,中午不回去吃飯了,李建請客。
我倆就嘮著嗑,說些幼年上樹掏鳥蛋下河捉魚的趣事。
吃飯時是在蒙古飯店,邀了幾個幼時玩伴。蒙古飯店別具風格,客房都是蒙古包,充滿蒙古風情。幾個少時的玩伴很久沒見面了,見面特別親。席間推杯換盞、觥杯交錯。“關系淺,舔一舔;關系鐵,喝出血”。李建最夠朋友,喝了個一塌糊涂。就在我們大呼小叫的時候,李建接了一個電話,嘴里含混說,哥們,對不起了,你嫂子在家沒有吃飯呢,我給她捎個菜,先走一步了。說著話,邁著踉蹌的腳步,徑自走了。
看著他的背影遠去,我心里嘀咕:這人真喝多了?不是一口一個他請客嗎?就這樣走了?
這時一個玩伴把嘴貼在我的耳旁說,想讓李建掏錢請客,沒門!
我一下明白,李建真像人們說的那樣,逃了。忙說,沒事,這帳是我的。
誰知到我算帳時,我卻傻了眼。連菜帶酒,本來就三五百塊錢的事兒,卻一下子上千還冒了。我問老板,太坑人了吧你?哪有這么多?
老板拿著賬本向我說,剛才李所長不是捎了一個菜嗎?
我說,是啊。別說一個,就是捎三五個,也沒有那么多。
老板說,你知道他捎回去的是啥菜嗎?
啥菜?我問,不會是鮑魚魚翅吧?我知道這個飯店沒有這種菜。
鮑魚魚翅倒不是,只是一只烤全羊,外加一瓶劍南春。
烤全羊?劍南春?李建啊李建,不瞎不瘸的,你怪狠啊你!
心里這么想,帳還得結。還好,把張寶的事兒給辦了,我也不虛此行,雖然被宰的感覺不大好。
然而讓我始料未及的是,后來張寶到派出所去了幾趟,事兒也沒給辦。
我的探親假完了,走了。據說后來有人給張寶出了個主意,說啥人也別找,塞李建兜里一千塊錢啥都有了。張寶照章辦理,果然小孩的名字很快改過來了。
妻子在電話里跟我說起這事,埋怨說,你不是有能耐嗎?咋沒辦成事?沒辦成事不說,咱還搭里面一兩千塊錢!
我無言以對。
我想,這種人當所長還能長久?嘿,你還別說,果然此后不久,李建沒當所長了,只是人家竟然提升了,進了局領導班子。
但我心里仍然固執地想:他這樣還能長久?
果然,這不就傳來了這個消息:李建進了監獄。
我后來聽說,李建說的“給你嫂子捎個菜”是他慣常的把戲,只要是熟人辦事請客,他都要捎個菜回去。其實,那菜他根本沒拿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