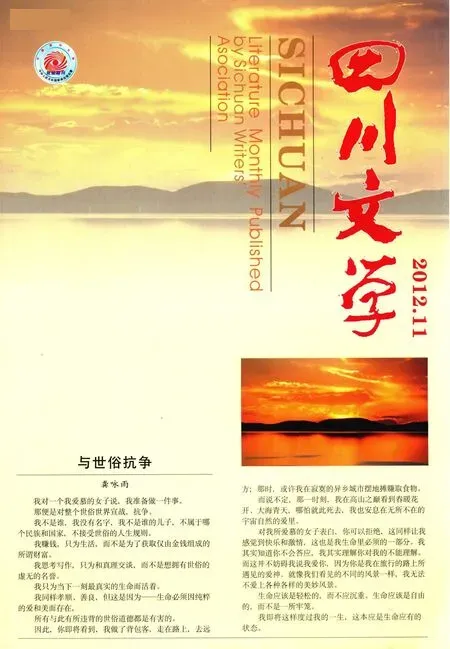天涼好個秋(三題)
□許冬林
舊時天氣
秋天是舊的。實實在在的舊。
躺在床上,聽黃昏的雨,雨是舊的。不用推了窗去看,單憑這霏霏的雨聲,便知道那雨是瘦細瘦細的。朦朧中,覺得那雨似乎是生了毛的液體。是黃梅天生了菌毛的液體,一直耗在陰暗的瓦罐里,終于待到深秋了,被高高端起,滿空里灑下來。
七八歲時,父母在雨天里吵架,平日里攢下的怨和怒,終于在雨里像列車到達站點。二十八年前的那個小女孩,無處安放她的惶恐無助,躲在屋檐下,兀自看雨。那雨也是瘦的,飄搖著,一如此刻。十八年前,懷著早戀的憂傷,扛著一把花布傘走在鋪滿金色梧桐葉的沙路上,傘頂之上的天空,也飄飛著這樣的細雨,無著無落地飄著。
歲月疊增,一層層,如同巖石的紋理,而秋雨,還是舊的。舊得瘦薄,舊得寒涼。
舊時天氣舊時衣。是的,衣也是舊的。
這樣微雨的天氣,天光穿過窗外并不疏朗的南方的香樟葉,落在室內一架長長的掛衣架上。掛衣架上的衣服多半是去年置下的,中式的民族的為主,兼以擠幾件今年新添的。年歲漸長,置衣的激情也是一年不如一年。半新不舊的那幾十件小襖或旗袍,被心思沉重的天光暈染,竟也越發呈現出年代久遠的古舊之色來。若要起身去聞,想必那紋理之間散發的,不是我的氣息,而是明朝的殘磚瓦礫的味道。脂粉轉身又凝作了富含碳酸鈣的石頭,胭脂盒子上生了厚厚青苔,一切都老舊老舊的。
我也是舊的。一日一日,兇猛地舊下去。
習慣是舊的。在不上班的日子里,還是像從前,喜歡在秋天百無聊賴地睡覺,睡一下午,睡那睡不著的覺。晴天里,喜歡躺在床上,看窗外的夕陽在西邊一寸一寸沉下去,終于像一塊橘子糖,慢慢溶化在灰藍色的水里。雨天,就干脆和一床素衾、一架衣服糾結在灰藍色的空氣里。直到天已晚透,終于點了燈,這才開始活動,仿佛一頭晝伏夜出的獸。晚上,散步,順帶購物,然后提燈,看書,或者網上看熱鬧。
日子也是。舊的多,新的少。記得從前,手中是有一大把的明天——少年時喜歡躺在春風浩蕩的江堤上,一邊嗅著馬蘭花的隱約清香,一邊空自描畫著二十歲三十歲的遙遠自己,該是怎樣的不凡模樣!如今,那么多的明天都早被我過成了昨天。如今,一雙蹄子終于沾了泥著了地,已經現實了,不再喜歡對鏡空自許。知道明天永遠是未知的,無數個明天還是未知的,只有昨天,一日日在行囊里沉淀下來,成為我們的尾巴。我們拖著長長的尾巴向中年和暮年緩緩走去,仿佛舊時鄉下生殖力極其頑強的女人,身后是高高低低的一長排衣衫粗陋的孩子,扯著母親的衣襟隨行。
生活越來越慢,不喜歡趕了。能坐下來,一個人看陽臺外的樹與日影子,一看一個時辰過去。無謂的期盼也漸漸少了,更在意過好每一個今天,哪怕素色,哪怕無驚無險。人群之中,更習慣去做一個配角,做一片安靜的樹葉。生活的內容里,新意漸少,慢慢將柴米油鹽奉為正道,成了十足良民……這舒緩與淡定,像從前父母終于安穩下來的中年。
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時家。這情懷,是中年情懷,無限情意揀揀疊疊縫縫起,舊上做文章。
喝茶男女
許多故事,只一個手勢,或低眉欠身,便道盡底細。譬如喝茶。
喜歡一個人坐在茶樓里,看那些過眼男女,且看他們侍弄茶事的瑣碎里,便能猜出了情到幾分。
豆蔻妙齡的一對人,相對的時光甜膩。那甜,絕不是五六十年代的紅糖水的甜,是黃梅天窗臺上稍稍化了一點的巧克力的甜,軟膏形的,摻和成一塊,分不清。明明兩張椅子,卻偏要擠坐在一張椅子上。女的或扎一個簡單的馬尾,短,戳在腦后;或長碎,秋草黃,散在脖子上,其實并不長,能拖到肩的沒有幾根,現在的年輕人沒有耐心養頭發。一般,女的把頭塞進男的懷里,頭發揉得不大像樣子,也無妨得很,有青春打底子,怎么都有味。男的一手攬著懷里的嬌人,一手彈撥著一根煙。吹出來的煙舞,沒什么形狀,像冬天放晚學在田埂上點起的一把野火,烏煙瘴氣的一片,燒得旺不旺不重要,就圖個熱鬧。喝奶茶,吃爆米花,也偶有面包或牛排。女的一只手撥弄飲料吸管,一只手撥弄手機,似在讀短信,咯咯地笑。他們在一起,不為喝茶,不為說話,似乎只為身體膩在一起,再各玩各的事。
從茶樓的角門又進來一對,看上去男的不到四十,微微有點不著痕跡的發福,女的大約不到三十五,清瘦。男的在前面,有點紳士,舉目找位子。女的安靜,在后面,隔男的有半丈遠的距離,有點羞澀和拘束,用手指將幾根劉海往耳后掖。想必,這茶樓,不常來,這一次的聚不容易。他們,是一對舊戀,今日重逢?還是,男的是部門上司,女的在他手下做文秘?今日一道出差,在這里找張位子不深不淺地說幾句心里話?大約還坐不久,孩子還托在幼兒園里,女人心里盤算著,回去怎么順路接上孩子。也有可能是一對網友,鍵盤上說了很多親密話,今天終于熬不住,見了,回去,各自還要瞞著老公和老婆。男的一伸手,做一個半紳士式的請坐動作,女的一低頭,走過去。他們尋了一處臨墻無窗的桌子坐下,各自淺笑,并不說話。
靠他們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是一對中年男女。男的成熟得有點滄桑感,頭頂的發根根亮,但稍稀。肩和背把灰色上衣撐得像風已停息的沙丘,高聳而厚實。女的長頭發,燙著小波浪,是不易察覺的栗色。妝化得精致,只是面上落寞而憂傷。兩人喝綠茶,桌上的點心沒大動。女人低眉,一只手托著下巴,目光向著低處迷離。不知道她眼里有沒有淚,如果有,一定也只落在她自己的腳尖。偶爾,伸出細長的另一只手,給男人斟茶。男人也不道謝,也不點頭,只呆呆地看她修長的手臂,看她斟茶。男人偶爾接電話,有點煩躁,那口氣似乎是一個局長或經理的。另一只手夾著煙,低低地抽,燒得很快,像高爐里的焰,洶涌得很,沒什么煙氣。想必是一對苦戀,已經拖了七八年,女的深情地等,等到無言;男的身后的擔子還沒交卸掉,抱歉到無言。
是下午三點來鐘,正門口進來一對。女的急匆匆沖在前面,背著精致的小包,男的跟在后面,手里拎著三四個盛女裝的商場膠袋,閑悠悠。一到廳里,女的目光四下一掃,奔向靠窗的一張桌子。剛坐下,伸手招服務員,一副當家婆模樣。女的點好了,男的才到了身邊。放下幾個袋子,長工一般,男的跌在椅子上起不來,嘆氣,喊累。看來是逛街累了渴了,進來休息。女的伏在桌子這邊,拿眼瞅男的,嗔笑,手一指,男的把袋子遞過來,女的在翻,滿臉的笑嘩啦啦。服務員端上來一壺茶,只有一壺茶,男的坐直身子端詳玻璃壺里的茶葉,女的也放下手中的衣服,擠過臉來看,兩個人碎碎地說著,議論茶葉,也議論一壺茶的價錢。大約盤算,這樣的一壺茶錢,在家里夠喝幾天。日子,就是這么掐著算著過來的吧。
街上的燈次第亮起來,茶樓里又走進一撥又一撥新的陌生面孔,下午的那些男女,不知幾時,從正門角門里一個一個地走了。一杯杯茶前,一對對男女,一場又一場悲歡人間事。
人漸老,話漸少
一場雨后,便覺風是涼了。
年輕人在房子外面,在香樟樹下,和蟬一起聒噪。他們話還多著呢。他們那里,天氣還是熱的,需要抱怨,需要踮著腳期盼真正的秋后西風涼。
我是不急的。
其實,說老,也不是太老。未到五十,再退退,還未到四十。但是,當自己愿意一切慢下來時,真的是覺得自己老了。老到人前人后話語儉省,連嗟嘆都覺得多余。
舊時閨密一年未見,竟也不急不提,電話也不打。偶爾心底閃過會一會的念頭,一個轉身晃悠,又覺得可以略過去。放假了,她要打麻將吧?她要陪孩子上興趣班吧?她在和老公慪氣不想見人吧?想想,見了面也無甚可說。老公,孩子,家務,公婆,領導,房子,貸款……都是車轱轆上的話題,滾過來滾過去,翻不出新意。這樣一想,就覺得許多唾沫都可以咽咽,許多套話老話陳話都可以略去不提。
似乎是真的老了。即使遇見自己欣賞的男人,也不再像十幾歲的小姑娘那樣,小蜜蜂一樣叮過去,嚶嚶嗡嗡,制造歡心。至多不過如此:走過他身旁,微風一樣地走過,偶爾回頭笑笑,連寒暄都可以省略;或者,揀一個安靜的角落,看他和別人說話,看他在與別人談論問題時露出來的一顰一笑。了解一個人,欣賞一個人,盡可以選擇這樣一個隔岸的位置:不出一語,不說一句,風清云淡,過后,思量,或不思量,也都是微風一樣。
近博情怯。以前,在自己的博客里,像個菜農撒種子,一畦一畦,把個漢字種得密密麻麻不透氣。現在啊,來得少種得少,總覺得那博客也不是自己的。知道每日里都有目光往這邊掃,忽然幽幽怕起來,不敢隨意吼嗓子,覺得端出來就該是堂堂一臺戲。于是破帽遮顏,倉皇繞過去。江湖漸老,博客里兜心思的話兒也漸少。
對于諂媚逢迎之詞,使用起來,更是覺得口拙手生,于是遇見那些坐在臺上的人物,索性閉了口,讓能量豐富的人去轟炸吧。人前被人捧,被人羨,也做不到感恩戴德禮尚往來回敬人家一籮筐贊美;背后遭人謗,遭人譏,也不會動用長長短短的句子和人家理論。人世一趟,遭毀遭譽,都難免,笑一笑,煙消云散。對于橫眉怒目批判周圍人事,也沒興趣,這個世界的聲音已經夠雜夠吵人,收收嗓子,于人于己,都很綠色環保。
歡喜和悲傷這樣一些色彩濃烈的詞語,在自己的筆尖已是漸走漸丟。關于內心晴雨的日記,也是漸寫漸短,直到,慢慢喜歡使用悠長的省略號。早晨看缸里睡蓮盛開,丟一個微笑,順便借水照一照自己的影子。美麗都會凋零,這一刻,有過盛開就好。依然會有悲傷,不過,已經習慣一個人慢慢消受,如海綿吞掉寫字臺上不小心潑下的藍黑墨水。方法簡單,不過是,花一個夜晚,或者兩個,或者再多一點的時間,將悲傷徐徐注水稀釋,如湯藥飲下,心里的城池又堅固一層。不再在雷電交加的夜晚,慌不擇路找朋友倒苦水,禍及他人。
看看窗外眾人頭頂的樹,忽然覺得,每一片葉子該是樹的詞語,每一枝綠蔭,該是樹說出的句子,那么自己呢?也許是另外的一種落葉小喬木吧,人生的前半截,識物,識人,歷事,憂心,有那么多的話語要向這個世界表達。可是,當車輪翻過某道山坡某個山頂,我的葉子也開始一片片落掉,開始習慣沉默。一些是不用說,一些是不可說,悟得七八成透,就覺得許多話都是多余,或者是多余的修飾。不說了,秋盡一身輕。
一佇足,一低眉,風就涼了。水上蓮花閉合,殘荷滿塘。大路之上,那么多人影遠去如豆,只余塵煙渺渺。看似漫長,不過須臾之間,這歲月。所有的話語,最后發現都是詞不達意,所以,我愿意早些抽身出列,停下來,收了口,來意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