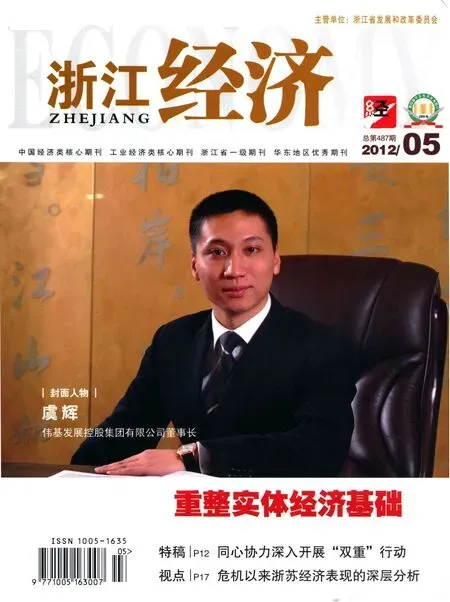危機以來浙蘇經濟表現的深層分析
□文/朱李鳴任正委
金融危機以來,浙江經濟波動較大,經濟總量占全國比重跌破7%,比“十一五”時期下降了0.4個百分點。江蘇經濟總量穩居全國第二位,占全國比重達到10.3%,比“十一五”時期提高了0.2個百分點。江蘇能在逆境中趕超浙江,體現了經濟轉型升級的成效。
經濟表現呈現六大差異
經濟總量差距擴大。2010年,浙江、江蘇GDP分別為2.8萬億元和4.1萬億元,差距從2005年的5181億元擴大到1.3萬億元。2009年浙江的人均GDP被江蘇反超103元,2010年差距擴大到1129元。2011年以來,經濟形勢均呈下行態勢,浙江下滑2.9個百分點,下滑速度快于江蘇和全國。
增長貢獻率不同。一是內需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于江蘇、外需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于江蘇。2010年,內需、外需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91.7%、8.3%,與江蘇的差距為1.1個百分點。二是投資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于江蘇,消費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于江蘇。2010年,投資、消費對浙江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49.5%、42.2%,前者低于江蘇2.2個百分點,后者高于江蘇1.1個百分點。
投資增速明顯落后。從總體上來看,2010年浙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2376億元,僅為江蘇的53%;“十一五”期間浙江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速為13.7%,落后江蘇近10個百分點。分資金來源來看,浙江的港澳臺商投資在2007年的水平上幾乎是原地踏步,2010年外商投資反而在2006年的水平上有所下降,“十一五”期間內資、港澳臺商投資和外商投資的年均增速分別落后江蘇8個、4個、6個百分點。分行業來看,浙江的第三產業投資增長相對較快,與江蘇的增速差距相對較小,但制造業投資增長乏力,2010年浙江制造業投資增速僅為10.7%,落后江蘇15個百分點。
出口結構與層次相對低端。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兩省的出口額在2009年都經歷了一次回落,2008-2010年浙江出口年均增速12.1%,高于江蘇2.2個百分點,但出口結構與層次的提升慢于江蘇。從貿易方式來看,加工貿易比重偏低。浙江出口以一般貿易為主,占比達到80%,加工貿易僅占18%;江蘇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分別占48%和47%。從產品結構來看,高附加值產品比重偏低。浙江出口的機電產品占40%左右,紡織服裝產品比重高達30%;江蘇機電產品出口占比70%,紡織服裝占比僅10%左右。從主體結構來看,外資企業出口額比重偏低。2010年浙江外資企業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32%,江蘇為71%;私營和其他企業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1%,江蘇為18%。

地方財政收入增速較慢。從一般預算收入來看,2010年浙江一般預算收入2608億元,與江蘇的差距從2008年的798億元擴大到1472億元;2008-2010年浙江年均增長16.5%,慢于江蘇5.7個百分點。從土地出讓金來看,浙江2010年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全國的1/7,但2011年以來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業相關稅收大幅減少。從企業稅收來看,2010年浙江企業所得稅收入374億元,與江蘇的差距從2008年的97億元擴大到180億元,增速落后于江蘇6.5個百分點,特別是2011年制造業稅收增速從年初的33.6%逐月滑落至27.8%。
發展主體實力遜色。從企業規模來看,浙江不如江蘇大。浙江入圍“2011中國企業500強”44家,落后于江蘇的49家,浙江之首省屬物產集團排名65位,與排名42位和51位的江蘇沙鋼集團和蘇寧集團仍有較大差距,況且后者是民營企業;浙江入圍“2011中國民營企業500強”144家,連續13年上榜企業數居全國首位,但相比2006年入圍203家可抗衡蘇粵魯三省總和,領跑優勢明顯減弱,江蘇入圍118家趕超之勢明顯。從企業效益來看,浙江不如江蘇好。2010年浙江私營工業企業4.67萬家,比江蘇多3000家,但工業總產值2.28萬億元,利潤總額1178億元,流動資產周轉次數1.8次/年,分別只有江蘇的70%、65%和60%;外資企業工業總產值1.31萬億元,利潤總額978億元,流動資產周轉次數1.7次/年,分別只有江蘇的36%、36%和74%;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工業總產值6722億元,利潤總額407億元,分別只有江蘇的68%和64%。
差異背后的六大因素
現階段浙江經濟表現落后于江蘇的深層次原因可以追述至三個歷史節點:(1)上世紀90年代后期,浙江仍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依靠外貿出口“一條腿”走路,而江蘇大力引進外資,充分利用外資發展本地經濟和提升本地產業層次;(2)加入WTO以后,浙江依靠外資出口企業優勢,出口增長帶動了經濟成長,但國內資源要素趨緊、成本趨高,海外貿易戰爭頻發,國家于2004年加強宏觀調控,此時浙江的企業、資本開始游離于省內實體經濟之外,而江蘇大力實施“科教興省”戰略并優化產業結構;(3)2008年金融危機后,浙江制造業企業大量外遷,省內制造業投資增速下滑,而江蘇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率先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并取得明顯成效。從上述三個歷史節點的比較可以看出,現階段浙江經濟表現落后于江蘇主要由客觀因素和自身戰略舉措實施等關鍵因素共同導致的。
(一)客觀因素
創新要素基礎薄弱。由于歷史原因,國家在浙江的科教投資很少,導致浙江科技、人才和高等教育等創新要素積累不多。在科研機構方面,轉型升級前的2003年浙江擁有縣及縣以上國有獨立的研究開發機構108個,高等院校辦科研機構421個,工業企業和其它單位辦科研機構1889個,分別只有江蘇的60%、9%和90%。在人才資源方面,2000年浙江每十萬人擁有大學文化程度人口3189人,在全國排名第17位。雖然10年來增長較快,2010年達到9330人,排名全國第11位,但與江蘇的差距從2000年的728人擴大到了1485人。在高等教育方面,浙江僅有浙江大學1所“211”院校,而江蘇擁有11所。創新要素的不足大大削弱了浙江承接發達國家高技術產業和服務外包轉移、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能力。
土地資源更為緊缺。從土地資源存量看,浙江與江蘇國土面積相當,同為資源小省,但浙江土地資源更為緊缺,只有江蘇的1/3。江蘇仍有廣袤的蘇北平原可以利用,但浙江欠發達山區有著生態環境保護的更高要求,全省的工業用地指標已相當緊缺。從土地資源開發潛力看,浙江土地開發強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按照目前年均實際建設用地情況計算,約200多萬畝的可供土地不到10年將全部用完,僅剩的土地挖掘潛力在于低丘緩坡綜合開發利用和灘涂圍墾造地,但涉及生態環境保護和相關政策問題,實施難度很大。用地指標緊缺,一方面使得浙江引進大項目難度更大,另一方面高企的地價房價推高商務成本導致企業經營困難,大量的企業已經向江西、安徽等中西部地區轉移或建立生產基地。
享受中央資源較少。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享受國家優惠性政策支持很少,而江蘇在鋼鐵、機械等基礎產業上受到國家的大力扶持。與江蘇國有、私營、外資各占1/3的企業主體結構不同,浙江的企業體系以中小民營企業為主,一直缺少大型國有企業。同時,中央擴大內需4萬億投資中涉及浙江的投資只有839億元,占比僅為2.1%。國有企業和中央投資較少,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浙江轉型升級的步伐。
(二)關鍵因素
結構轉型不快。在前一段轉型升級的過程中,先進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發展相對遲緩,過于依賴低端產業的增長方式尚未根本轉變。工業領域,傳統紡織業仍然是第一大行業,占比達到11.4%,高于江蘇的6.7%;規模以上企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全國比例為4.42%,僅為江蘇的20.5%。服務業領域,“十一五”期間服務業比重僅提升2個百分點,落后于江蘇兩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江蘇在新興產業選擇和培育上把握時機、搶抓苗頭、因勢利導。以光伏產業為例,江蘇在全國率先培育,總產量位居全國首位,已形成以尚德公司為龍頭的40多家光伏企業集群,贏得了“全國光伏看江蘇”的美譽。浙江傳統優勢產業正在轉移與新興產業發展緩慢,導致區域實體經濟過快萎縮,培育能夠帶動新一輪經濟成長的主導產業群十分緊迫。

創新驅動不足。江蘇在本世紀初就開啟了以創新為核心的第三次轉型,突出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南京、蘇州和無錫等城市都已經提出與“創新”有關的城市發展戰略。蘇州工業園獨墅湖科教創新區近年來集聚了一大批國內外知名大學和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中國科技大學蘇州研究院、西交利物浦大學已成為蘇州高等教育和自主創新的重要支撐。由于本土科技底蘊不足,浙江在發展創新型經濟方面推進動力不強,科技創新能力與江蘇差距拉大,過于依賴一般仿制加工的增長方式尚未根本轉變。研發和專利方面,浙江大中型工業企業研發項目1.1萬項,R&D經費272億元,僅為江蘇的61%和49%;累計擁有發明專利78278件,僅為江蘇的63%。新產品方面,浙江大中型工業企業新產品項目數、開發經費、銷售收入分別為1.4萬項、350億元、6283億元,僅為江蘇的67%、49%和67%。技術、新產品與市場拓展能力等創新條件不足,已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產業轉型升級步伐。
開放帶動力不強。江蘇在上世紀90年代就經歷了以擴大對外開放為核心的第二次轉型,推動了開放型經濟大發展。近年來,蘇州大力引進重大產業項目和創新型、總部型項目,全市形成軟件開發、動漫創意、研發設計、生物醫藥、金融數據處理和物流供應鏈管理等服務外包集群,國家級開發區達到9家,昆山綜合保稅區和蘇州高新區綜合保稅區投入運營。盡管浙江經濟的外向型特征非常明顯,但主要依靠外貿出口和境外投資,在吸引國內外高端要素和利用外資方面與江蘇差距拉大。世界500強企業落戶浙江只有92家,遠遠落后于江蘇的400多家。截至2010年底,浙江外資企業28769家,注冊資本1069億美元,投資總額1832億元,僅為江蘇的56%、39%和36%。開放不足大大削弱了浙江承接發達國家高技術產業和服務外包轉移、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能力。
對比分析的有益啟示
江蘇在金融危機的逆境中趕超浙江的事實表明,面對復雜多變的宏觀經濟環境,提高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水平,必須在發揮原有優勢的同時突破經濟增長的瓶頸。在轉型升級的初始階段,必然會有較大的經濟社會陣痛。因此,政府必須積極地有所作為,通過規劃、政策引導和平臺搭建等有效服務,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當前浙江似乎陷入了“科技人才基礎薄弱→創新能力積累不足→新興產業發展滯后→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政府財政收入增長受限→新興產業和創新要素投入能力弱化”的不良循環之中。要走出這一不良循環,學習江蘇的經驗,以創新和開放驅動經濟轉型升級。
啟示一:必須加快結構調整。結構調整是經濟轉型升級的最核心環節,浙江要圍繞產業結構調整,優化投資結構、出口結構、地方財政收入結構和企業主體結構。在穩定和拓展出口、提高出口產品層次的同時,擴大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和工業投資。在加快中小企業轉型升級的同時,著力引進大型外企和央企,完善稅源結構。經濟轉型升級,關鍵靠轉變,基礎在培育,浙江要多層次推進產業轉型發展,引進培育現代產業集群,改造提升傳統塊狀經濟,引導產業有序梯度轉移,再創發展新優勢。
啟示二:必須強化創新驅動。自主創新是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驅動力,浙江要以培育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和創新型企業為重點,大力推進自主創新,大幅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發展創新型經濟,關鍵靠人才,基礎在教育,浙江要堅定不移地把創新驅動作為轉型發展的主戰略,把加快建設科技強省、教育強省和人才強省作為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大力度引進高層次人才特別是領軍人才和創新創業團隊,著力發展高等教育,積極推動國內外知名院校在浙合作辦學和成立教學科研聯合體。
啟示三:必須提升開放帶動。開放合作是經濟轉型升級的主要引導力,浙江要積極適應全球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調整的新趨勢,有效發揮承接國際資本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集聚功能。發展開放型經濟,關鍵靠產業,基礎在要素,浙江要實施民資、外資“雙輪驅動”戰略,發展民營配套經濟,促進外資企業降低成本落地生根,實現本地生產要素和國際生產要素的優勢組合;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對內開放力度,推動開發區轉型升級,大力度招引大型央企和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入駐;鼓勵在外浙商協會和有實力的企業在中西部重點經濟區、資源富集區、邊境口岸等建設產業園區,積極探索異地開發、定向開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