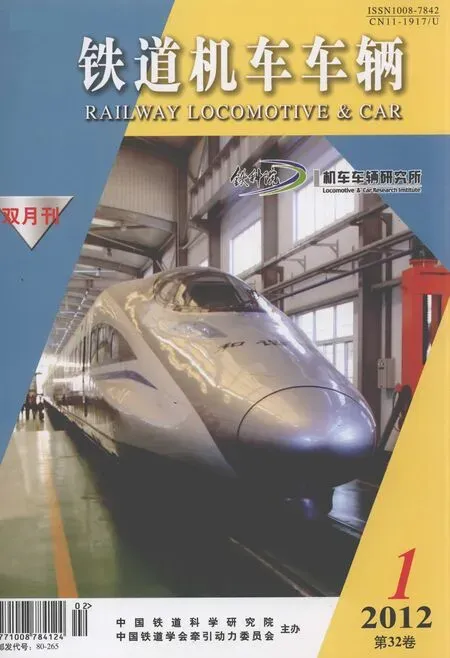基于工裝預(yù)變形的高速列車側(cè)墻尺寸偏差控制方法*
吳桃生,李志敏,王 華,馮孝忠,楊建華
(1 上海市數(shù)字化汽車車身工程重點(diǎn)實(shí)驗(yàn)室 上海交通大學(xué),上海200240;2 唐山軌道客車有限責(zé)任公司,河北唐山063035)
高速列車可以滿足長(zhǎng)距離、大運(yùn)量、高密度、短時(shí)間等運(yùn)輸需求,對(duì)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1]。側(cè)墻是高速列車的車體關(guān)鍵大部件之一,其制造質(zhì)量不僅影響著車體外觀和車體總成的裝配精度,也直接關(guān)系到列車行駛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側(cè)墻由5塊鋁合金中空擠壓型材焊接而成,變形規(guī)律復(fù)雜、各種偏差源高度耦合,尺寸偏差控制難度大[2]。當(dāng)前,我國(guó)的高鐵制造技術(shù)還處于起步發(fā)展階段,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側(cè)墻尺寸偏差控制方法,導(dǎo)致產(chǎn)品一次性成形合格率較低。實(shí)際生產(chǎn)中,只能依靠大量的火焰和機(jī)械調(diào)修來(lái)保證后續(xù)裝配工序的順利進(jìn)行,這不僅增加了制造成本、影響了生產(chǎn)進(jìn)度,更嚴(yán)重削弱了側(cè)墻的強(qiáng)度和焊縫疲勞等性能。如何有效地控制側(cè)墻等車體大部件尺寸偏差已經(jīng)成為軌道裝備制造企業(yè)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3]。
傳統(tǒng)的尺寸偏差控制方法主要立足于偏差源的定位與診斷。如Hu等[4]針對(duì)汽車車門裝配過(guò)程提出兩級(jí)故障模式的在線分類方法,實(shí)現(xiàn)偏差源的定位;來(lái)新民等[5]建立了夾具假想失效的誤差樣本模型,利用失效映射程序,診斷出夾具的失效類型和偏差來(lái)源。王華[6]針對(duì)柔性薄板裝配的特點(diǎn),引入核函數(shù)PCA方法診斷裝配偏差源。這類方法的特點(diǎn)是在檢測(cè)和評(píng)價(jià)的基礎(chǔ)上,確定各類偏差來(lái)源,再依據(jù)工程經(jīng)驗(yàn)在實(shí)際生產(chǎn)中逐一加以控制。然而,由于高速列車側(cè)墻的偏差源種類多樣且高度耦合,變形規(guī)律非常復(fù)雜,要建立準(zhǔn)確的偏差源診斷模型難度很大,導(dǎo)致上述方法在側(cè)墻生產(chǎn)中的工程應(yīng)用價(jià)值不高。
本文嘗試在側(cè)墻批量生產(chǎn)中,利用工裝預(yù)變形來(lái)平衡其他偏差源的影響,實(shí)現(xiàn)對(duì)側(cè)墻尺寸精度的控制。借助統(tǒng)計(jì)學(xué)手段,考察工裝預(yù)變形量對(duì)側(cè)墻輪廓尺寸的影響規(guī)律,利用多元回歸方法建立側(cè)墻尺寸偏差與工裝預(yù)變形之間的定量關(guān)系模型,對(duì)該模型進(jìn)行檢驗(yàn)及修正,在此基礎(chǔ)上,提出了基于工裝預(yù)變形的側(cè)墻尺寸偏差控制方法,并進(jìn)行了工程應(yīng)用,有效提高了側(cè)墻的制造質(zhì)量。
1 工裝預(yù)變形與側(cè)墻尺寸偏差定量關(guān)系模型
結(jié)合側(cè)墻產(chǎn)品結(jié)構(gòu)和制造工藝特點(diǎn),分析了利用工裝預(yù)變形實(shí)現(xiàn)側(cè)墻尺寸偏差控制的可行性,在此基礎(chǔ)上,應(yīng)用多元回歸方法建立了側(cè)墻尺寸偏差與工裝預(yù)變形的定量關(guān)系模型。
1.1 側(cè)墻結(jié)構(gòu)及制造工藝
側(cè)墻由下墻板、窗下板、窗間板(若干塊)、窗上板和上墻板等鋁合金型材組焊而成[如圖1(a)所示]。外形輪廓是側(cè)墻的關(guān)鍵控制特征,控制的目標(biāo)是使其尺寸處于設(shè)計(jì)要求的范圍之內(nèi)。側(cè)墻外形輪廓表面為三維曲面,通過(guò)在側(cè)墻不同斷面上布置測(cè)點(diǎn)[如圖1(b)所示],以測(cè)點(diǎn)y向偏差來(lái)反映側(cè)墻外形輪廓的尺寸偏差。
側(cè)墻外形輪廓尺寸偏差的主要來(lái)源包括擠壓型材本身制造偏差、焊接變形、工裝夾具影響及工人操作影響等[7]。實(shí)際生產(chǎn)過(guò)程中,各種偏差源高度耦合,當(dāng)出現(xiàn)質(zhì)量問題時(shí),幾乎難以逐一、準(zhǔn)確地實(shí)現(xiàn)所有偏差源的定位及診斷。生產(chǎn)實(shí)踐表明,在上述各種偏差來(lái)源中,型材制造偏差、焊接變形及操作影響通常處于階段性穩(wěn)定的狀態(tài)(同一批次型材尺寸波動(dòng)趨勢(shì)一致、標(biāo)準(zhǔn)操作下的焊接變形較為固定),在這種情況下,通過(guò)調(diào)整工裝預(yù)變形量可以平衡其他偏差源的綜合影響,提高側(cè)墻的制造精度。

圖1 側(cè)墻示意圖
工裝預(yù)變形量指的是在一批側(cè)墻生產(chǎn)之前,為獲得更好的外形輪廓而實(shí)施的工裝定位參數(shù)的調(diào)整量。側(cè)墻組焊工裝如圖2所示,主要由12組y向定位支撐板組成,每組支撐板包括3塊高度方向(y向)可調(diào)的小支撐板。所有支撐板的高度位置共同實(shí)現(xiàn)了側(cè)墻外形輪廓的y向過(guò)定位,因此,支撐板的y向位置對(duì)側(cè)墻外形輪廓有決定性的影響,通過(guò)合理地調(diào)整支撐板的y向高度,可以實(shí)現(xiàn)側(cè)墻尺寸偏差的有效控制。

圖2 側(cè)墻組焊工裝
1.2 基于多元回歸法的模型建立
要利用工裝預(yù)變形量實(shí)施精度控制,關(guān)鍵和難點(diǎn)在于如何建立準(zhǔn)確的“尺寸偏差—工裝預(yù)變形”模型,定量描述工裝預(yù)變形量與側(cè)墻外形輪廓尺寸偏差的關(guān)系,從而為后續(xù)的外形輪廓控制提供定量的數(shù)學(xué)公式。
在建模過(guò)程中,由于12組支撐板相互距離較大,對(duì)于側(cè)墻每個(gè)斷面,只考慮其對(duì)應(yīng)的單組支撐板的影響。此外,相對(duì)于工裝參數(shù)實(shí)際調(diào)整量,定位點(diǎn)磨損造成的高度變化可以忽略不計(jì)。
對(duì)任意一組支撐板,設(shè)3塊小支撐板高度方向調(diào)整量(即預(yù)變形量)為 Δy1、Δy2、Δy3,調(diào)整后側(cè)墻斷面輪廓測(cè)點(diǎn)Pi處尺寸偏差為Hi,由前討論可知,Δy1、Δy2、Δy3都會(huì)對(duì)Hi的值產(chǎn)生影響,為了準(zhǔn)確地了解各支撐板對(duì)側(cè)墻輪廓尺寸的影響規(guī)律,需要建立支撐板調(diào)整量與側(cè)墻尺寸偏差之間的定量關(guān)系模型。多元回歸方法常用于建立主變量與其多個(gè)相互之間不相關(guān)的原因變量(解釋變量)之間的關(guān)系公式,比較簡(jiǎn)便、實(shí)用性很強(qiáng)[8],因此本文采用該方法建立側(cè)墻尺寸偏差與支撐板預(yù)變形量之間的模型,為保證模型的準(zhǔn)確性及計(jì)算簡(jiǎn)易性,分別討論了二次回歸和線性回歸兩種情況。
多元二次回歸數(shù)學(xué)模型為

多元線性回歸數(shù)學(xué)模型為

式中i為側(cè)墻斷面測(cè)點(diǎn)序號(hào);Hi為Pi測(cè)點(diǎn)y向尺寸偏差;H′1-i、H′2-i分別為二次及線性模型的Pi測(cè)點(diǎn)y向尺寸偏差估計(jì)值;ε1-i、ε2-i為其擬合誤差;α及β為系數(shù)的估計(jì)值;Δyk為第k塊支撐板預(yù)變形量。
為獲取多元回歸模型所需的樣本數(shù)據(jù),生產(chǎn)過(guò)程中需記錄每組支撐板高度及所對(duì)應(yīng)的斷面測(cè)點(diǎn)尺寸偏差。表1以斷面測(cè)點(diǎn)P7為例,列舉了側(cè)墻制造過(guò)程積累的20組數(shù)據(jù)。

表1 測(cè)點(diǎn)尺寸及對(duì)應(yīng)支撐板高度變動(dòng)量
基于表1數(shù)據(jù),通過(guò)最小二乘回歸可得式(1)、(2)的系數(shù),從而得到測(cè)點(diǎn)P7尺寸偏差與支撐板預(yù)變形的多元回歸公式。計(jì)算得到二次回歸模型為

線性回歸模型為

對(duì)于側(cè)墻斷面其余測(cè)點(diǎn)可采用同樣的方法計(jì)算二次及線性回歸公式,從而獲得側(cè)墻斷面尺寸偏差與工裝預(yù)變形之間的整體定量關(guān)系模型。
2 定量關(guān)系模型的驗(yàn)證與分析
對(duì)上述回歸模型進(jìn)行顯著性檢驗(yàn)、擬合誤差分析和單因素子模型分析,在此基礎(chǔ)上,針對(duì)二次及線性模型進(jìn)行對(duì)比討論。
2.1 模型驗(yàn)證
回歸模型驗(yàn)證通常利用統(tǒng)計(jì)F檢驗(yàn)及多重判定系數(shù)R2對(duì)其顯著度及擬合優(yōu)度進(jìn)行驗(yàn)證,以證明模型的有效性。
首先對(duì)二次回歸模型進(jìn)行檢驗(yàn),通過(guò)分析模型方差對(duì)其顯著性及適合性進(jìn)行判斷。設(shè)α=0.05,回歸模型方差分析如表2所示,其中,S為組間平方和(回歸因子)以及組內(nèi)平方和(殘差誤差);M為平方和除以自由度得出的均方,查F分布表得臨界值F-tab=F0.05(9,10)=3.02,因?yàn)镕=69.8>3.02,所以二次模型顯著度非常明顯。計(jì)算可得到R2=0.998 4,說(shuō)明模型擬合優(yōu)度非常良好。

表2 二次回歸模型方差分析
依據(jù)同樣的方法對(duì)線性回歸方程進(jìn)行驗(yàn)證,其回歸因子自由度為3,殘差誤差自由度為16,查表可得F-tab=F0.05(3,16)=6.30,因?yàn)镕=1 999>6.30,且R2=0.999 9,所以線性模型顯著度非常明顯,模型擬合優(yōu)度同樣十分良好。
2.2 擬合誤差分析
將表1中數(shù)據(jù)分別代入式(3)、(4),將計(jì)算結(jié)果與實(shí)際數(shù)據(jù)進(jìn)行比對(duì),可得到二次模型與線性模型的擬合誤差,以此來(lái)分析兩個(gè)模型之間的精度差異。
圖3為20組數(shù)據(jù)下的二次及線性模型擬合誤差折線圖,可以看出,二次及線性模型的擬合誤差均較小,都處于小偏差范圍,從而再次驗(yàn)證了模型的有效性。此外,兩種模型擬合誤差趨勢(shì)一致,雖然二次模型精度略高,但精度差異非常小。

圖3 擬合誤差折線圖
2.3 單因素子模型分析
將回歸模型中的2個(gè)因素固定在零水平,或其他水平上,即可得到單因素子模型[9]。分別將式(3)和式(4)中的兩個(gè)因素置零,可得到3塊支撐板子模型。
獲得的二次回歸子模型為線性回歸子模型為


圖4為單因素子模型的回歸曲線圖。由該圖可以看出:支撐板1,2的預(yù)變形量與測(cè)點(diǎn)P7的尺寸偏差正相關(guān),即若Δy1、Δy2增大,則單因素影響下的測(cè)點(diǎn)尺寸偏差趨向于增大,支撐板3預(yù)變形量與其負(fù)相關(guān),若Δy3增大,單因素下的偏差趨向于減小。其中Δy2對(duì)P7測(cè)點(diǎn)偏差的影響程度最大,Δy1最小。此外,在一定范圍內(nèi),線性子模型與二次子模型曲線圖形狀差別很小,兩種模型下工裝預(yù)變形對(duì)側(cè)墻尺寸偏差的影響規(guī)律相似。

圖4 子模型回歸方程曲線圖
由上述所有檢驗(yàn)及分析可知:
(1)側(cè)墻輪廓尺寸偏差與工裝預(yù)變形定量關(guān)系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良好;
近年來(lái),通信傳輸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發(fā)展迅速,新技術(shù)層出不窮。日新月異的通信技術(shù)為建設(shè)堅(jiān)強(qiáng)可靠的電力通信傳輸網(wǎng)創(chuàng)造了條件。目前,通信業(yè)界采用的傳輸網(wǎng)技術(shù)體制主要有 SDH,DWDM,ASON,OTN,PTN等。目前,國(guó)內(nèi)地市電力通信網(wǎng)仍以 SDH 網(wǎng)絡(luò)為主。
(2)兩種模型擬合誤差均較小,揭示的單因素影響規(guī)律相同,雖然二次模型精度略高,考慮到計(jì)算的簡(jiǎn)便性,在后續(xù)的尺寸偏差控制中,可以使用線性模型進(jìn)行預(yù)變形量的計(jì)算。
3 基于工裝預(yù)變形的側(cè)墻尺寸偏差控制方法
3.1 尺寸偏差控制流程
將尺寸偏差—工裝預(yù)變形定量關(guān)系模型應(yīng)用于側(cè)墻實(shí)際生產(chǎn)中,通過(guò)調(diào)整所需的工裝預(yù)變形量以獲得更小的尺寸偏差,實(shí)現(xiàn)對(duì)側(cè)墻外形輪廓的有效控制。
基于工裝預(yù)變形的側(cè)墻尺寸偏差控制流程如圖5所示。首先,在側(cè)墻生產(chǎn)過(guò)程中采集20組檢測(cè)數(shù)據(jù),統(tǒng)計(jì)測(cè)點(diǎn)偏差均值為第m個(gè)側(cè)墻上第i個(gè)測(cè)點(diǎn)的尺寸偏差)。然后計(jì)算偏差因子K值
其中T為測(cè)點(diǎn)公差;n為測(cè)點(diǎn)數(shù)量),其值大小反映側(cè)墻輪廓與理論輪廓的偏離程度。若K<1,則說(shuō)明側(cè)墻尺寸偏差處于可控的階段,不需要調(diào)整工裝進(jìn)行控制。若K>1,則表示側(cè)墻尺寸偏差過(guò)大,外形輪廓質(zhì)量不好,需要根據(jù)式(1)、(2)所得的模型計(jì)算工裝預(yù)變形量,對(duì)下一批次側(cè)墻進(jìn)行尺寸偏差控制,并在控制過(guò)程中修正定量關(guān)系模型。接下來(lái)檢測(cè)控制后的側(cè)墻(20組)輪廓尺寸,循環(huán)以上過(guò)程,持續(xù)改進(jìn)側(cè)墻的制造質(zhì)量[10]。

圖5 側(cè)墻尺寸偏差控制流程圖
3.2 工裝預(yù)變形量的計(jì)算
當(dāng)側(cè)墻輪廓出現(xiàn)較大偏差(K>1)時(shí),需要依據(jù)定量關(guān)系模型計(jì)算工裝支撐板預(yù)變形量。理想情況下,為保證下一批次的側(cè)墻能夠有更好的外形輪廓,工裝預(yù)變形引起的應(yīng)該將實(shí)際偏差完全平衡、抵消,使經(jīng)過(guò)調(diào)整之后實(shí)際輪廓尺寸偏差為零,即與應(yīng)該大小相等,正負(fù)相反

對(duì)于式(4)取i=3,7,12,聯(lián)立可得三元線性方程組

將式(7)具體數(shù)值及回歸系數(shù)β代入方程組(8),計(jì)算得到工裝反變形量Δy1、Δy2、Δy3。
3.3 尺寸偏差控制及模型修正
在尺寸偏差控制過(guò)程中,應(yīng)用3.2節(jié)計(jì)算得到的Δy1、Δy2、Δy3調(diào)整工裝參數(shù),可對(duì)下一批次的側(cè)墻外形輪廓進(jìn)行控制。理論上經(jīng)過(guò)調(diào)整之后的側(cè)墻輪廓尺寸偏差均為零,但由于工裝預(yù)變形—尺寸偏差定量模型存在誤差,調(diào)整后側(cè)墻外形尺寸偏差依然存在,統(tǒng)計(jì)工裝調(diào)整后側(cè)墻各測(cè)點(diǎn)尺寸偏差均值計(jì)算 ΔH′i,將值與ΔH′i加入到表1中,更新數(shù)據(jù)后重新計(jì)算系數(shù),可得到“工裝預(yù)變形—尺寸偏差”修正模型。
循環(huán)3.2節(jié)與3.3節(jié)的計(jì)算過(guò)程,可將側(cè)墻輪廓尺寸偏差控制在一個(gè)較小的水平,同時(shí)使得側(cè)墻制造精度得到不斷地提升。
3.4 工程應(yīng)用效果
將上述方法在某軌道裝備制造企業(yè)的側(cè)墻工段中進(jìn)行工程應(yīng)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實(shí)際生產(chǎn)表明,利用工裝預(yù)變形控制側(cè)墻尺寸偏差的方法,對(duì)于提高側(cè)墻制造精度,提升生產(chǎn)效率,穩(wěn)定側(cè)墻性能效果顯著。
圖6為工程應(yīng)用實(shí)施前后的效果對(duì)比圖,其中三維直方圖的垂向坐標(biāo)為測(cè)點(diǎn)尺寸偏差。

圖6 尺寸偏差對(duì)比效果圖
經(jīng)過(guò)調(diào)整工裝預(yù)變形對(duì)生產(chǎn)進(jìn)行控制之后,側(cè)墻最大偏差由3.21mm減小至0.98mm,平均偏差由1.81 mm減小為0.41mm,一次性合格率平均值由42.6%提升到81.3%,側(cè)墻外形輪廓及制造精度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側(cè)墻制造精度的提高,不僅大幅度減小了人工調(diào)修的工作量,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縮短了生產(chǎn)周期,還大幅度降低了火焰調(diào)修的溫度及頻率,使側(cè)墻疲勞強(qiáng)度和剛度性能得到了有效提升。
4 結(jié)束語(yǔ)
(1)提出了一種基于工裝預(yù)變形的制造精度控制方法,該方法簡(jiǎn)便有效,通過(guò)調(diào)整工裝預(yù)變形量即可獲得良好的側(cè)墻外形輪廓;
(2)基于多元回歸方法,建立了側(cè)墻尺寸偏差與工裝預(yù)變形的定量關(guān)系模型,并通過(guò)生產(chǎn)實(shí)踐驗(yàn)證了該模型的可靠性及有效性;
(3)利用實(shí)測(cè)數(shù)據(jù)及定量關(guān)系公式計(jì)算工裝預(yù)變形量,避免了生產(chǎn)控制對(duì)經(jīng)驗(yàn)知識(shí)的過(guò)度依賴,為實(shí)現(xiàn)經(jīng)驗(yàn)制造到科學(xué)制造的轉(zhuǎn)變提供了基礎(chǔ);
(4)對(duì)于其他穩(wěn)定、持續(xù)的產(chǎn)品制造過(guò)程,利用工裝預(yù)變形平衡其他偏差源對(duì)制造精度進(jìn)行控制的思路同樣適用。
[1]董錫明.高速動(dòng)車組工作原理與結(jié)構(gòu)分析[M].中國(guó)鐵道出版社,2007.
[2]何華武.創(chuàng)新的中國(guó)高速鐵路技術(shù)(上)[M].中國(guó)工程科學(xué),2007.
[3]張衛(wèi)華,等.中國(guó)高速列車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J].機(jī)車電傳動(dòng),2010,1(1):1-11.
[4]Hu S.J.Stream of variation theory for automotive body assembly[J].Annals of the CIRP,1997,46(1):1-6.
[5]來(lái)新民.轎車白車身制造尺寸偏差控制關(guān)鍵技術(shù)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1999.
[6]王 華.基于核函數(shù)PCA的柔性薄板裝配偏差源診斷[J].機(jī)械強(qiáng)度,2007,29(3):433-436.
[7]周軍年,等.軌道車輛用6005A鋁合金型材焊接裂紋研究[J].焊接質(zhì)量控制與管理,2008,37(6):49-51.
[8]張撓庭,等.多元統(tǒng)計(jì)分析引論[M].科學(xué)出版社,1997.
[9]張烘州,等.響應(yīng)曲面法在表面粗糙度預(yù)測(cè)模型及參數(shù)優(yōu)化中的應(yīng)用[J].上海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44(4):415-420.
[10]林忠欽,等.轎車車體裝配尺寸偏差控制技術(shù)[J].中國(guó)機(jī)械工程,2000,11(11):1 215-1 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