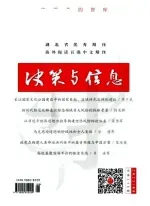中國改革攻堅縱橫談
文/紀屏
在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之際,中國的改革又處于十字路口,再次面臨選擇,真是進亦憂,退亦憂,但倒退或停止,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條。到底怎么改,如何改,改革的阻力是什么,這些改革攻堅問題成為社會各界共同關注的熱點。我們根據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的發言和專家學者的論述以及有關媒體的報道,對此進行了梳理,歸納出幾個方面的問題。
當前中國改革攻堅需要解決的問題
高尚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許多更深層次的問題逐漸暴露,改革過程當中一些瑕疵和疏漏以及部分改革不到位造成的扭曲,經過長期的積累也出現爆發跡象,亟待解決。主要問題是:
第一,市場仍然受到過度的行政干預,政府和市場界限不清,行政壟斷仍然廣泛存在。行政權力過度參與市場扭曲了資源配置,并助長了權力尋租造成的腐敗現象。
第二,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勢頭需要遏制,與此相關的收入分配制度、稅收制度改革進度緩慢,社會保障體系尚不健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懷不夠,并逐漸產生階層固化的現象。
第三,法治不彰,政府轉型乏力。依法治國的治國方略雖然早已確立,但是政府職能缺位、錯位、越位并存,距離“法治型政府、服務型政府”還有較大的差距。
第四,世界經濟動蕩不安導致出口受限,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粗放型發展帶來的環境壓力巨大,長期以來的高投入、高污染、以出口為導向的傳統發展模式不可持續。而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又面臨收入分配不均、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的制約,經濟發展有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第五,教育體制、科技研發體制、人才培養機制難以滿足以創新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的要求。人才培養與市場需求脫節,造成一方面技術工人、高端研發人員短缺,另一方面大學生就業壓力巨大。
韓德云(重慶市律師協會會長):目前改革迫切需要改的是,在決策中增加民主的因素,開放公眾參與機制,擴大表達的自由,讓民眾說話。不同的階層、群體有不同的利益,只有充分地讓民眾表達,才能弄清楚社會不同階層的利益交叉點,社會才不會一頭熱。批評監督機制也要相應地改革。現在,龐大的公務員群體讓人憂心。沒有監督,無法想象他們的決策是正確的。不能讓代表少數人利益的人決策。
為什么改革攻堅難度比20年前更大
厲以寧(著名經濟學家):經濟好比人的身體,經濟一旦出了問題,馬上通過宏觀政策進行調整,就如同人生病了要吃藥來恢復。而改革正是要讓經濟這一“肌體”,依靠制度的“療效”,具有內部調整和促進發展的功能。從外生轉變為內生,改革解決的就是這樣一個問題,這也是目前所欠缺的。三十多年前的改革,無論是農業承包制、鄉鎮企業改革或是股份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由民間自發、自下而上式的改革。現在不能再靠“摸著石頭過河”,“水深了”已經摸不著“石頭”了,今天的改革,更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這就要求改革的決策者具備戰略家的眼光,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將整個戰略布局做得更好。現在的改革跟三十多年前不一樣,中國面臨雙重轉型,即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現代化社會。同時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這兩個轉型疊加在一起,特別是第二個轉型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從沒有經歷過的,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改革的艱巨性。
胡德平(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不斷取得經濟上的奇跡,經濟總量和政府財政收入都很大。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民受益,利益集團也受益,壟斷集團更受益,官商勾結的賺錢最多,這個矛盾必須要解決。不按規則辦事、甚至按潛規則和人情來辦事已經成為改革的重大阻力。
當前改革的亂象還包括“頂層設計”被一些部門和企業攬走,使最高決策部門無作為。“頂層設計”的意思是說政府必須從戰略管理的高度來統籌改革與發展的全局,因為現在很多原屬于“頂層設計”的文件和法律交給了一些部門或公司來制定,其中包含大量部門利益。如很多法律都是部門起草的,稍加修改就報人大審議。但這個工作應該是人大組織專家來做。把國之重器委托給一個公司一個部門來做,這就比較亂了。作為改革的突破口,土地是個大問題。現在全國窮困人口共一億,進城務工的農民有2.5億,如果再產生一億失地農民,那么“改革真危險”。在這改革的關鍵時刻,應從農民角度想想,土地是村子里的,賤賣就不行,強征強拆就是違法,可是有人卻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這對改革開放精神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希望我們公有制所有者都歸位,這是所有問題的根本。
郭如才(中央文獻研究室):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制約科學發展的機制障礙躲不開、繞不過,必須通過深化改革加以解決。這就要求我們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堅持不懈地把改革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
吳忠民(山東大學社會學系主任):“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可以選擇余地大,可以主動調整,而社會矛盾引出的改革呼聲無法回避。改革會涉及權力部門切身利益,所以要有決心和勇氣,不能總是改別人。規范公權沒有勇氣和決心也是不行的,不改的話誰都不是贏家。
改革攻堅的阻力是什么
柳斌杰(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一是我們對一些根本性的體制機制性問題沒有突破,所以有些改革改到最關鍵的時候,深不下去。二是改革本質上是國家、單位、企業、個人之間利益深度調整的過程,有時涉及到一些人的根本利益,就有了阻力,利益矛盾表現很突出。
王林祥(鄂爾多斯集團董事局主席):改革阻力主要來自既得利益集團和權貴利益集團,既得利益者拼命抵抗改革。
俞敏洪(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阻力還真摸不著。中國的問題在于,打太極拳不知道往哪兒打。如何解放雙手將是未來政府攻堅的難點。
羅 援(全國政協委員、少將):改革的阻力來自包括利益集團、思想觀念等。有時候,抱陳守舊是比較頑固的深層次因素,這在一定的程度上是由于文化積淀造成的。利益集團是非常主要的阻力,他們不愿意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
改革攻堅怎樣進行
遲福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我國三十多年的改革實踐表明,無論是改革的總體思路的形成還是單項改革的突破,中央層面的改革協調機制都至關重要。一是以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的改革處于重要的歷史機遇期,二是改革進入重大利益關系協調的關鍵時期,三是新階段的全面改革。目前的改革協調機構是國家發改委,它偏重負責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很難把改革擺在一個突出的位置。它既管理宏觀經濟政策、又負責重大項目的審批,很難超越部門利益。現在,任何一項改革都超越了這項改革的本身,比如收入分配改革,原來把它作為社會領域的改革,但現在它又涉及到經濟利益里的初次分配,還涉及到社會領域的再分配,更涉及到政治領域。要建立收入分配的基本數據,就需要財產公開。所以,任何一項改革都具有多重屬性,這就需要一個能夠統籌多方利益又能超越部門利益的協調機構。該機構要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屬于中央層面的、中央級。因為現在的改革錯綜復雜,只有中央層面的改革機構才能擔當。第二、由中央高層領導來主持工作。當年國家體改委是由國務院主要領導出任領導的。第三、要做好三件事,它是改革決策咨詢部門、指導部門、協調部門。這個機構應該做實,這很關鍵。如果做虛了又會陷入無法協調的境地。
關于改革的“頂層設計”,目標很重要。我概括為“以公平與可持續為目標,以協調利益關系為主線,以結構調整為重點”。改革重點在五大方面,除了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里說的理順五大關系(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理順中央與地方及地方各級政府間財政分配關系;理順城市與農村的關系;理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我概括為20字:“消費主導、均富優先、綠色增長、市場導向、政府轉型。”要圍繞這些重點設計好。
吉哲(媒體工作者):“頂層設計”的本意是強調自上而下設計的重要性,中國改革改到今天,容易改的都改了,積累到今天的問題和矛盾,已經不是基層和底層能夠解決的了——很難有像當年小崗村那種自下而上的突破了。而需要自上而下的總體設計和系統謀劃——比如農村教育問題,它涉及總體的教育資源分配不均,一個地方靠自身力量很難擺脫貧困的宿命;留守兒童問題,農民工背井離鄉留下一個空心的農村,老人與孩子相依為命,這也是依靠自身無法擺脫的命運,需要頂層設計打破目前這種不由分說的“城市中心”。“頂層設計”需要每個人的智慧,但改革需要自上而下改起,具體地說就是“改革要從領導干部改起”。本次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都談到了“學雷鋒應該從領導干部做起”,引起很大的輿論共鳴,其實這也屬于“頂層設計”。我們經常說一些問題是老大難問題,比如公款吃喝,還有公車不改革,政務不公開——老大難問題,癥結正在于“頂層設計”的缺乏。老大難問題,“從老大改起”自然就不難了。一些地方的車改,只改處級以下干部,地方一把手不帶頭,當然難以服眾;一些地方的官員財產公開,只要求科級以下干部公開,地方老大拒當先鋒,改革當然無法進行。
趙啟正(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當改革越步入深水區,在面對一些核心問題時,越凸顯出突破的必要性。我們處理問題要完全沒有風險不可能,冒點風險不怕,要更加深刻地認識到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應當看到,有些問題老百姓等不起。最典型的就是涉及生老病死的醫改。這就要求各級政府、衛生部門、醫療機構、慈善救助、社會力量等等,盡可能地利用各種資源與渠道,千方百計幫助群眾解決燃眉之急,不能以制度缺陷為借口推脫、不作為。
朱燕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目前情況比較特殊,面臨著復雜的轉型,比如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從農業化到城鎮化轉變,在這一過程中,政府需要發揮很大的作用,并參與其中。但是在經濟、政治等領域的發展到了一定階段,政府就應該考慮及時退出一些領域。環顧當今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基本上都表現出政府角色相對較小的特點,在這方面,中國香港非常典型,香港的行政部門非常小。如果政府不能夠及時轉型,從一些領域中退出來,將會造成并加重行業壟斷現象,同時會讓尋租現象越來越嚴重。政府和經濟活動分不清,過多的政策干預造成了一些特殊的利益階層。現在老百姓普遍反映的腐敗等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因為政府參與經濟太深,給了腐敗以機制上的土壤。
陶斯亮(全國政協委員):對政治體制改革,反腐是一個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首推從吏治開始。這就好比用干細胞去治療癌癥,化療能殺死癌細胞,但也能殺滅正常細胞。但給你種植干細胞就不一樣,讓這個新生的健康的細胞來代替你這些不好的不健康的細胞,而不是同歸于盡。
王正福(貴州省政協主席):盡早啟動收入分配改革。這是一個非啟動不可的問題,再不改革就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了。
葉小文(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黨組書記):改革千頭萬緒,應該以什么順序推進?對群眾,要多講先經濟、再社會、再政治這個順序。民主是個好東西,但不能急,中產階級起來了,理性的思考多了,這樣的民主才有質量。但上層還真要有緊迫感,得看遠一點,應該多講黨內民主、政治建設。
朱小丹(廣東省省長)我個人理解,最關鍵的改革是政府自身的改革。當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而政府自身改革的最大阻力也來自于政府自身。我們要拿出革自己的命的勇氣,真正使政府職能歸位,理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革命革到自己的頭上,是真改革還是假改革,是口頭上說改革還是實際上促改革,對政府是個大的考驗。現實中,現有的政府管理體制,也讓一些部級官員深受其苦。像現在的財政分灶、分級管理體制,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跑部錢進”現象。
穆德貴(貴州省副省長):盡管對三公消費的罵聲是一浪高過一浪,“跑部錢進”的體制不變,三公消費難以改變,一個財政部管資金分配的官員下去了,你怎么可能讓他自己到餐館就餐?如果各項專項資金在年初就按一個標準分配給各省了,誰還跑部?中央部委管理的項目可以年初就按標準分給各省。如果這個體制不改變,誰帶頭抵制三公消費誰吃虧。中國的改革歷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不可能的。
林方略(海南省副省長):國家應該有一個規劃,下面按照國家的規劃部署抓實施,否則無所適從。就像大部制,下面把部門集合起來,結果上面部門的精神在下面貫徹得不順暢,逼得有些地方又恢復設立迎合中央有關部門的條塊部門。
辛 鳴(中央黨校教授):今日中國堅持的道路還是鄧小平開辟的道路,方向還是鄧小平指出的方向,旗幟也是鄧小平高舉的旗幟,但是很多的狀況、態勢卻已與鄧小平的預期有不小的距離:市場經濟沒有帶來應有的公平正義,“先富”也沒有帶來及時的“共富”。市場是手段,但駕馭這一手段是要有前提的;沒有權利保障,也就沒有市場正義。“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策略與突破口,可是事情的演變卻不像大家預想的那樣。一部分人是先富起來了,但是,共富卻好像遙遙無期。現在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一聽說共富,就扣上平均主義的帽子,認為是走回頭路,甚至還找出種種理論根據。
那么,為什么政府在推進共富方面好像也沒有大作為呢?一方面,市場化的改革讓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計劃經濟背景下那樣的有力量。面對市場的邏輯、法治的約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擔當很難有大手筆、大決心;另一方面,政府中的成員財產狀況也在發生變化。
從改革設計到改革實踐,其間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實踐不能是對改革設計的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照葫蘆畫瓢”是實現不了改革藍圖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藍圖不詳盡,是推卸責任的行為,不是真正改革實踐者應有的態度。把鄧小平提出來但沒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對腐敗、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來,實實在在兌現了,改革的權威、改革的共識、改革的動力就會重新回到中國社會。
大林(時事評論員):當下關注改革,似乎不存在凝聚共識問題。上層強調要改,媒體呼吁要改,廣大群眾更是期盼真改、深改、快改、穩改。作為一般群眾,雖未必能從理論層面思考與評判改革,但是有足夠的經驗與智慧去認知改革的現實狀態,判斷改革的難與易、虛與實、真與假。一切改革,最終使他們看到了什么,獲得了什么,才是他們對改革進行價值判斷的根本依據。在政治領域,群眾希望看到依法行政的政府,謙卑恤民的權力,坐實的人民主體地位;在人權領域,群眾希望落實人人生而平等的生命權、健康權、勞動權及其報酬權;在經濟領域,群眾希望享有健康的市場秩序,獲得公平交易、財富安全的保障;在社會領域,群眾希望平等地擁有人格尊嚴,享受公共福利,以主人身份參與公共事務。在人民群眾的心里,改這改那,歸結到一點,無非就是調整好國家權力和人民權利的關系,而且調整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一定是讓國家權力更好地服務、保障、增進人民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