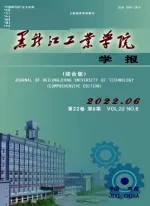淺談武士道的形成和內涵
王彧
淺談武士道的形成和內涵
王彧
武士道是日本文化精神的核心,在社會行為、精神信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留有印痕。它的形成和發(fā)展既受島國環(huán)境所制約,還受到佛教、神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響,講究忠君、尚武、勇烈、服從、禮儀、廉恥等封建道德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從而形成獨樹一幟的民族特性。
武士道;源流;精神內涵
一
武士道興起于藤原氏政治專權的背景下,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又是武士應盡的義務和職責。最初的武士道并不是成文法典,大多是口傳或者通過學者和武士之筆流傳下來。因此,我們不能指出一個明確的時間和地點來說“這里是其源泉”,不過由于它是在封建時代自然源流的,所以在時間方面,可以認為它的起源是與封建制一致的。[1]大化改新后實行的征兵制隨著中央集權制的衰落日漸松弛,此時興起的莊園主為了領土和安全成立了專門負責保衛(wèi)工作的武士團,神廟、神社也相應組織了僧兵,地方武裝上則是由當?shù)馗缓澜M成的“郎黨”。隨著武士勢力的出現(xiàn)和加強,11世紀初期逐漸形成了超越莊園范圍的地方性武裝集團,首領稱“物領”,下屬稱“庶子”。武士團有著極強的宗族觀念,堅決貫徹首領的命令,實行主從關系。武士在戰(zhàn)場上的勇武和對主人的獻身精神,是武士個人和武士團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之氣”“弓矢之道”等新觀念,成為維持武士團組織的重要思想支柱。[2]
武士道作為日本民族在孤立島嶼中產生的復雜而極端的生存意識,是與它特殊的島國根性不無關系的。島國根性是日本人自己形容自己的性格和氣質特征的說法,與大陸性寬厚、大度、沉穩(wěn)相比,顯示出來的劣根性部分。[3]日本人認為,那種相互嫉妒、排斥、對他人的猜疑心、不顧大局、為小事處心積慮、卑屈與盲目驕傲都是島國根性的反應,引起情感上的大起大落,也就是美好的理想同狹隘的現(xiàn)實之間的矛盾結果。長期的孤島生活養(yǎng)成了他們封閉內向的性格,心存芥蒂,拘謹害羞,即使是對首領也不肯輕易打開自己內心的大門。
在島國根性的基礎上,武士們的為人處世之道又是通過佛教、神道和中國傳來的孔孟之道三大方面逐漸形成的。首先,佛教給予了武士道平靜地聽憑命運的意識,對不可避免的事情恬靜地服從,面臨危險和災禍像禁欲主義者那樣沉著,從而形成了悲死輕生的心境。因此武士道十分重視冥想,也就是佛講的“禪”,認為禪的目的在于辨析現(xiàn)象深處的原理,從而達到身心的和諧一致。其次,日本本土的神道對武士道的影響十分深遠且具有民族特色。神道的教義中,對主君的忠誠、對祖先的尊敬以及對父母的孝行為武士的傲慢性格賦予了服從性。神道相信人心本來是善的,如同神一樣是純潔的,比如很多神社里都會放上一面素鏡,當人心完全平靜清澈時就會反映出神的崇高形象,同時也會自省出自我的內心世界。[4]神道教義包含兩大特點——愛國心和忠義,武士不僅躬行盡忠,更時刻體現(xiàn)出民族情感,了解了這一點我們便不會對日本人狂熱地崇敬天皇感到不解了。第三,武士道嚴格的道德教義多來自中國的孔孟之道。雖然之前日本民族就已經(jīng)認識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以及朋友間的這五種倫常關系,但孔孟之說卻將其正式確定下來。尤其是孔子的貴族化言論切合了作為統(tǒng)治階級的武士政客們的要求,適應了等級社會的需求。孟子的學說極具說服力,同時又很平民化,不僅成了年輕人的主要教科書,還是成年人討論問題時所依據(jù)的主要權威。這些不同來源的零散滋補為武士們提供了可靠的行為指南,根據(jù)時代需求創(chuàng)造出與之相適應的武士道精神,從而鍛造出一種無與倫比的男子漢氣概。
二
武士道經(jīng)歷了三大發(fā)展階段,即江戶時代前的舊型武士道、江戶時代的新型武士道和明治維新后轉為近代軍人精神的武士道。早期以“弓矢之道”為特色的傳統(tǒng)武士道通過長期的沉淀,在吸收儒家思想做為理論骨架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的“士道”。18世紀初,佐賀藩武士山本朝常完成了有“武士論語”之稱的《葉隱聞書》,提出了“武士道者,死之謂也”的觀念,這些“死狂”之言從軍事意義上體現(xiàn)了忠與死的奉獻。然而這種筆記式的著述尚缺乏義理論述,不能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江戶時代中后期,由于幕府實行兵農分離和嚴格的士農工商四等民制,武士們開始了城市的寄生生活,修養(yǎng)內容也從重武功變?yōu)橹氐滦校氊熒矸莸淖兓沟镁褡非笠搽S之轉向儒家的士大夫理想和君子之道,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山鹿素行提出的“士道”論。山鹿素行從朱子學說中為武士道尋找理論依據(jù),提倡尊忠節(jié)、義理等儒家倫理道德,把“得主盡忠”作為武士應盡的本分,向武士灌輸“忠于主君”“不顧身家”的思想,還要有“報恩、克己、面對死亡毫不動搖的勇氣”。[5]他規(guī)定的這套禮法被作為日本社會倫理的基本支柱而大加宣揚,甚至被后來的軍國主義者利用而對國民進行奴化教育。
由于島國根性的存在,武士道或許會保留其品格或者附庸風雅,而一旦發(fā)展開來就會表現(xiàn)出極其殘忍的一面,甚至導致世界性的災難。[6]幕府末期,明治維新的先驅、稱山鹿為其“先師”的吉田松蔭在“士道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了“七規(guī)七則”和“忠魂不滅說”,使得明治維新后尊崇效忠天皇的思潮仍影響深遠,對欺騙日本人民盲目充當侵略戰(zhàn)爭的炮灰發(fā)揮了很大的作用。[7]
三
武士道精神具有極其豐厚的內涵,首先是忠誠至上。武家統(tǒng)治以忠誠為紐帶,運用利益機制開發(fā)家臣、武士忠誠道德的精神資源,希冀建設成“忠的市場”。統(tǒng)治者認為,武家社會沒有不忠之人的立錐之地,對主君不忠,就是“盜父母之惠,貪主君之祿,一生之間唯終于盜賊之命”,[8]其結果便是被逐出武家社會和喪失經(jīng)濟來源,精神上永無翻身之日。武士“忠君”是無條件的,因而武士道一旦演變?yōu)閷μ旎实挠拗遥统闪藢ν馇致詰?zhàn)爭的靈魂,乃是軍國主義的溫床,甚至使一些日本人迄今對于歷史上日本對外侵略戰(zhàn)爭的滔天罪行仍然缺乏負罪感,這是不爭的事實。關于武士道的消極影響,后世應當客觀辨析,防止被右翼主義者引入誤區(qū)。而誠,不僅僅指誠信,更代表了一諾千金的真誠之心。自士農工商區(qū)分以來,武士崇高的社會地位要求武士的誠信標準要高于普通民眾,甚至一些就武士因食言而以死抵償。
勇義為本。武士以戰(zhàn)爭為職業(yè),以武勇為謀生技能和晉升途徑,個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貧富貴賤統(tǒng)統(tǒng)取決于此。德川曾將“勇”定義為:“知有所畏與有所不畏”,這就區(qū)分了道德之勇和肉身之勇。武士們從小被灌輸各種膽量和無畏的精神——偶爾剝奪他們的食物、暴露于寒冷之中、困于山谷、觀看兇宅甚至殺頭……這種堪比斯巴達戰(zhàn)士的訓練培養(yǎng)出武士們英勇、堅忍、果敢、無畏的品德,使武士們?yōu)榱藢崿F(xiàn)自我價值勇往直前,不畏險阻。然而,在武士道的戒訓中,為了不值得的事情勇往而死,是沒有價值的,而價值所在,就是指義——正義之道,即切勿匹夫之勇。[9]鐮倉以來,對主君的服從、忘我的獻身,如追隨亡君剖腹殉葬曾被看作是最高的忠義之舉,但在幕末“士道”已逐漸形成新的價值觀。“不畏懼死”并不等同于“渴望去死”。這種轉變體現(xiàn)出幕府末年的時代變化引起平安時代以來武士道精神的變革,即重視現(xiàn)實,注重利益。可以說以實現(xiàn)人生價值為根本而非盲目獻身,即為了真正的正義之事而勇敢為之,正是時代思想的一種進步。
仁德之心德川時代,武士道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儒學的影響。江戶時期的儒學家山鹿素行將兵學和儒學相結合,使官僚組織機構中的武士成為道德標榜。提倡仁慈與德行,能助于避免封建制度下黷武之風的愈演愈烈,仁之為德,其性如母。這樣的“士”,被賦予了類似中國封建官僚的社會責任,對主君盡忠不再只通過武力,更多的是要肩負起道德教化、安定社會秩序的作用。[10]就武士而言,“仁”并非盲目沖動慈悲之心,日本的“仁”還包含另一層含義。就武士而言,“仁”適當?shù)乜紤]了正義之道,被賦予生殺予奪大權之余,甚至可以因為正義而將敵人作為敬重、交托的對象。正如尼采所說,以你的敵人而自豪,敵人的成功也就是你的成功。這種更高境界的仁是深層意識通過內心自覺反省的產物。
禮儀風度。殷勤而鄭重的禮貌是日本人的顯著特點,尤其受到注重心性修養(yǎng)的武士階層的重視。小笠原流宗家曾說過:“禮道之要,在于練心”,世人熟知的的茶道、花道即是武士道禮儀的體現(xiàn)。茶道等的內在要義在于內心平靜、感情明澈、舉止安詳,武士們同樣也注重培養(yǎng)溫文爾雅之風,學習茶道,喜愛音律,并且為了使這些優(yōu)美的情感表現(xiàn)于外,涵養(yǎng)于內,武士們創(chuàng)作詩歌也是禮儀之一。想必這就是日本國民性的一大體現(xiàn)——矛盾性,忠勇之豪邁和仁德之教養(yǎng)的相互融合。然而一旦失去平衡,就會成為如二戰(zhàn)時的失去人性的屠戮機器。
克制和榮譽。禮儀的存在要求武士們不可隨意流露出自己的痛苦和情緒,不可喜怒形于色,以免影響別人的平靜。尤其佛教傳入日本后,強調通過人格修養(yǎng)學會忍耐、自省、寬容和克制自我的精神,并逐漸成為武士人格修養(yǎng)的指導和標準。這便導致日本人表面上的翩翩禮讓和禁欲主義——正如上文提到的內在矛盾性。但這種忍讓和克制僅僅是表面上,對感情的壓抑往往會激起數(shù)倍的感情反彈。名譽意識包含著人格的尊嚴以及對價值的明確自覺,是青年武士們的追求目標。名譽催生羞惡之心,是武士們一種強烈的廉恥心,一些看不出價值的行為在武士道訓條中卻可以用名譽的借口付諸實現(xiàn)。[11]武士將名譽看得非常重要,如果面臨名譽與生命的兩難抉擇,武士會毅然選擇名譽。名譽不僅關系個人的得失,還關系到家族的榮譽和利益,所以在必要時刻,武士不惜犧牲性命保全名譽。而為世人所熟知的切腹,基本動機也是為了追求名譽,這種死亡方式在日本人看來無尚光榮,是完美的升華。
鑒于武士道精神內斂又張揚的矛盾性,我們應當辯證地對待,既看到傳統(tǒng)文化的溫情脈脈的涵養(yǎng),也要注意到這種民族文化的爆發(fā)性。希冀武士道精神在日本進一步發(fā)展完善,成為真正致力于和平安樂之道。
[1]凱風.東洋武士[M].中國時代經(jīng)濟出版社,2009:100.
[2][日]石田一良.日本文化史——日本的心和形[M].東海大學出版會,1989:78.
[3][美]大衛(wèi)·松本.解讀日本人[M].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2004:45.
[4]李濤.畸形的武士道[M].中國友誼出版社,2007:24.
[5][日]山本常朝.葉隱聞書[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71.
[6]楊紹先.武士道與日本軍國主義[J].世界歷史,1999(4):104.
[7]東行.毀滅與新生——日本明治維新人物傳[J].科學時代,2004(02).
[8][日]新渡戶稻造.武士道[M].商務印書館,1993:156.
[9][美]魯斯·本尼迪克特.菊與刀[M].商務印書館,1990:145.
[10]李卓.日本國民性的幾點特征[J].日語學習與研究,2007(5):147.
[11][日]會田雄次.何意毅,譯.日本人的意識構造[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154.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Bushido
Wang Yu
Bushido is the core spirit of Japanese culture,which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the social behavior,spiritual beliefs and way of life for Japanese people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not only by the island environment,but also by the influence of Buddhism,Taoism and Confucianism,Bushido contained many feudal ethics lead to an uniqu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
Bushido;origin and development;connotation
K313
A
1672-6758(2012)04-0130-2
王彧,碩士,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專門史專業(yè),山東·青島。研究方向:思想文化史。郵政編碼:266071
Class No.:K313Document Mark:A
(責任編輯:蔡雪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