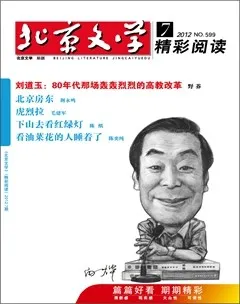夷地雞毛(散文)

我的前半生是在國內度過的。由小學,到中學,再大學,一路上順順暢暢,沒有什么坎坷。就連上山下鄉(xiāng)也是失之交臂。1982年大學畢業(yè)后,趕上了國家用人之際的好時光,被分配到北京做機關工作。過了幾年熬資歷的日子,漸漸倦怠了一眼可以望盡一生的生活。1989年,妻到美國讀書,我?guī)缀跸胍矝]想就于次年初赴美陪讀。
初到異國的日子,除了新鮮興奮之外,更多的是柴米油鹽醋的生存壓力。于是就有了這種升斗小民凡夫俗子雞毛蒜皮的故事。經過時間的沉淀,當年辛苦的日子變得有滋有味;而到了知天命的年紀,生活教會了我調侃也是一種生活態(tài)度,有時候它能讓日子變得輕松美好。
買車
話說俺到夷地后,風里雨里苦了兩三個月,從牙縫里摳出了千余兩銀子,便踅摸著鼓搗一四個轱轆上的沙發(fā)回家。
在夷地買車,有幾個路數(shù)。倘是身懷金山銀山,便可上選奔馳寶馬,中選豐田本田,下選現(xiàn)代起亞,肆無忌憚地直闖新車行大堂。往那兒一矗,你就是爺;往那兒一坐,你便是皇帝。那靠傭金吃飯的店小二們,自會把你當?shù)r上十分笑臉把你哄著,鼓動三寸不爛之舌把你抬著。眼里看的是你包袱里的銀子,心里想的是自己夢想的票子。現(xiàn)代起亞被店小二一吹,質量好過了奔馳寶馬;寶馬奔馳被店小二一比,價錢低過起亞現(xiàn)代。什么時候你簽了字,畫了押,交了銀子,一場大戲便告落幕。店小二與你已成路人,你不再是皇帝不再是爺。買車如相面,身上有銀子,自然底氣兒足。車型上跑車、房車、箱型、吉普、兩門、四門,顏色上赤橙黃綠青藍紫,自任你挑,由你選。
倘是個中產,便到個正經八百的舊車行,由那些被富豪們休了出門的車中,揀那面相尚好,未曾破相的,娶其回家。雖不是黃花閨女,倒也可以挑挑揀揀。車行通常有一到兩年,幾萬英里的質量保證。雖是比上不足,比下卻有盈余。
最不濟的便是俺這等囊中羞澀之輩。那點道行,漫說新車行,就是舊車行也是入之無門,空余艷羨之心。剩下一途便是或翻報紙廣告,或注意掛在車上的求售幌子,或是經人介紹。落魄到這個地步,什么車型、廠家、顏色均無力挑揀,只求能否生養(yǎng)。娶回家的,禍兮福兮,端看自己的造化。
那時節(jié),買車成了俺心里一結,甚是糾纏。見天拿著報紙,直奔廣告欄,只揀1200兩以下的汽車廣告由頭看到尾,由尾看到頭。間或有中意的,卻無人駕往,過的盡是干癮。行走在道上,只拿兩眼向過往車輛脧巡,行盡注目禮。卻說一日從做鞋處出來,眼見遠處一車停著,窗上猩紅的幌子甚是耀眼。走近一看果是求售。幌子上只有電碼,余皆不詳。俺懼怕記不下來,復回到做鞋處,取來紙筆,記將下來。回到家中,不及吃飯,央妻立馬照電碼去話。
“要價多少?”妻問。
“沒寫。”俺照實回話。
“是何出生?”妻復問。
“不知。只看到車上有四個圓圈連在一起的標牌。”妻聽了俺的回話,如行在五里霧中,混沌得緊。
妻給那車主去過電話,那廝一報價碼,妻嚇了個跟頭,不到1分鐘便敗下陣來。原來那車乃名門世家,雖是徐娘半老,猶是瘦死的駱駝,要價6500兩。豈是俺可以問津的?車沒買到便罷,卻留下話把兒,迄今仍被妻嘲笑。
經了如此曲折,俺收起騖遠之心,因陋就簡,專在俺的工友及妻的學友中打探。工友中有一先賢,家有兩輛座駕,愿意出讓一輛。俺一打探到,頗有踏破鐵鞋的感慨。也不還價,只求熟人同鄉(xiāng)看在中土同源的份上,不要弄個不能生養(yǎng)的,把俺給忽悠了。
這夷地土生土長有三大車廠,通用、克萊斯勒、福特。克萊斯勒旗下有道奇、普列茅斯和克萊斯勒三大品牌。俺的座駕便是出自道奇門下。這克萊斯勒雖不是名門,卻也是源遠流長,先前富過,祖上大紅大紫過。二戰(zhàn)時期,夷地大兵乘著克萊斯勒大卡車東奔西撞,打下了許多江山。當官的乘坐的吉普更是今日運動休閑車的鼻祖,小覷不得。70年代在艾柯卡同志的英明領導下,旗下發(fā)明的箱型車,迄今仍風行世界,為家庭主婦、婦男的最愛。石油危機前,率先炮制出的小型車,一舉為克萊斯勒迎來了繁華盛世。只此三樣,倘是當年申請了專利,如今即便是關了生產線,光靠專利費也可以過得人五人六的。
先賢將車開來過目,叫俺朝面。俺見那車,老便是老些,尚是四肢俱全,面相尚好,并無傷痕。往里一坐,頗為寬敞。車行如風,尚是平穩(wěn)。先是心許了。不日備妥了銀兩,辦了交接。復由先賢領著,到車輛管理部辦了過戶手續(xù),一樁大功便已告成。
隨后再到車輛管理部文考,拿了學車駕照,學車,武考,自是后話。卻說俺拿到駕照,銀子已然耗罄,無力舉辦任何慶典。遂帶著妻,也無膽在高速上比劃,沿著27號小道由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一路南行。其時時近仲春,大地回暖,小車一路越小丘,過小橋,路兩邊或綠樹成陰,或綠草遍地,鮮見人跡,美不勝收。約半個時辰,路兩邊漸有人氣。右邊一排平房涌將過來,門前均掛有各式幌子,有酒肆、衣店、書屋,顯是到了一市鎮(zhèn)。左邊一群樓舍,俱用青石造就。樓頂多作尖狀,甚是宏偉。看似教堂,卻又不像。將車泊住,隨三兩路人由大門進去,也不見個把門的。往里進時,卻見處處綠草茵茵,芳草萋萋,合抱大樹點綴其中,灑下的濃陰將草分作深綠翠綠。各式樓宇東一座,西一棟,互不連接。初看時似零亂,細看時倒像是為那一樹一草點綴,卻是養(yǎng)目,和諧得緊。游了一圈,往回轉時,眼見一棟房子,各式男女進進出出。走近一看墻上鑲的不大牌子上,赫然寫著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原來俺們不曾沐浴更衣,就這么不期然闖進了學界最高殿堂。欣然之余,多少有些褻瀆斯文的后怕。
有了此番經歷,越發(fā)悟到轱轆上的沙發(fā)是個好物件,堪為中用。遂越發(fā)愛惜起來。不惜代價,拿到車廠換油、換水、換剎車,只差沒有將全車上下重新刷過。指望著那車,將心比心,把俺對它的好多少退還些給俺,不枉了俺的一番苦心。
秋初時,由國內來了弟兄。帶著弟兄俺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上了1號高速,一路北上再向西行,進了新澤西與賓州交接處。上到高處,但見山巒起伏,萬樹爭鋒。風騷的樹木,等不及秋霜,爭先紅了黃了紫了,雖未及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境界,倒也把個群山弄得風情萬種,鮮活起來。幾個人流連忘返,早忘了時辰。眼見夕陽西下,這才不舍歸去。
俺回到車里,照章程系好安全帶,將鑰匙插入點火,不想那車并不理會。俺何曾見過這陣勢,早慌了神。將鑰匙拔出,復插入,再打火,那車如發(fā)了牛脾氣猶是不理俺,俺失了計較。幾個人大眼瞪小眼,荒郊野嶺的早沒了主意。眼見天色漸暗,相持下去定是個只輸不贏的不了之局。幾個人遂棄車步行下山。好不容易找到一人家,借了電話,央友人驅車救駕。夜半時方回到住處。
二天一早再由友人馱著,找到一家拖車公司,回到事發(fā)地點,再也無心欣賞美景,看那廝將車捆綁了,呼嘯著拖下山去,草草找個醫(yī)館,在門口停下。彼時已是周日,醫(yī)館打烊,無人問診。只得將鑰匙由門洞投入,也不知救得活否。這才一步三回頭離去。
回到家時,仿佛失了魂,茶飯無思。再天一早,妻給醫(yī)館去話。得回話曰,車已收到,能否醫(yī)治,所需多少,等下午回話。苦等一下午,未接到只言片語。晚飯也不曾吃,尋思道那車恐怕是病入膏肓,兇多吉少了。囫圇睡了一夜。天亮后,好不容易挨到醫(yī)館開門,電話過去,被告知車上一管氣缸運作頻率的帶子損壞,須等零件三天后修好。三天后再央人帶俺到了醫(yī)館,付了500余兩銀子,將車子取回。
經過這么一折騰,對那車失了信心。前后壞了不少銀子,那車已為雞肋,俺已勢成騎虎。有心修理,不知窟窿有多大,需多少銀子填補。欲不管不顧,淡定下去,又恐哪日再舊戲重演,尥了蹶子,將俺獨自一人扔到一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荒郊野嶺。車子掛了也罷,再遇上個大蟲,或假李逵,卻是如何善了?不得已,將車送到車行大修,復壞了600余兩銀子。
那時俺新交了幾個牌桌上的朋友。一到周末便廝混在一起,在牌桌上比高下,論英雄。牌友中有一達人,無師自通,精通修車之技。初到夷地,買過一老舊車。一日,那車罷了工,這爺們兒,自己買了本書,借了些扳手、起子等工具,三倒兩弄,把個破車擺弄活了。從此立了腕兒,成了僑界的角兒。也就是在牌桌上混熟了,那爺們兒聽了俺座駕的傳奇,動了凡心,要替俺看覷一二。這可是天上掉餡餅的事兒,可遇不可求。這牌倒也沒白打,打出個名醫(yī)朋友來。隔天將車開來,在秋日明媚的艷陽下,將能開的門蓋全部打開,讓那爺們兒看個明細。
那爺們兒在引擎蓋下只看了幾眼,便直起腰來看定俺,也不說話。俺被他看得心里發(fā)毛,不知如何應對。想起醫(yī)生告知病人得了絕癥,需要字斟句琢的景況,一陣寒意透徹全身,哪敢開口動問。估計那爺們兒實在找不出安慰俺的話,稱量俺大概經得住這直來直去一刀,問俺道,這車你還敢開呀?
俺被爺這么一問,越發(fā)混沌起來。這爺不提車的優(yōu)劣,倒找俺的不是。合著這車不好倒成了俺的問題。爺瞧俺滿臉的無辜,指定一位置叫俺看。俺見那位置乃左前輪的支架,周圍已然銹蝕。那爺指指中間部分,復指指引擎蓋,讓俺仔細瞧,慢慢看。原來那銹蝕部分不堪承重,輪子支架已然頂出,將引擎蓋頂出個大窩。倘是高速行駛,車子一顛一簸之間,引擎蓋被頂起,那可不是說笑的。俺請個名醫(yī),期望著華佗再世,那車縱有千般不是,也能手到病除。最不濟的,也能為俺指點迷津,或指出哪里該修,或讓俺轉投明醫(yī)。似這般沒把車看好,一句話倒把車給判了死刑的,實讓俺無力承受,直娘賊的。那車俺不敢再開。胡亂找了一“買”主,收了50兩改嫁費,方了這份孽緣。
事后經爺?shù)闹敢蛋儆嘤⒗铮蔂斂彬灒?000兩銀子新買了一舊本田王。那車跟著俺凡六年,并未尥過蹶子。其間由新澤西到舊金山橫貫夷地大陸,俺將它,它將俺也不知是誰將誰帶到舊金山。至1997年妻學業(yè)期滿,謀到差事,俺從此改買新車,混到爺?shù)慕莾海允呛笤挕?/p>
購房
話說俺投了舊金山不久,妻謀了差事。妻與俺便蓄謀著結束俺們在夷地上無片瓦,下無寸地,寄人籬下的凄涼日子。遂向先到夷地的先賢請教,得寶典后,擇了經紀便開始了漫長的與房相親的歷程。
那媒婆須是個中老手,頭回見面,話無三句,便摸清俺們能出的價格,年入的多寡,首付的價碼,巴望的房屋形式,一應備細,拐帶著妻與俺東奔西突,四處相親。
幾個周末下來,所相面之屋,約二三十間余,有鎮(zhèn)屋,雙拼,獨棟;有拐角的,路沖的;有平房,樓房;有收會館費的,有不收的。林林總總,洋洋灑灑,甚是豐盛。妻與俺,早沒了主意,木偶般隨那媒婆,但見那求售的幌子,便搶入門內,覷個三兩眼,便撤至門外。并不知房屋的好壞,館舍的優(yōu)劣。那媒婆并不催動妻與俺,但見俺有意的對象,便數(shù)落那對象的不是,煞是為俺著想。幾番下來,妻與俺早把心中尺碼放下,順了媒婆。
那媒婆眼見妻與俺漸漸入港,對相親亦失了忍耐之心,便兼起了媒婆兼家長的角色。卻說一日,妻與俺相中一獨棟小屋,房屋不大,只1500尺。小屋逐灣而居,后院搭著一公園,公園傍著灣,灣內漾著水。門前與甲骨文巨大的玻璃樓隔街相望。屋內玲瓏剔透,拾掇得鮮光美麗。雖到中年,尚是風韻猶存。妻與俺頗覺是驀然回首,一見傾心。那媒婆觀色察言,自是讀懂了妻與俺的心思,幫妻與俺作了決斷,就是它。
那媒婆從包袱里順出早已備好的文案,寫好了門牌街號,禮聘的價碼,讓妻與俺各自按了手印,畫了押。馬不停蹄將個問單傳將過去。限時三日,予以回話。越明日,那媒婆給妻與俺賀喜道福,言對方并無討價,受了妻與俺的問單,有了文定。
文定有了,尚有一應龐雜須在30日內理順。原來在這夷地購屋,有環(huán)節(jié)若干,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斷斷馬虎不得。其一是下單,對方同意,便有了文定。倘使價碼上有所不合,彼此往來若干回合也是有的。文定之后,夫家須將定金若干(約3%)放到特定的中立賬戶。夫家同時有三天的毀婚時間。其二是清除條件期。夫家作文定時,通常附有暗款,諸如女方太丑(房屋有問題),或夫家囊中羞澀(貸不到款),文定便自動終止。這女方的美丑須不是夫娘兩家說了算,須找專業(yè)的鑒定師勘驗。其三是貸款。末了才是迎娶過戶。
卻說妻與俺一洗近月的勞頓,請了有執(zhí)照的土木工程師,擇一風光明媚的周末,投親家去。那師爺一水的工裝,開一老舊的皮卡。皮卡上印有執(zhí)照號碼及公司行號。遞出的名片赫然寫著美國xx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加州xx公司總裁。來頭著實不小,很是唬人。師爺下車伊始,并不進屋,只上下打量那半老徐娘,再細看左右鄰舍,度量著近朱近墨。踱入屋中,將一應電開關開啟,所有水龍頭大開,洗碗機,洗衣機,烘干機,爐灶,微波爐,烤箱盡皆打開,如此這般,勘察備細。妻與俺自隨著那師爺?shù)谋砬樯舷缕鸱幥绮欢ǎM受熬煎。眼見師爺勘驗完畢,步出屋外,妻與俺如釋重負。這徐娘,老便老些,尚是秀外慧中,以俺這等身手,得此佳麗,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那師爺轉至屋內,卻換了一身行頭,袖口褲腳齊綁,偌大的塑料帽將頭裹個密實,巴掌大的口罩將嘴罩個嚴密,白色的手套裹手,黑色的膠鞋套腳。妻與俺俱吃他一驚。那師爺也不搭話,卻轉自屋角,掀開一木板,作勢鉆地。卻原來妻與俺自顧竊喜,渾忘了這重頭戲——地基。那師爺伏身,拿頭在前,正待入港,卻猛一激靈,退爬而出。妻與俺不明就里,趨前探視,卻是黑漆一片,不識個中乾坤。拿個明火一照,卻見黑泥一池,俱作湯狀。那徐娘原是金玉其外,地基已然損壞經年,不堪用度。
妻與俺白空喜了一場,當即辭了親家,毀了婚約。
妻與俺費時月余,心力俱勞,壞了幾百兩銀子,用竹籃子打了一回水。痛定思痛,舍徐娘,改二八佳人。
卻說夷地金山半島已無余地可建新屋。離機場附近有一小城喚作南舊金山。區(qū)內常有云霧相伴,不見陽光。炎夏甚是凄冷。居民俱為建筑工、水管工、電工藍領。離城區(qū)不遠有山岡地一片,原作花圃,被個商家沽下,辟為新屋之所。妻與俺看過樣屋,填好請狀,報備錢莊放款具狀,自回家等候消息。
約旬余,那商家告,周六首批10戶新屋出售。妻與俺挨到周末,顧不得貪床,起個大早,沐浴更衣,自投商家去。盞茶工夫,早望見商家。周圍皆做工場,各式建筑用料堆滿周遭。三棟樣屋,孤零零地矗著,用各式彩旗、氣球團團圍住。門前辟一空地,約百尺見方。早填滿了黑壓壓的人群,約二三百號。走近一看,各人手持一紅紙,盡書所售房屋大小、方位、式樣、價碼。妻與俺擠上前去,報上名號,見過商家,受過紅紙,自候作一處。
頓飯工夫,新屋銷售開始,三兩店小二舉過一牌,立于場前,上秀是日所售之屋。一主事自拿出名單,開始唱名。被叫之人,有若中舉,自慌不迭搶至臺前,顫抖地指向鐘情之屋。主事自將一小紅旗貼于其上,謂之名花有主。那主事如此這般管自叫號,被叫之人無不喜氣洋洋,興奮莫名。妻與俺踮腳、伸脖、豎耳,兩顆心,上下起伏,撲騰不定。那主事并無體諒妻與俺的心情,一路唱將下去,并未見妻與俺的名號。妻與俺只好收起企盼之心,揣著落寞,鎩羽而歸。
兩旬過后,那商家又告,二期銷售周末開始。至周六,妻與俺循例起早,穿戴齊整,打了包袱,投商家去。妻與俺這回是熟路輕車。下得車來,徑奔商家,取過紅紙,移過一隅,仔細詳查。那所列之屋與頭回別無二致,價格卻加了萬余兩銀,頗似黑店。妻與俺幾經周折,瞧眼下這陣勢,早已是刀俎上的魚肉,自由人割宰,半分由不得自己。那店小二循前掛牌,主事亦循前唱號。唱到第一人時,并無人應答;再唱,猶是無人應答;如是者三,算作棄權。
再叫時,赫然卻是妻與俺。俺卻不敢相信,只覺得四周皆死一般寂靜,一無聲響。被妻一拉扯,方回過神來,磕磕絆絆擠到前場,恍恍然選了一戶,退下陣來。稀里糊涂做了一回狀元。妻與俺所得之屋,并非現(xiàn)屋,尚需時日建造。妻與俺又費時若干,跑了幾百里山路,選定廁所、地磚、地毯、灶臺等一應所在之材料,顏色,交與商家。自在家等候,每遇周末,轉至工地,覷個幾眼,留三兩照片。并無曲折。
不久,新屋建成。妻與俺往過戶處交了銀兩,取過鑰匙,自此聊居于此,生子度日。轉眼幾年過去,兒戴著小博士帽由幼兒園畢了業(yè)。妻與俺惶急著打探學堂。四周的公立學堂俱是濫竽之輩,不合用度。原來在夷地置產,有個說道,地點是唯一之要。所謂地點好,學區(qū)好是為首要。妻與俺當年貪便宜圖方便,如今周遭竟找不到一間像樣的學堂,嘗到了苦果。說不得,只好將兒送到境內一基督教私立學堂。那學堂,只大樓一座,四處并無綠樹草地。樓內頗顯黑暗,有若監(jiān)舍。平日所學除算學外,俱皆圣經。兒自入得那學堂,每日心事重重,失卻了笑臉。卻說一日俺與兒閑聊,問及兒與何人最親,兒回說,God。妻與俺辛苦將兒拉巴得將將不用端屎把尿,那God就要將俺兒騙走。妻與俺斷冒不得這個險,只好將那屋胡亂打扮一下,將就著變些銀兩,逃往他處,重回蝸居。
(三年后俺用自己的地產執(zhí)照,另購一屋,自是后話。)
認罰
2011年新年剛過,俺帶著兩個童黨由舊金山經19街上高速280,再接高速110一路南行。車過機場,童黨嘴饞,要吃一種夷地飯食喚作漢堡的。這漢堡制作甚為簡單,拿火雞肉、牛肉、雞肉,剁為碎末,或放火中烤,或入鍋中煎。至熟,置兩片面包中,加兩片酸黃瓜,一片菜葉,一片西紅柿,佐以些許醬料即成。滋味不敢恭維。果腹尚可,要談色香味,可是不入流。擱俺中土,充其量乃憶苦思甜時的道具。
童黨要去的店喚作進進出出(in out)。這進進出出做出的漢堡與眾不同,食材俱是新鮮,就連炸土豆條,也是用新鮮土豆炮制而成。做出的漢堡,算是個中極品,在夷地頗得人緣。進進出出的夷人有白皮、黑皮、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絡繹不絕,生意火得緊。這漢堡做的確有獨到之處,這店名起的可是琢磨不得。各位看官,這果腹的玩意兒自然是需進出兩個程序。雖是進出有個上下起承的關系,沒有進何來出?沒有出何能進?這進的地方可見可說,這出的地方尋常時且想不得,說不得,況乎進的時候?
話說俺拉著兩個童黨,下了101右轉上了迷爾布雷大道(Millbrae Ave)。進進出出的幌子在道左發(fā)出耀眼的光芒,后座的童黨齊齊歡呼。路前迎面一紅綠燈,俺循例靠左,準備左轉。這紅燈區(qū)有個說道,貌不驚人可是遠近聞名。不知哪個天殺的主兒,弄出個照相的勞什子,安插于此,多少英雄好漢在此落了難,毀了一世英名。果是迷爾布雷,非浪得虛名。俺知所厲害,自打起十二分精神,拿兩手攥緊輪盤,拿兩眼死盯左行燈號。大氣也不敢喘,只心說道,娘的,但凡見了黃燈,打死俺也不走,看誰狠!彼時有5輛車排在俺前面。綠燈亮時,前面的車依序左轉。緊靠著俺前面的小車打了回轉,一溜煙重上高速。到俺時綠燈仍然閃亮,俺隨著前車回轉后右轉去了進進出出。找到停車位,入位、換擋正要熄火,透過后視鏡赫見紅燈閃爍。一公人頭戴白色警盔,全副披掛,計有通話器、手槍、手銬、警棍、警徽,正跨下電驢子。俺的心就此一咯噔,卻不知犯了哪項天條。
那廝靠近前來,對俺道:
“早安,先生。請出示駕照。”
俺暗自琢磨,此番休矣。這廝上來不問緣由,直奔主題,一張罰單十有八九是有來無回了。依令奉了駕照,那廝又問道:
“知道我為什么截你嗎?”
俺堆起滿臉的無辜,回道:
“不知!”
“這里是禁止回轉的。”那廝又說。
敢情俺只顧看左邊的信號,沒見到正前不能回轉的幌子。一不留神,被這雷給炸個正著。
“先生,俺只是跟著前面的車輛。”俺把滿臉的無辜換成一臉的委屈。
“是的。我看見了,我一次只能抓一個。”那廝雖未獰笑,卻分明得意得緊。
幾年前俺一兄弟在280上跟著一群車瘋跑。行在最后,被個公人拿下。兄弟不服,上了公堂。那縣吏問,一個樹上有很多只鳥,一槍能打下幾只?俺兄弟被問了個張口結舌。想到此,到嘴邊的為何拿俺不拿他的話,被俺生咽了回去。
“你的駕駛記錄如何?”那廝仿佛要氣俺。
“從1994年來到加州從未吃過罰單。”
“非常好!”
“那意思是,俺今天不走運!”俺氣不打一處來。
“不全是,你等等。”
那廝回到電驢子前,俺升起了一線希望。
這夷地有個規(guī)矩,倘使公人開了罰單,抑或是只寫了一個點,又或是公人已知罰單開錯了,這罰單也是要開出的,斷作廢不得。有何冤屈到公堂上喊,那公人自會到場還你個清白。
那廝再過來時,退還了俺的駕照。又讓俺在一2寸寬5寸長的紙上畫押。
“你會在3周內收到公堂文書。告知你罰金事項。你有權去公堂申述。你同時可上駕校,考試合格后,免去你的駕駛計點。”那廝給了俺一黃色收據。
那黃色收據上記有如下內容:
日期,時間,星期幾;罰單號;俺的姓名,住址,駕照號碼,出生年月,性別,頭發(fā)顏色,眼睛顏色,身高;俺的車牌號碼,州別,出廠年份,廠牌,型號,顏色;所犯事由,車速,地點;公人姓名,所屬衙門。
俺攥著這黃條,有若抱著一炸彈。每天惦著那公堂文書。想著它來,盡早了了這劫難;又怕它來,不知是多大個雷,俺消受得起不?幻想著公人犯了錯,它永遠不來;又怕它不來。倘使寄丟了,誤了付款的時間,那可是罪加三等。見天回家第一句話就是來了沒有。搞得自己倒有些祥林嫂起來。
也就是時間將將滿21天那一日,一封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圣馬刁縣最高法院中央分部的通知寄到了俺家中。俺掂量半天,卻不敢打開。做了幾次深呼吸,勉強打將開來。見通知上寫著俺的案件號碼。罰銀234兩。駕校注冊費用57兩。俺必須在2月28日前通過以下方式與公堂聯(lián)系:
1.出席公堂;
2.網上聯(lián)絡;
3.電話聯(lián)絡;
4.郵寄付款。
這夷地有個規(guī)矩,公堂開時,為公平起見,縣吏讓兩造公堂回話。倘使一造無故未到,另一造自然取勝。有一慣犯,深得其中奧妙。開堂時間到時,數(shù)度推延堂期,搞得那公人不勝其擾,最后自我放棄。俺有心如法炮制,寄希望那公人屆時或忙或病或出交通事故或被裁員,總之不能前來,好歹讓俺逃過此劫。又聞山姆大叔如今貧賤能移,英雄氣短,常為五斗米折腰,況乎幾百兩銀子的計較?
依著公文的路引,硬著頭皮電話公堂。不料輸入俺的姓名,案情號碼,卻找不到俺的記錄。再輸入俺的駕照號碼亦是不得門而入。換了上網俱是如此。敢情俺沒有案底,乃一清白之身?取過公文祥察,赫見俺的姓名錯了。想到那公人“不全是”的禪語,莫非公人放俺一馬?有心就此了過,卻是放心不下,不得已往公堂上走上一遭。期待這案底一筆抹消。
第二天起個大早,7點到了公堂。卻見公堂前一溜煙兒排了一長串男女,到了房子轉角處。俺杵在后排。不一會兒,后來的男女將個隊伍拉到遠處再轉個彎,看不見了。7:30出來一攜槍公人,口報入堂規(guī)矩,前面男女明白后方才開門。眾人不敢造次,依序入內,十分緩慢。輪到俺時,方見需要安檢。俺將袋中銀包、鑰匙、手機,放入筐中,復將腰帶解下,雙鞋脫下一并放入筐中。將小框推入一黑乎乎小窗口,滑行入內,卻不知它們的命運如何。俺提溜著褲腰,哆哆嗦嗦過那安檢門。幸喜無事,過了一關。入得屋內彎彎曲曲又見一隊,惶急將一應物件納入袋中,提著褲腰站在隊尾。也不計較,將臥室與茅房該辦之事,眾目睽睽下辦了。方才抬眼望望窗外的自由世界。
8時余挨到窗前處。但見一溜小窗口,倒有七八個之多。前面的人出來各人拿了一白紙,所寫為何卻是不知。輪到俺時,窗內乃一西夷女將。臉上的肉甚為富裕,說話粗聲大氣,有孫二娘的風采。
“所為何來?”孫二娘問道。
俺將個罰單的前世今生備報完畢。滿心期望二娘法外開恩,放俺一馬。不料那二娘視俺為肥羊,入了包子鋪,豈容得俺生還?
“名字錯了,地址對嗎?”
“對”
“駕照對嗎?”
“對”
“名字改過,你今天要過堂嗎?”
幾番下來,俺早已入了二娘的彀,空余說“對”的本事,全無說“不”的膽量。
那二娘依例拿出一張紙,在上面寫了一“G”字,說:“8:30 G堂。”把俺打發(fā)了。
俺接過那催命符,但見上面寫滿洋碼,無一漢字。用的盡皆律法之語,倒有一半不識。猜了許久,大意是:
交通違章者權利忠告
1.有權在公堂辯護。
2.有權請辯護律師。如因經濟原因無力雇請,法院可為你指定律師。
3.認罪或不認罪,都不會影響將來你在民事訴訟中的權益。
4.你將面對盤問和證人的作證。
5.你有權利用法院傳票的權力來強迫證人為你出庭。
6.憲法特權,你不能被迫成為自證其罪的自我見證。
7.你的案件審理期為45天。特別情況可以改變。
8.如果你是一個輕罪指控,你有權要求陪審團審判。
9.如果你被定罪,你有權要求延遲宣判。
10.如果你想承認有罪,并作出解釋,你可在認罪后做出。
挨到時辰,遠遠聽見G堂附近有人唱號。擠到前面一瞧,見一公人被眾男女擁堵著,拿著一沓白紙,不斷唱名。被念到的人,沿著一小門,一頭栽將進去。卻不知里面是天堂還是地獄。俺瞧那公人,除未戴花翎外,通話器、手槍、手銬、警棍、警徽俱是齊全。操弄著這眾人的生殺予奪大權,愈發(fā)顯得威風。約盞茶工夫,俺的大號終于從那公人嘴中蹦出,俺的姓卻變成“譚”音。也不敢與之計較,乖乖入了甕中。
那公堂不大,卻是煞氣重重。正面墻上高懸一信天鳥。地面上矗著兩面旗,一國旗,一州旗。縣吏的堂案高高在上,不見何物為之持平。驚堂木變作驚堂槌。下來兩個臺階,右邊一座位,面對案犯,卻是虛空著。左邊一座位,亦是面對犯人,上坐一女將,模樣像師奶。師奶右下手,一男將面壁而坐,前置一電腦。再下兩級臺階,到了平地。前置一條案,為案犯們準備。過堂時案犯們需站立于前,接受詰問。縣吏、師爺們由上往下,自有一番氣勢。犯人們在心理上先自輸了一陣。有理的變成平理,平理的變成失理,失理的變成無理。條案旁邊坐一女將,不知所為何來。余為案犯席,共5排,每排14座,中間一過道。案犯的位置循序排好,不可亂坐。
眼見疑犯到齊,座無虛席。那師奶也不站立,對眾人吼道:不得說話,不得咆哮公堂,關閉手機等一應物件,倘若違犯,逐出公堂。續(xù)道,給各位忠告,如若不認罪,需另行安排庭審。庭審若判你有罪,你會失去降低罰金的機會,同時喪失參加駕校減免計點的機會。雖是忠告,話里話外,卻是極盡威脅。令俺想起中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古訓。頗有認罪減罰,辯誣嚴懲的風韻。
師奶話畢,旁邊座位上一人忽地站立,卻是那叫號的公人。也不知何時爬將上去的。那公人平地一聲吼:“肅靜威武。”眾皆起立。這時屏風后轉出一通體裹著黑布的白皮女將,乃今日通判縣太奶奶。那縣太奶奶,也不寒暄,直奔主題。叫了第一個案犯。
這案犯乃一妙齡女子,由父親作陪。那縣太奶奶先問了有無讀過“交通違章者權利忠告”再談案情。原來小女子開車沒有帶車險證書。
縣太奶奶問曰:“可服罪?”
答曰:“當日忘帶,今日卻有。煩請過目。”
“遞將過來。”縣太奶奶命道。
那事主離那縣太奶奶甚遠,不知如何傳將過去。那公人卻早早站立,一手接過,復轉身低頭弓腰雙手遞將上去。那縣太奶奶瞧也不瞧那公人,一手接過,并無言謝。俺看得有些癡,想那公人在堂外時如何八面威風,如今卻如小李子見了光緒爺他娘。縣太奶奶看過事證,頭也不抬,道:證據接受,罰金25兩。隨手將案紙與事證往下一丟。那物件并無落地。原來那三樓與二樓間有一木板連著,作滑梯狀。那師奶見紙張滑落,連忙接著,將案紙收好,事證交與事主。
第二個嫌犯亦是一女將,傍著一訟棍。兩人皆西裝革履,打扮齊整。女事主乃一飛將軍,因超速被緝拿歸案。如今面臨吊銷駕照的命運。那訟棍解說,我的事主乃一安分守紀的良民……話尚未說完,被個縣太奶奶不客氣打斷,照紙念道,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超速,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闖紅燈……嘲笑道,良民?那訟棍再圖解辯,再被縣太奶奶無情打斷,罰銀400兩,吊銷駕照30日。訟棍復不敢言,落荒而逃。
第三嫌犯乃一西夷白皮男將。整個一勞苦大眾的穿戴,蓬頭垢面。回話時答非所問,牛頭不對馬嘴。條案旁的女將霍地起身,原來是一通譯。西夷闖紅燈被個照相機拿下,卻是不服罪。這廝如不是有天大的冤枉,便是壽星公上吊活膩味了。那縣太奶奶想也不想,判道,下次再來。座前的師奶在案上一通亂翻,唱到某年某月某日再次開堂。
眾嫌犯見此陣勢,再想到師奶認罪減罰,辯誣嚴懲的脅迫,均不敢造次,一概服罪。縣太奶奶將罰金略為減免,問道,今日付還是某月某日付?無非是初一、十五的距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Jian Tian,”縣太奶奶一聲吼,倒也字正腔圓。俺被那氣勢嚇著,跌跌撞撞上到堂前,尚未站穩(wěn),耳邊已響起問話:
“有無讀過‘交通違章者權利忠告’?”
“有。”
“服不服罪?”
“服。”
“罰銀177兩。今日交還是某月某日付?”
“今日。”
攏共一分鐘,敗下陣來。出得公堂,見先前出來的難友著一路縱隊排在來時的窗口。那窗口們來時像砧板,將俺等做魚肉。現(xiàn)時搖身一變化作吸金口,各人乖乖將血汗所得奉上。里面的想不收都不行。可比周扒皮同志的道行深多了。
俺逃出魔窟,擇日繳費上過駕校。一場劫難就此塵埃落定。兩個漢堡,兩盒土豆條,兩瓶可樂,搞得俺官司纏身,復壞了200兩銀子,是為高消費,當真腐敗。
責任編輯 王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