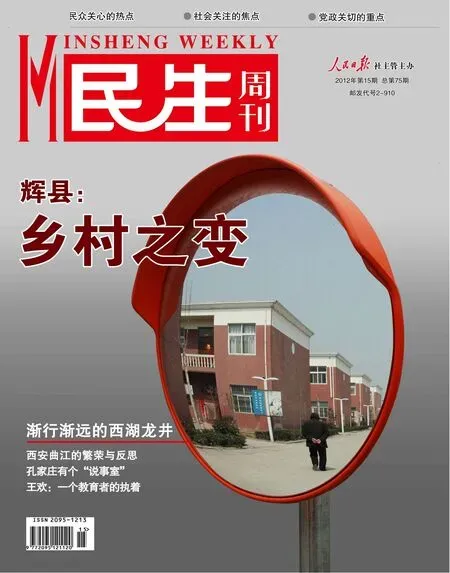證件空缺的農村社區房
——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輝縣探索
□ 本刊記者 丁筱凈
證件空缺的農村社區房
——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輝縣探索
□ 本刊記者 丁筱凈
曾有觀點認為,在全國,新型城鎮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都是一場“戴著鐐銬的舞蹈”。而這把鐐銬,正是我國實行了63年的城鄉二元結構。
截至3月29日,河南新鄉輝縣市已經有1.3萬名農民“上樓”了。新鄉市稱這些住進社區的農民為“城鎮居民”,而不再是“農民”或者“村民”。
“新鄉市里說要給這部分人辦理統一的‘新鄉市居民戶口’,意思就想叫他們城市居民,讓搬進社區的農村享受城市的待遇。”輝縣市新農村辦公室副主任原官喜說。
但是事情遠不是稱呼 “農民”還是“居民”這么簡單。在戶籍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打破的情況下,要讓上樓農民真正“享受城市待遇”,可謂難之又難。
這個問題,在房屋問題上就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談到能讓這一部分新居民享受什么樣的待遇時,原官喜坦言:“這個(讓他們享受市民待遇)我感覺很難。新鄉畢竟是地級市,沒有那么大的權力。比如新鄉市原來有文件說會給農村社區居民發房產證,但房產部門就指出我們農村社區辦理房產證的相關證件不齊,沒法辦理。”
房產證:市內探索
在輝縣市裴寨社區采訪時,當地居民告訴記者,他們現在住的二層小樓是由村支書裴春亮個人出資建設,并免費發放入住的,他們沒花一分錢。但是,關于這沒花一分錢的房屋的任何證件卻沒發到居民手中。
“除了一把鑰匙,什么都沒有。”村民裴春花(化名)告訴記者,如果村民不想要分配的房屋,那只能直接上交給村大隊,得不到任何補償。并且,這房子不能租、不能賣,只能自住。“我們用耕地、舊房屋和原來的宅基地換來的這套房,卻不能給我們任何保障。”
一氣之下,裴春花和丈夫花了7萬元在社區規劃的商業街上買了一個店面,二樓自住。搬進商業街以后,裴春花發現生意很冷清,“我們社區周圍沒有工廠,大家都上外面打工去了。”裴春花說,就連這個二層店面,也沒有任何正規的使用證件,還是不能出租、不能賣。因為買店鋪、裝修、購置新家具花光了他們所有的積蓄,裴春華稱自己“被困在這里了”。
而在澗頭社區,雖然入住一年多的房子沒有任何房產證,但居民并不擔心。在隨機采訪中,多位居民告訴記者,村里已經把他們的相關證件都收上去了,說“會給大家統一辦理房產證”,只是現在還沒有辦下來。
在記者多天走訪的數個農村社區里,居民無一例外地都沒有拿到任何房產證明。根據《物權法》,不動產實行登記制度。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
根據建設部《城市房屋權屬登記管理辦法》,國家實行房屋所有權登記發證制度,房屋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依法擁有房屋所有權并對房屋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權利的唯一合法憑證。
對此,新鄉市自己也在探索。據原官喜介紹,原來新鄉市出臺了一份文件,要求下面區縣給所有住進農村社區房屋的居民發放房產證。但在實施過程中,卻受到了城鄉二元結構的牽制。“由于農村社區用地仍然是農村集體土地,房管部門說你要辦房產證,依據現行政策必須有土地許可證、規劃許可證、建設許可證等等,但是農村集體土地沒有這些,所以房管部門辦不了大產權證。”原官喜無奈地說。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作為河南省唯一的統籌城鄉發展試驗區,新鄉也在現有條件下做出了自己的探索。
原官喜透露,近日新鄉市有關部門開了會,研究了農村社區的房產證問題。給出的會議文件中表明,新鄉市有發放本市范圍的房產證的想法。“蓋的可能是新鄉房管部門的章,這是最大的不同。”原官喜說,“之后可能會讓農村社區居民帶上身份證、由社區開具的住房證明,到房管部門辦理新鄉范圍內的房產證。”
原官喜介紹,這個屬于新鄉市的房產證是新鄉在二元結構沒有打開的條件下的小范圍探索。他透露,這本新鄉房產證將來也許可以做到在鄉鎮范圍內流通,也可在銀行進行抵押貸款。
宅基地:上樓中失去
調查中記者發現,“新鎮民”缺失的不僅僅是關于房屋的合法憑證,就連法律賦予每戶農民的宅基地,也在上樓的過程中失去了。

目前城鄉二元模式還沒有放開,全國的城鎮化工作都只能“先試先行”,在小范圍內活動。圖為輝縣市澗頭村在建的社區住宅樓。圖/丁筱凈
在《澗頭村整體改造實施方案》中注明了這樣一句話:“原宅基地、田工地統一使用,原宅基地證同時廢止。”對此,郭永生的解釋是:“宅基地是白紙黑字的,這(實施方案)是我寫的。我也是怕將來需要把房子拆了,他拿個證說這是我地方你不要動,所以當時就加了句‘宅基證同時廢止’。”
事實上,宅基地的失去并非個案。在輝縣市的農村社區建設過程中,所有農民都失去了自己的宅基地。對此,輝縣市農辦主任郜六零給記者的答復是:“對于宅基地問題百姓反映得非常多,法律也支撐,群眾的要求絕對是對的。失去了宅基地就失去了應有的權益。”
我國關于宅基地的分配,長期以來實行“一戶一宅”的政策 ,指農村居民一戶只能申請一處符合規定面積標準的宅基地。但是由于近年來城市擴張迅速,為保證農民權益,國土資源部在2010年專門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完善農村宅基地管理制度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的通知》。其中說道:“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擴展邊界內的城郊、近郊農村居民點用地,原則上不再進行單宗分散的宅基地分配,鼓勵集中建設農民新居。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擴展邊界外的村莊,要嚴格執行一戶只能申請一處符合規定面積標準的宅基地的政策。”
按照這份通知,目前輝縣市在推行新農村社區的過程中,對于近郊和城鎮邊界之外的村莊,應該區別處理。對此,輝縣市國土資源局規劃科一位不愿具名的負責人告訴記者:“輝縣市目前分城鎮規劃區和非城鎮規劃區,而新型農村社區屬于非城鎮規劃區之內。”
按照這位負責人的解釋,入住輝縣市新型農村社區的原村村民,依照規定還應擁有“一戶一宅”的宅基地。但郜六零表示,在現有條件下推行農村社區建設,取消部分宅基地分配也是合理的。“住進小區的居民就沒有什么宅基地了,都是集體建設用地。我們在推行的時候,群眾同意(取消宅基地)才會搬進小區居住。單家獨院有很多優勢,但是現在農民都愿意住進樓房,過城里人的生活。”當記者追問這樣做是否合法時,郜六零表示,新鄉是國家級實驗區,有好多繼續沿用的政策已經不適應當今情況,以后都要修改,所以實驗區可以進行適當的先行先試。
受到城鄉二元結構制約的,不僅僅是農村居民的房屋和土地。在戶口本上,這些“城鎮居民”的名字依然打著“農業戶口”的標簽。而這個標簽給這些居民帶來的,是二元結構下由法律法規劃出的城鄉落差。
曾有觀點認為,在全國,新型城鎮化、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是一場“戴著鐐銬的舞蹈”。而這把鐐銬,正是我國實行了63年的城鄉二元結構。
如何“帶著鐐銬跳舞”?輝縣還在繼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