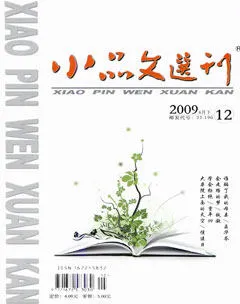母親的往事
任 勇
母親看不見了,兩只眼睛都看不見了。在北京同仁醫院住了一個多月,同時在幾個權威醫院的專家那里都作了診斷,都沒能治好她的眼。我們都很傷心,也很無奈。她的眼是因為視神經萎縮而看不見的,而神經萎縮目前醫學界還沒有成功的辦法來治療。我們只有給母親吃各種營養神經的藥,我們只能抽空陪母親多聊一會兒,讓母親那顆無助的憋悶的心,稍微得到一些撫慰。
母親看不見以后,說特別的憋悶,現實的看不見了,就常常有過去的事兒在眼前閃動。過去人常說,人的命天注定,我從來不相信,現在我真有些信了。母親從小就特別的命苦。
母親講,她的親生父親在她還很小的時候就走了。姥姥帶著她改嫁,后來姥姥又生過幾個孩子,但都沒有活下來,由于奶水充足,就給人家當奶媽,再后來干脆就抱養了一個小女孩。這個小女孩就是唯一與我們兄妹幾個感情很深的姨。姥姥她生孩子多死的也多,對她打擊很大,加上沒錢看醫生,弄得一身的病。記憶里的姥姥一直都是個氣喘噓噓抬不起腰的小腳老太,仿佛從來都沒年輕過似的。母親的繼父,也就是我們唯一見過的姥爺,是個性格剛毅、善良勤勞的人。母親打記事起就開始幫助姥爺做各種各樣的活兒,包括男孩子要干的活兒。姥爺對她們母女很好,在母親的心目中,他就是唯一的父親,因為她的親生父親從來就沒盡過一天當父親的責任。
那年月兵荒馬亂的,姥爺一直是在有錢人家做私家廚子。家里的大小事情就都落在母親還很瘦弱的身上。可以這么說,比母親整整小一輪同樣都是屬雞的姨,是我母親從小帶大的。她們姐倆的感情,可想而知。除了帶妹妹、挑水做飯做家務外,母親還在姥姥的教導下,給全家人做衣服,做鞋。說是做衣服,實際上就是把攢下的洋面袋或包袱皮染成羊肝子色,然后做衣服,剛做的衣服是大人們穿,后來打了幾次補丁后就是母親和姨穿。做鞋,要自己打千層底,再一錐一錐一針一針地納鞋底,做鞋幫。母親說不知道做鞋的時候扎破多少次手,只知道年輕的她,手卻過早的變得粗糙。母親還要到外面拾柴禾揀煤渣,就象《紅燈記》里的李鐵梅一樣。揀煤渣要到火車站下面的鐵軌上去拾,拾煤渣的不是大人就是男孩子,唯有母親是姑娘去揀的。有時一去就是一天,又怕又冷又餓的一天。
那年月挨餓是常有的事。母親一家人到了晚上,就都守在煤油燈下等著在外面做活的姥爺買吃的回來。老爺不論干活多晚總是買一點米或面回來,全家人就這樣多了多吃少了少吃,在已經很深很深的夜里,吃下全天里唯一的一頓飯。
后來母親長大一些,舅姥爺給母親攬活干,用針線把一小塊一小塊的羊皮、狗皮、兔皮縫接在一起,一天要目不轉睛地干八九個鐘頭,才能掙幾分錢,干一年掙得錢也不夠做一身花布衣,可那也讓當時的母親感到生活有了奔頭,能給家里賺錢了,能給姥爺減輕一點壓力。
后來解放了,共產黨的部隊來了。有人介紹母親為一個軍官看孩子,也就是如今的小保姆。那個軍官待人很和靄,沒有想象中的軍官那么可怕,尤其是那軍官的夫人更好,與一般的公家人沒有二樣,待母親像待妹妹一樣親切。她跟母親說年輕輕的,要念點書,要學文化,還抽空教給母親認幾個最簡單的字。后來那個軍官要開拔了,那個夫人跟我母親提出可以跟隨她們到北京去,母親也不知北京有多遠,也不知跟她們去北京會怎樣,就一口回絕了。母親畢竟是沒見過世面的小女子,她那個時候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吃上一頓飽飯,能穿一身花布衣,她跟著人家到外面去的事是從來也沒想過的。到后來,那軍官走了很長時間以后,她才知道那個軍官是個很大的官,那軍官叫趙漢,是共產黨進大同后,接受國民黨政權的共產黨代表,是家鄉解放后的第一任市委書記。
第二年,母親由姥爺做主與父親成了親。那年母親也就只有十七八歲。父親小時候讀過書,父親在共產黨進大同那年參加了革命,當時在公安部門做警察。父親的父親是個做小買賣的,雖沒有什么產業,但一家人還能維持一般的生活。所以母親從出嫁那天起,生活才算是有了實質性的改變。改變的第一標志就是能一天吃上兩頓飽飯了。
很快的,母親在八年的時間有了我們四個孩子。為了帶大我們,她省吃儉用,日夜操勞,她四處打零工賺錢以補貼家用。因為父親的收入是有限的,記得在我上小學時,父親只掙六十五元一毛二。母親為了我們有人看管,又不得不幾次辭掉工作。過去的家里,總有母親做不完的活兒。一年四季日復一日,母親都在做這做那,她自己刷房自己拉碳自己拾柴,更不用說還有沒完沒了的家務事。記得最清的是每年年根兒那些天她天天都做到很晚,有時就是通宵地做衣服什么的。在我四五歲時姥姥就死了,在我上大學期間姥爺也走了。姨與我們常常在一起,我們無話不說,但她的身體也不好,經常鬧病,幾年前也去了,那年姨才五十六歲。
多少年過去了,這么多年里發生了多少事,母親都堅強地挺過去了。現在我們兄妹幾個都是五十多歲的人了,日子過得覺夠睡,飯夠吃,錢夠花。父母親都離退休多年了,正到了享清福的時候了,可是母親因為年輕時過度的勞累,已經是一身的病。她長年的腿疼,已經發展為雙膝關節壞死,那幾年連拐杖都很不情愿用的母親,不得不坐上了輪椅。也許是比她小十二歲的姨先她而去對她打擊太大,也許是坐輪椅以來心情一直不好,也許是她的視神經真的發生了病變,也許是其它什么原因。母親在半個月里,兩個眼睛都失明了。我們希望上蒼能把慈愛的光芒照耀在我那一輩子辛勞而又苦命的母親身上,讓她的晚年過的好一些,讓她重新看到這個世界,至少不要再給她降臨什么新的不幸了。
選自《大同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