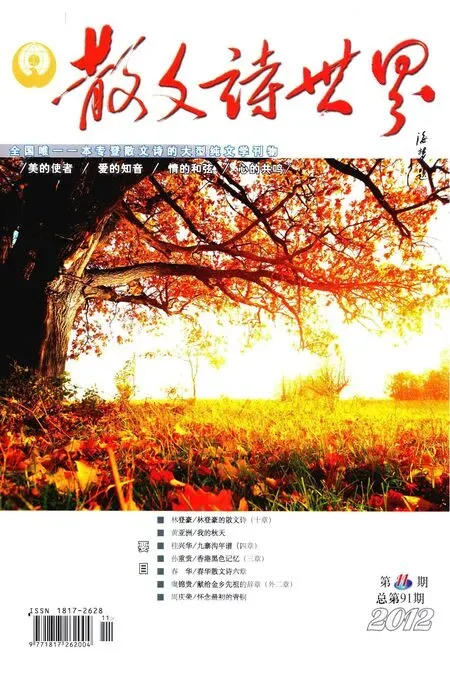燈 籠 草(外二章)
廣西 黃煥紅

一定有什么東西,被遺落。
多年后,一路尋回。
看你掛起小小的燈籠,一盞,又一盞,在屋后的坡岡上,滿懷希望地尋找。心,一下子變得柔軟。
不用掰開那些膜質鼓脹的花萼,每個曾經的鄉村少年都知道,每棵燈籠草的每盞燈籠里,都裝裹有一顆青澀圓潤的心。
這一路走來是有過太多的辛酸,不知該從何說起。那么不說也罷。
要說也只說舊時的明月,雨后初晴的山岡,天上飄忽的云,遠山、近樹,身旁的雜草蓬勃過的欲望,以及身側怒放的花朵,她們燦爛的笑臉曾經蠱惑了多少日日夜夜。
一定還有一只蜜蜂飛過,蝴蝶的翅膀曾經扇動過你招搖的手,少年的身影從你身邊飛快地掠過并迅速追趕上了一只飛鳥的影子。
與少年的情義,是山村坡岡上與一棵燈籠草的相知相惜。
愿意一次次地回望,提著燈籠慢慢尋找。
尋找那些遺失在歲月里的溫軟時光,那些純凈清澈永遠不會再來的菁菁年華。
蒼 耳
風起時,薄公英打開了飛翔的翅膀,告別了童年的青梅竹馬,也道別成長的山村。
被誘惑與牽掛的人,想再保持一貫的沉默,實在太難。
日里夜里,無法遏制蓬勃生長的欲望。
豎起耳朵,蒼耳始終聽不清遠方。一顆心,在塵世的低處,在生活的無可奈何里,落寂憂傷,直至,長出密密麻麻的堅硬的鉤刺。
所有的冥想,都顯得毫無意義。所有的希望與惦念,都不及一次出走和追尋來得真實。
在時光里等待,博弈。讓渴望的手,抓住哪怕僅有一次的機會。
讓生命中路過的那些物種,借路過我身邊的你,從此把我帶走。
去到夢的遠方。
午時花
在鄉下,人們都管她叫太陽花,也叫死不了。
那年月,幾乎家家戶戶都種植有。就在房前、屋頂、院子矮墻上、破盆爛甕里,一捧泥土很容易就養出一片蔥蔥綠綠。
水嫩的肉身,好看,也好養。葉子尖尖細細的,可愛的橢圓形,仿佛會刺人的樣子,終究是水肉做的骨頭。脆生生的腰枝,即使折了,斷了,也不礙事,傍晚回家的女孩會把曬得失水焉焉的花枝揀起,簡單扦插進土里,便活了。
普通、平常,蓬勃、健壯,耐干耐旱,耐瘠薄,更多時候她們站進草的列隊,同野草一樣低矮地活著。命運里有諸多不計較,渾然就是天生的賤命。
最喜是陽光。溫暖、光亮和潔凈的午后,在枝莖頂端,午時花便會羞羞答答展露笑臉,紅的、白的、黃的,單瓣的、重瓣的、半重瓣的,輕輕巧巧,搖搖曳曳著,引來一大幫小姐妹圍觀。細數著花朵,風中還能聽見她們竊竊地笑。陽光越熱烈,她們會笑得越開心,肆無忌憚地,卻天真、純樸、自然。
多年后,重返故地,卻難再尋舊時蹤影。沒有了矮墻,沒有了房前屋頂上鮮活的記憶,那些搖曳生風的笑臉也不見了。
他們都說花朵兒一半被風帶走,一半被牛羊牽走。而你我的鄉間姊妹,有些進了城,有些則去了遠方。
真心希望她們,能像那些午時花一樣,適應性強,耐生,堅韌頑強,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