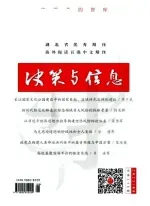鄧小平會見國外首腦言談錄

鄧小平是20世紀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最具影響力和個人魅力的領袖人物之一,他以非凡的理論勇氣、經驗和智慧,從跟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社會面貌,并對21世紀中國和世界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鄧小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新中國成立以后,他先后會見各國首腦達300多次。通過系列的外交活動,推動中國逐步走向世界。下面摘介是他與若干國外首腦會見時的言談及外國首腦的感受,從中可以具體地領略到政治家鄧小平的偉人風采。

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
鄧小平獨特的個人魅力和風格使尼克松難以忘懷。他后來在談到會見鄧小平的印象時說:
“他那急切的決心和絕對的自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離開北京時印象都比上次更深刻。而每一次,他所領導的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變化又加強了我對這位領導人的印象。”
“當鄧把處理政府日常事務的權力讓給他的下級時,西方許多觀察家侃侃而談,認為一位共產黨領袖自愿地、得體地下臺讓繼承人繼續執行他的政策是多么不尋常。觀察家卻沒有看出這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包括民主政體)治理下都是不尋常的。戴高樂貶低了顯然會成為繼承人的蓬皮杜,邱吉爾貶低了艾登,阿登納貶低了艾哈德。鄧在讓位時留下了他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創造了一個杰出的政治奇跡。歷史上很少有強有力的領袖能自己正視——而不是在他人逼迫下——生命總有盡頭這一現實。他說過:‘趁我腦子還沒有糊涂時就退下來。’寥寥數語,生動地反映了他人品的偉大。”
尼克松說,“在我同中國領導人進行的歷時3小時的毫無限制的會談結束時,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確信,鄧小平是當代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我離開中國時,對未來抱審慎的樂觀態度。……我之所以樂觀,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認識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緊縮措施以后,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將會繼續下去,從而必然會重新出現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壓力。我遇到的每一個領導人都表示堅決支持鄧的改革的基本原則。他們都知道走回頭路再搞教條主義只會走進死胡同。”


會見美國總統卡特
在執政期間和卸任后,卡特曾三次會晤鄧小平,在同鄧小平的交往中,卡特深深地為鄧小平獨特的個人魅力所吸引。
卡特說,“鄧身材矮小,坐在內閣會議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幾乎看不到他這個人了。他在出神地聽我講話。他接二連三地吸著煙卷,一對明亮的眼睛常常東轉西看。當譯員把我的話譯給他聽時,他時而發出笑聲,時而對其他中國人員頻頻點頭。”
卡特回憶:“在宴會桌上,這個很受歡迎的伙伴談話輕松自如,自始至終都滔滔不絕地介紹他國內的生活情況,并談論他認為國內情況如何好轉。我們很風趣地談到了我孩提時代就很感興趣的基督教傳教士的傳教計劃,他不無勉強地承認也有一些好的傳教士到過中國,但是他又堅持說有許多傳教士到中國去只是要改變東方的生活方式,使之西方化。”
卡特在當天的日記中以頗具感情色彩的筆觸寫道:
“我們在肯尼迪中心觀看了一場很輕松的演出。后來我和鄧、鄧的夫人卓琳、羅莎琳以及艾米一起登臺與演員們見面。當鄧擁抱美國演員,特別是擁抱演唱中國歌曲的小演員時,流露了真誠的感情。他親吻了許多兒童,后來記者們報道說不少觀眾甚至感動得流淚了。”
“鄧和他的夫人似乎真誠地喜歡人民,他確實轟動了在場的觀眾和電視觀眾們。”“那天晚上艾米和其他孩子們都非常喜歡挨著他,同他在一起,其實雙方似乎都有這種感情。”
“我對鄧的印象很好。他個子矮小,卻很健壯。他機智、豪爽、有魄力、有風度、自信而友善,同他進行會談是愉快的。”
當兩國領導人再次握手時,鄧小平興奮地說:“現在兩國人民都在握手!”
鄧小平這句富有感情、意味深長的話也深深地打動了卡特,此時,他把鄧小平的手握得更緊了。
卡特十分喜歡鄧小平這種想什么就說什么的開朗坦率的性格。鄧小平在會談中所表現出來的大家風范以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也使卡特欽佩不已,在他看來:“中國人似乎知道如何表達他們對國家的自信和自豪,卻又并不傲慢。在這一過程中,我明白了為什么有些人說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
鄧小平對卡特說,“我真誠地希望中美關系不要停滯,要繼續發展下去。發展中美關系是全球戰略的需要,也是中美兩國的共同需要。”
會見美國總統里根
里根后來在回憶錄中是這樣描繪他與鄧小平會見的情形的:
“第二天是我訪問中的大事。我同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會晤。他個子矮小,但肩膀寬厚,有一雙烏黑并令人難忘的眼睛。當我們見面時,鄧表現出調侃式的幽默。南希跟隨我出席了正式介紹儀式,鄧笑著邀請南希將來獨自再回到中國,好讓他帶南希到處看看。”
會談中,鄧小平嚴肅地對里根說,“中美關系中的關鍵問題是臺灣問題,希望美國領導人和美國政府認真考慮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國政府為解決臺灣問題作了最大努力,就是在不放棄主權原則的前提下允許在一個國家內部存在兩種制度。”
鄧小平希望美國不要做妨礙中國大陸同臺灣統一的事情。他說:

“海峽兩岸可以逐步增加接觸,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統一。統一后,臺灣的制度不變,臺灣人民的利益不會受到損害。臺灣同美國、日本可以繼續保持現有的關系。我相信我們這個辦法是行得通的。臺灣問題解決了,中國同美國之間的疙瘩也就解開了。”
里根回憶說,“作為主人,他開了第一槍。接著輪到我了。我竭盡全力反駁他說的每一件事,糾正他的事實以及數據,不管他是不是主人,因為是他首先發難,所以我不會讓他感到輕松。爾后,我驚奇地發現他又突然變得熱情起來,笑容又浮現在他的臉上,并且他似乎想調和一下剛才緊張的氣氛,使之變得融洽一些。然而,這并不能使他不提及我們與臺灣的友好關系問題,他認為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我告訴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臺灣之間的裂縫是個要由中國人來解決的問題,只是美國想讓它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罷了。”“當我們暫停談判就餐時,我們先前爭論時的緊張氣氛轉換成了親切和愉快的社交形式,到處都在碰杯,那時,我自忖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
會見美國總統布什
20世紀70年代時,在杰拉德·福特擔任美國總統期間,布什曾于1974年10月至1975年12月擔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
布什以較多的、生動的筆觸描述了與鄧小平的會談:“我曾見過鄧小平幾次。當時,他的地位正處于上升階段,很可能在毛澤東和周恩來去世后接任國家最高領導職務。他抽起煙來一支接一支,喝起茶來也是一杯又一杯。他把自己打扮成來自中國西南四川省的土生土長的農民的兒子和歷經風雨的軍人。”
“鄧小平是那種在同外國領導人交談中強硬和和藹都運用得恰如其分的人。但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他明顯地傾向于強硬。”
“鄧,像毛和其他中國領導人一樣,對美國面對同蘇聯的冷戰所采取的政策方向十分關注。”
會談中鄧小平強調:“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穩定的政治環境。總的來說,中國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他們知道離開國家的穩定就談不上改革和開放。”
鄧小平進一步指出:“中國正處在特別需要集中注意力發展經濟的進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結果是既實現不了民主,經濟也得不到發展,只會出現國家混亂、人心渙散的局面。對這一點我們有深切的體驗,因為我們有“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親眼看到了它的惡果。”
在各國政府首腦人物中,喬治·布什可以稱得上是與鄧小平接觸較多者之一。鄧小平的氣質、風格等都給布什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
鄧小平對舒爾茨說,“中國有兩條是重要的:第一,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二,要搞社會主義現代化,要使中國擺脫落后狀態,沒有穩定的政治形勢是不行的。我們一定要有一個穩定的政治局面,有秩序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些問題,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直這樣講,從來沒有變過。我們的既定政策不會改變。”
鄧小平還說,“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國外有些人過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別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錯;如果要說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較正確地說,我是實事求是派。”
舒爾茨對鄧小平的這一觀點表示贊同,并說,中國有著很好的發展基礎。中國的沿海經濟發展區為增加出口而進行的努力特別令人感興趣。中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和物價改革,也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舒爾茨認為,“鄧小平的頭腦非常清楚,對國際上的事情了如指掌,極為坦率和富有遠見地談了他對有關問題的看法。談到中美關系時,鄧小平說,中美關系的發展是比較穩定的,當然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既然是兩個國家,存在一些分歧也是正常的。總而言之,中美是兩個大國,而且都有發展的余地。從世界和平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我們需要發展關系。”


會見美國國務卿基辛格
1979年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在接受《時代》周刊采訪時,告訴記者他對鄧的印象:“很顯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對于政治,他極為精通并能游刃有余。總之,鄧是一個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響將是巨大的!”
1989年10月,在中國發生動亂和中美關系緊張的嚴峻時刻,基辛格再一次到中國訪問。剛剛辭去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是鄧小平完全退下來后第一次會見外賓。
鄧小平當著幾十名中外記者的面對基辛格說,“博士,你好!咱們是朋友之間的見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經退下來了,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制度,中國現在很穩定,我也放心。”
基辛格說,“你看起來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國的發展中仍會發揮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過去所起的作用一樣。你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你是做的比說的多的少數幾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后來,基辛格在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一次會談中,在談到21世紀領導人素質時,特別贊譽鄧小平說,“鄧小平是中國推行改革的領袖。他著手共產黨領袖從未搞過的改革,解放了農村經濟,把糧食進口國變成了糧食富余國。他作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許共產黨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將經濟改革搞下去。”
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
在會談中,中曾根問及鄧小平的個人經歷。鄧小平說,“談到我的個人經歷,你在毛主席紀念堂的展覽室里看到的那張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時只有19歲。我自從18歲加入革命隊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沒有任何別的考慮,經歷也是艱難的就是了。我1927年從蘇聯回國,年底就當中共中央秘書長,23歲,談不上能力、談不上知識,但也可以干下去。25歲領導了廣西的百色起義,建立了紅七軍。從那時開始干軍事這一行,一直到解放戰爭結束。建國以后我的情況你們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
中曾根又問鄧小平,一生中覺得最高興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鄧小平回答說,“在我一生中,最高興是解放戰爭的三年。那時我們的裝備很差,卻都在打勝仗,這些勝利是在以弱對強、以少勝多的情況下取得的。建國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干部,而是領導干部,從1956年起我就當總書記。我一生最痛苦的當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其實即使在那個處境,也總相信問題是能夠解決的。前幾年外國朋友問我為什么能度過那個時期,我說沒有別的,就是樂觀主義。”
應中曾根要求,鄧小平介紹了有關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設想。他說,“我們越來越感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但現在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我們設想,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朝著下述三個目標進行。這就是:第一,始終保持黨和國家的活力,這個目標不是三五年就能夠實現的,能在15年內實現就好了。第二,要克服官僚主義和提高工作效率,我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這是中國的特點,不能放棄。但是黨也要善于領導。第三,要調動基層和人民的積極性,努力實現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決這個問題。”


當中曾根首相問到馬列主義是否仍然是中國的理論基礎時,鄧小平指出,“馬克思主義要發展。我們從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提出中國的政策,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夠取得勝利。現在我們仍然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里有繼承的部分,也有發展的部分,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真正的堅持了馬列主義。我們歷來主張世界各國共產黨根據自己的特點去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離開自己國家的實際談馬克思主義,沒有意義。所以我們認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沒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們也不贊成搞什么“大家庭”,獨立自主才真正體現了馬克思主義。”
中曾根首相還問起鄧小平從事革命工作的經驗,鄧小平說,“根據我長期從事政治和軍事活動的經驗,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人的團結,再加上堅定的信念,我指的是共同的、萬眾一心的信念,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凝聚力;沒有這樣的信念,就沒有一切。”
會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主席金日成
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去四川訪問途中,雙方有了更多機會交流看法。鄧小平著重闡述了一個思想:一心一意搞建設。
他談道:“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難,怎么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四人幫’叫嚷要搞‘窮社會主義’、‘窮共產主義’,胡說共產主義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簡直是荒謬之極!我們說,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在開始的一段很長時間內生產力水平不如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完全消滅貧窮。所以,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滅貧窮,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則,社會主義怎么能戰勝資本主義?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三十多年,截至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這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因此,我強調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決了這個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從這以后的實踐看,這條路線是對的,全國局面大不相同了。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我們打開了一條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新路。”
會見聯邦德國總理施密特
施密特在他的回憶錄《偉人與大國》中,詳細描述了他訪華期間與鄧小平會晤的情形,他寫道:“幾乎是我訪問毛澤東十年以后,1984年9月~10月,我第二次來到中國。這次,鄧小平以回憶我們幾年前的談話作為開始會談的引子。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說:‘你當時不同意我們對形勢的估計,你是對的。’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
施密特強調:“在所有的談話中,包括在首都以外的私下談話中,1984年使我們幾乎明顯地感覺到,中國每個人把改善生活狀況的希望寄托于誰呢?第一位是鄧小平,第二位是鄧小平,第三位還是鄧小平。他自己不搞個人崇拜,他大概鄙視個人崇拜。他也不需要為貫徹其政策而推行個人崇拜,因為他是深得人心的,所有的期望都凝聚在他身上。”
當有人問施密特誰是當今最重要的政治家時,他說,“中國的鄧小平在他眼中是‘最成功的政治家’。這是因為在‘四人幫’造成的動蕩之后,鄧小平把10億中國人的龐大隊伍引導到速度并不慢的改革之路上,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社會主義共和國總統胡薩克
鄧小平與胡薩克總統會見中談到毛澤東時說:“從1921年建黨到1957年,三十六年內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領導我們取得了革命勝利。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不能丟掉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就是否定中國革命的大部分歷史。當然,毛澤東同任何人一樣,也有他的缺點和錯誤。特別是他的晚年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他錯誤地分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堅持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受到了損失。”

雙方談話中,鄧小平特別提到《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這個決議就是公正地、科學地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來總結黨的歷史,評價毛澤東同志的。他指出,“對于毛澤東同志的晚年錯誤,不可過于追究個人責任,而應分析錯誤的復雜歷史背景。毛澤東同志個人當然要對他的晚年錯誤負主要責任,但我們決不可將錯誤完全歸咎于個人。”
胡薩克事后回憶說,“鄧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寬闊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主動承擔責任。他說,從1954年起,我就擔任黨中央秘書長、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1956年起擔任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是在領導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們黨犯的‘左’的錯誤,我也有份。不能把錯誤的責任完全推到毛澤東同志身上。”鄧小平在談話中還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將工作重點由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建設四個現代化為中心,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擁護。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較,‘文化大革命’的經歷變成了我們的財富。”
會見蘇共第一總書記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當政期間,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曾先后訪問蘇聯,赫魯曉夫也曾三次訪問北京。在此期間,赫魯曉夫與鄧小平曾有過多次接觸。隨著中蘇兩黨論戰全面展開,沖突日益升級,赫魯曉夫與鄧小平之間也開始了面對面的、針鋒相對的斗爭。
赫魯曉夫第一次與鄧小平打交道是在1956年處理匈牙利事件時,當時,他就領教過鄧小平的能力。兩年后,赫魯曉夫在向毛澤東談到他初次見到鄧小平時的情景時苦笑著說:“是啊,我也感覺到這個人很厲害,不好打交道。他觀察問題很敏銳。”
1960年9月,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受到的接待是高規格的,但這并不能緩解兩黨兩國間原則上的分歧以及隨之而來的激烈的爭論。
實際上,在鄧小平還沒有到達莫斯科之前,赫魯曉夫就親自在克里姆林宮主持了好幾次會議,與蘇聯的最高層領導研究與鄧小平談什么的問題。會上,赫魯曉夫不止一次地站起身來說:“我要與鄧小平親自談,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不過我不會怕他的。他是總書記,我還是第一書記嘛。”
雙方會談時,鄧小平顯得從容大度,坦坦蕩蕩,而赫魯曉夫卻始終在臉上保持著一種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
幾次敬酒剛剛過去,赫魯曉夫就開始了他的挑戰:
“鄧小平同志,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那個霍查老愛自搞一套,弄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是不團結,中國應該有個態度才對。”
他的這席話很顯然是從阿爾巴尼亞入手,影射攻擊中國共產黨。
鄧小平放下酒杯,直率但又是誠懇地對赫魯曉夫說:“赫魯曉夫同志,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個小黨,但他們能夠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你應該好好地尊重人家才對,不應該隨便向他們施加壓力。”
“可他們總和我們過不去。”
“在這一點上我們中國共產黨與你們有不同的看法。”
“這不僅僅是蘇共和中共之間的分歧問題呀!”赫魯曉夫脖子紅了,聲音也大了,“他們拿了我們的金子和糧食,可是反過來還罵我們,說我們是想控制他們,也太不像話了!”
“赫魯曉夫同志,”鄧小平語調不高,“我們一向認為援助是為了實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義務,而不是為了干涉和控制別人。再說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過你嘛!”

“這”赫魯曉夫一下子語塞了,漲紅著臉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鄧小平的這些話打中了他的要害。正是在他的旨意下,蘇聯剛剛單方面背信棄義地全面撕毀了對中國的援助合同,撤走了專家,中斷了幾百個正在建設中的大型項目,這種國際交往上罕見的不守信用,已經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赫魯曉夫不再談援助了,不再談阿爾巴尼亞的事了,直接把矛頭對準了面前的客人。
“鄧小平同志,你們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在斯大林的問題上態度那么前后不一致呢?”赫魯曉夫的粗暴性格現在又顯現出來了。
鄧小平顯然不買他的賬,很干脆地回答說:“不對!我們的態度是一貫的。”
“不!你們開始贊成我們,后來卻又在反對我們。”
“贊成什么?反對什么?這個原則問題是要說清楚的喲。反對搞個人迷信我們過去贊成,現在也贊成。在我們黨的八大上,對這個問題早有明確態度,劉少奇同志向你們的尤金大使講明了我們黨的態度,你問問米高揚同志,他到北京來時,我們對他講過沒有?”
鄧小平隨即把目光落在一旁的米高揚身上,這位蘇聯領導人有些不自然地與赫魯曉夫對視了一眼,忙調開了目光,端起杯子到別處敬酒去了。
赫魯曉夫氣得用手拍打了一下桌子:“對斯大林的問題,我們是不能讓步的,他是犯下了罪的!”
“不應這樣一概而論!赫魯曉夫同志,我們贊成反對搞個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績和錯誤怎樣看待,這不僅關系蘇聯國內,也關系到整個國際共運。斯大林的錯誤當然要批評,但成績也一定要肯定,我們反對的是全盤否定。”
“你知不知道?我們蘇共比任何人對個人迷信的體會都更深切,我們受害也最深。”
“個人迷信要批判,但對斯大林不能全盤否定。尤其不允許借反對個人迷信來攻擊其他的兄弟黨。”
鄧小平毫不含糊,把氣勢洶洶的赫魯曉夫弄得一下子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了。

在赫魯曉夫看來,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獨樹一幟”,將頭發剪得很短,這種發型在中國恰恰又是被稱為“小平頭”。然而,在歐洲,圣保羅早已肯定這種發式是“給上帝的榮耀”,象征著男性的力量與雄偉。
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卡達爾
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卡達爾時說:“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怎么搞,我們經過多年的思索,認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否則社會主義有什么優越性呢?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成果是屬于人民的。就中國來說,首先要擺脫貧困,我們的分配原則,是按勞分配,我們的目的是共同富裕;我們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我們要加快社會主義建設,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要改革,要尋找我們應該走的道路和步伐。改革涉及政治、經濟等所有領域。我們設想改革分三步走,現在第一步的目標已經達到,這增強了我們的信心。我黨的十三大將加快改革的步伐。不僅加快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也要提到日程上來。”
卡達爾向鄧小平介紹了匈牙利自60年代以來改革的情況。他說,“只有改革才能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我們堅持從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不搞教條。”
鄧小平對卡達爾的話表示贊同,強調說,“關鍵是,第一,我們都堅持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第二,我們都按自己的不同特點走自己的路,不能照搬外國模式,更不能丟掉自己的優越性。”卡達爾回憶這次談話時說,“鄧小平堅持他在八大會議上曾闡述過的觀點。他說,共產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都是我們的優越性。我們的黨政要分開,要有制約,但無論如何也是黨的領導。總之,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在談到這次訪問感想時,卡達爾說,“三十年之后我再次來到中國,為匈中兩國各個方面的關系都得到了恢復而感到由衷的高興。匈中兩國雖然幅員、人口等具體情況不同,但面臨的不少問題是相同的。改革是我們共同的事業,我們都在加速改革。中國對匈的改革感興趣,但我們的經驗有正反兩個方面。我們也高度評價中國改革的經驗。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不只是中國人民的事業,而是每一個擁護社會進步的人的基本利益所在。希望中國在社會主義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