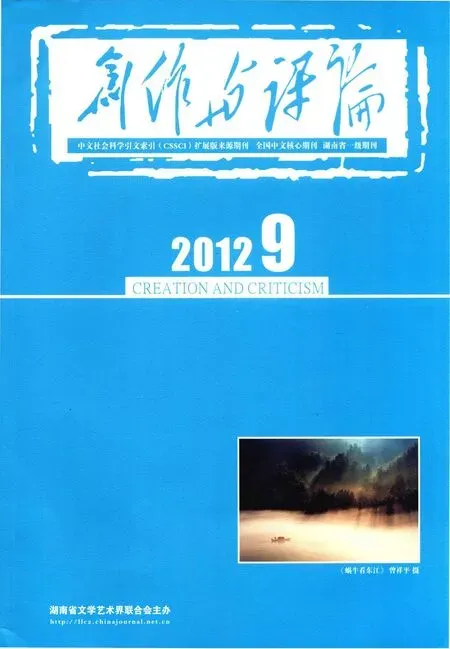來自土地的深沉歌吟——侗族詩人姚茂椿《我的胞衣地》組詩悟讀
■ 徐昌才
讀侗族詩人姚茂椿先生的《我的胞衣地》這組詩,我頭腦里立刻蹦出幾個詞語:“鄉里鄉親”、“土里土氣”、“原滋原味”、“地地道道”。這些詞語像腳下的土地一樣沉實厚重,像山里清泉一樣清明質樸,像山澗幽蘭一樣清雅脫俗,用來形容茂椿先生組詩《我的胞衣地》的風格特色真是恰如其分。我不認為來自土地的歌唱有多么低俗,來自生活的抒情有多么庸常,來自心靈的沉思有多么做作。相反,侗族詩人姚茂椿先生,從大山深處走出來,吮吸幽幽清泉長大,身上流淌著蒼山血脈,心里沉淀著民族魂魄,詩里充盈著濃濃鄉情,我在他不同時期的鄉土詩中讀到了這種味道和氣息,也在詩人2011年5月創作的《我的胞衣地》這組詩中強烈感受到了這些民族特色。茂椿對鄉土的刻骨眷戀,對親情的依依難舍,對古老生命的深情詠唱,對民族文化的崇高致敬,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過,這組《我的胞衣地》詩篇似乎有別于他的其他鄉土詠唱,字里行間,天頭地腳,洋溢著淡淡哀傷,滲透著縷縷憂思。詩人為一個民族日漸流失的習俗而嘆惋,為一個民族本色風范的流變而傷心,為一種精神的同俗退化而擔憂。茂椿用詩歌來傳承民族文化的精髓,用心血來澆灌民族精神的花朵,他的詠唱和嘆惋無異于一盆盆冷水,在這個物欲橫流、利欲沖天的時代,澆滅人們的狂熱躁動,送來深秋的習習清涼。
“胞衣地”是組詩的總標題,也是第一首詩《寨口的樹》歌詠的核心意象,詩人從一棵屹立在村口的古樹落筆來探索深邃而玄奧的民族文化。這棵樹千年如斯,蒼翠參天,見證了一個村寨的滄桑變遷,見證了一個個生命的來去無常。他以博大開闊的胸懷包容人們的激動、高興,他以枝繁葉茂的蒼翠接納嬰兒的呱呱墜地,他以莊嚴肅穆的姿態迎接牛犢的哞哞降生,他比村寨古老,他比老人長壽,甚至連村里的老人也說不清他有多大年紀,只能用合圍的姿式去丈量他悠久的歷史。他知天知地,知人知事,他知道每一條牛犢怎樣來到這個世界,他知道每一個嬰兒怎樣哭泣著開始他的人生,他知道春天哪一朵花最先開放,他知道秋天哪一株樹最早落葉,他知道村寨的角角落落、里里外外。但是,他“抿嘴不言 /一臉沉靜”,他“心事蔥蘢”卻“從未說漏過嘴”,他“從未挑明”人們的“疑惑和猜想”,他平靜地站在村寨路口,與風雨對話,與大地交流,與天空默會,蘊含大美而不言,隱寓萬千而不語,給人留下莊嚴邈遠、玄虛深奧的印象。不過,聰明的詩人靈光一閃,猛然頓悟,從這棵樹身上,他讀到了無以回報的感恩,他讀懂了流浪天涯的回歸。俗語道,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人走四方,魂歸故里。詩人坦白,這是每一個游子生命的唯一,這是每一個生命思想的歸宿。胞衣地,生我養我之地,鄉土鄉音之地,魂牽夢繞之地,我怎能割斷那份血濃于水的鄉情?
詩人用“胞衣地”一詞概括組詩情感內容,頗具生命感發力量,它會觸動人們的心靈,引發人們的諸多聯想。直白地講,“胞衣”是指一個生命誕生時的胎盤和胎膜,它與生命軀體血肉相連,與生俱來。“胞衣地”在侗族地區被人們用來指稱祖居地、出生地,暗含追終懷遠,反哺報恩之意,警示人們不忘本,不忘根,所謂“飲水不忘挖井人”,“前人栽樹,后人乘涼”之類的俗語,就包含了這類意思。茂椿在《寨口的樹》這首詩中就點明了這一點,不忘出生地,不忘鄉土情,不忘家園親,感恩父母,感恩生命,感恩自然,這是生命的“一些”,甚至“唯一”。詩人又用“胞衣地”作為組詩的總標題,依次寫到了能夠反映胞衣之情的古老侗民族的一些生活習俗、生存方式和生活信念,這些都是有形有態、有聲有色的侗族文化,這些文化構成了每一個侗族游子的精神家園。胞衣地對游子來說,就是一個充滿巨大吸引力的精神家園。
另外,此“胞衣”諧音彼“袍衣”,古老的《詩經·秦風·無衣》如此歌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衣,泛稱一切衣服。袍,長衣。行軍者日以當衣,夜以當被。就是今之披風,或名斗篷。“同袍”是友愛之辭。澤,指汗衣,內衣。裳,下衣。詩歌抒發將士們同甘共苦、并肩戰斗、保家衛國的豪情。“袍澤”、“袍衣”一詞由此誕生,寓含情同手足,血濃于水之意。讀到“胞衣地”是很容易想起這個“袍衣”之說來的。其實,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詩人對于故土家園、親人故舊的緬懷眷戀。情意真切、深厚,綿綿不盡。
《便橋》一詩虛實結合,形神兼備,是寫便橋,更是寫侗民;是寫歷史,更是指向未來;是抒寫信念,更是寫真生活。這些便橋是山民就地取材,削木建成。它們橫陳溪澗,越溝過坎,迎來送往山民無數,風吹雨淋日曬久遠,簡陋至極,默默無聞。但是,在侗民心中,在詩人心中,卻是“一道道堅實的彩虹”,照亮人們的雙眸,燦爛人們的心靈。橋有被山洪暴雨沖走的時候,但是古代侗民心中那個與人方便、行善積德的信念,卻代代傳承,生生不息。侗民深信善有善報,因果輪回,他們秉持良知和本性為人處世,行善積德,助人為樂,不求虛名,不圖利益,吃苦受累,無怨無悔。便橋的姿態就是他們勞作的身影,便橋的遭遇就是他們命運的寫照。人與橋,餐風飲露,堅守歲月,鑄就了一種鐵骨錚錚的大山風骨。詩人詠嘆:
“一根根長樹搭起便橋 /搖晃著 /我們當年的稚嫩/老人沉重的想法走過/我的心/戰戰兢兢”
面對便橋,詩人有一種站立橋上,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感覺。他心中翻涌復雜情思:年輕時的懵懂稚嫩,搖晃無知,年老時的風雨回首,滄桑感慨,勞動者的艱辛苦難,侗民心中永恒不變的善念,……凡此種種,包蘊其中。詩人“戰戰兢兢”,那是因為他站在連接過去與現在的便橋之上,感慨萬分;他站在連接現實與信仰的便橋之上,心懷憂思。每一次山洪過后,便橋就如雨后春筍遍地生長;每一次災難之后,善念便如星星草芽綠遍山野。便橋是一道風景,滄桑了歲月,溫暖了人心。
侗族是一個能歌善舞的民族,俗話說得好,“飯養身,歌養心”,侗族人民常常借助歌聲來表達他們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趕坳對歌就是一種深為侗族民眾喜聞樂見的習俗活動,詩人對此有鮮活的記憶和生動的描寫:
“蔥綠鮮活的情節/在眼前不時晃蕩/樹上滴落的歌聲 在山坳 /像放光的珍珠 /一些是揪心的往事/一些是攝魂的情歌 /難忘的面孔有說有笑 /逐一出現”
坳會時節,盛裝男女云集山坳,對歌青春愛戀,對歌天地自然,對歌家長里短,對歌鄰里鄉親,歌聲婉轉悅耳動聽,如黃鶯“間關鶯語花底滑”,如山泉“更添波浪向人間”,歌聲回蕩山坳,響徹藍天白云,歌聲喚醒塵封記憶,歌聲復活生動細節,讀著詩句,我們不知不覺和詩人一道沉浸到那些美妙或憂傷的境界當中去。詩人的重點不在于放肆詠贊歌坳的美好,而是憂慮這種民俗傳統的悄然流失。山寨男孩,脫去了民俗,找工作去了;坳旁的美女,丟下了歌聲,沿海打工去了。歌坳變得“夢少人稀”,蕭條慘淡;詩人心中的“珍珠”撒落一地。一地的“珍珠”就是一地的淚水,一地的“珍珠”就是一地的憂傷。詩人知道,社會在發展,文明在演進,古老的傳統日益受到現代文明的擠壓,人們也不得不為更好的生活而奔走他鄉,遠離了故土,遠離了歌坳。這就是現實,很殘酷,亦很無奈。詩人通過“刺目的憂傷”傳達了自己的嘆息和隱痛。讀到此處,筆者腦海里突然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一個詩人站在人去山空的坳上,若有所失地尋覓,眼含憂郁地思考,他在尋找古老的歌謠,他在尋找遺失的記憶,大山不語,天地不語,但是他耳畔、心中卻響徹經久不息的歌聲。
同樣的隱憂和痛楚在《雀坳》一詩中也表現得很明顯。侗鄉山民有趕坳斗畫眉的習俗,大家提籠架鳥,湊到一起,比試各自精心喂養、調教的畫眉哪個摸樣漂亮,哪個聲音動聽,哪個靈泛可人,哪個會解人意,贏者中大獎一般狂喜,輸者心服口服,怏怏不樂。這種活動很有看頭,很迷人,詩人一句“一聲哦嗬/迷倒無數/純潔的心靈”足以活畫現場的精彩。可是,世易時移,人心不古,傳統不傳,“斗畫眉”如今已經演變成了一種名利賭斗,巧舌變為厲嘴,生死伴隨打斗,場景血腥不堪,沒有山花綻放的詩意,失去了畫眉歌唱的歡樂。而且,那些經過層層比試,屢屢打斗之后勝出的“冠軍”畫眉,被人們帶進城去,去一個更大的舞臺打斗,去一個“陌生的漩渦”拼搏。這種搏殺與美無關,與歌唱無關,與民俗無關,卻與利欲密切相關。顯然,詩人對于這種演變,準確地說是墮落,深感痛心,深表憂慮。人心不古,趨利逐臭,同流合俗,喪失了自然與和諧,喪失了純樸與率真。原來那種養鳥愛鳥,癡心把玩的勁頭沒有了,原來那種和樂和睦,談笑風生的關系不見了,原來那種悠哉閑哉,滋潤生活的味道全沒了。一種習俗的變異,其實折射出一種世俗、一種人心的變異,這種退化與墮落,詩人是不能接受的。
古老的侗族在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信念和神靈崇拜。娛人娛神,消災祈福的巫儺表演就是深受侗民喜歡的古老戲劇之一。每逢節日,山民們都要戴上猙獰怪異的巫儺面具,穿上五彩繽紛的民族傳統服裝,利用簡簡單單的農耕道具,熱熱鬧鬧,開心演唱,手舞足蹈,得意忘形。觀者如云,絡繹不絕,場面火爆,氣氛熱烈。如今這個名為“咚咚推”的儺戲,仍在侗族地區長演不衰,并已進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名錄。筆者家鄉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縣貢溪鄉四路村天井寨,就是侗族北部地區著名的儺戲之鄉。儺戲表演,遠近聞名,傳揚四海。可以說,“儺戲”像侗族大歌一樣成為了侗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茂椿對于這種古老藝術的感受和思考,洞穿歷史,引領未來。他惋惜,史無前例的文化浩劫粉碎了流傳久遠的“咚咚推”;他贊嘆,向往幸福的先民歷經劫難,“沒有屈服”;他憂憤,這方土地“往昔的山水/妖怪橫行”,平安空白。他更站在歷史與未來的交匯視角中反思:一方面,“我們樸拙的展翅/將掙脫蒙昧歲月/漫長的影子”,我們走出了蒙昧和稚嫩,我們掙脫了陰影和黑暗,我們變得成熟而理性;另一方面,“鑼鼓如夢似幻/擊醒孤獨 渴望/無盡的黃牛 磅礡萬里 /讓心愿和幸運 蹄飛/塵起”,對于未來,我們有美好的憧憬和熱烈的追求,這個民族,踏夢而行,劫后求生,何等雄強,何等執著。一次次巫儺演出,一聲聲“咚咚推”響,見證著這個民族難以磨滅的記憶和永恒不變的精神。當然,詩人對于歷史,對于儺戲的沉浮不定的命運,充滿了憂思,充滿了感慨。
《草標》一詩則從社會秩序的維護,道德力量的滲透這個角度來思考侗族的歷史和現實。草標,顧名思義,是一些用柴草偏扎而成的標志符號,根據功能不同,又可分為路標、井標、界標、柴標等類別,路標指路,井標記水,界標劃界,柴標分柴,無不職責分明,秩序井然。這個民族沒有那么多繁瑣的法規制度,沒有那么多抽象的空洞說教,只憑借這些簡簡單單的符號,就將做人做事、交結往來的道德觀念輸入人心。而且,人人遵從,權威無比。可是,如此地道、古老而淳樸的社會規范如今卻“紛紛倒下”,蕩然無存。信任失血,信念坍蹋,人心不古,詩人“頻頻回望”。他渴望“草葉的懷想”“漫山鮮活”,他渴望蒼白的現實一去不返。但是,他的回望能變為現實嗎?許多空白,也是許多蒼白,給人們留下一個個沉重而傷感的問號。
相對于《草標》而言,《秋后的稻草堆》則顯得明快一些,輕松一些。筆者生于侗鄉,長于侗鄉,對秋天收割之后的稻草堆可是情有獨鐘,記憶猶新。秋收之后,人們將稻草捆扎成堆,形成一個巨大的圓柱草堆,以便不時之需。喂牛、墊豬圈、鋪床、織草鞋等等,都用得上稻草。對于小孩來講,那可就是溫暖的窩,三五成群的玩伴可以在那兒打滾,捉迷藏,做游戲,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家人呵斥,那種生活非常自由快樂,非常貼近村莊和人性。對于稻草堆和稻草堆旁邊的生活,詩人有自己的感悟。孩子開心摔打,苦練翅膀,從這里走出大山;老牛大口咀嚼,嚼出清香,嚼出力量,從這里積蓄體能;少年,揮汗如雨,辛勤勞動,從這里出發,長高長大。是啊,侗民的后代都是在稻草堆旁邊度過寶貴的童年時光,都是在天真戲謔中展開自己的夢想,及至長大告別稻草堆,告別自己的家鄉,仍然是依依難舍,念念不忘。詩人寫這種人生的告別,如此動情,又如此深沉:
“你像金黃的夢/綴在小路的枝頭 /回望寨口/還金燦燦的告別/揮手/我們遠離家園 /不是飄香的稻穗/在山外/是一群沉甸甸的思想”
揮一揮手,不帶走一片故鄉的云彩,但是早已把故鄉所有的云彩貯藏心間;不再聞到兒時稻穗的飄香四溢,卻早已經如癡如醉地思念和緬懷。鄉愁啊,就是這樣一種感情,你在故鄉的時候,故鄉就是你的一切,你離開故鄉之后,一切都是故鄉。李白說“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人啊,怎么走得出故鄉的懷抱呢?詩人和萬千游子一樣,游走都市他鄉,但是,心卻藏在草堆里,留在記憶的深處。那一叢叢稻草,分明就是詩人蔥籠的心情;那一片片金黃,分明就是鮮亮的鄉愁。鄉愁跨越時空,風塵仆仆,撲面而來,構成一道永恒而凄美的風景。
對于故鄉而言,茂椿是個游吟詩人;對于城市而言,茂椿是位鄉村守望者。這組《我的胞衣地》從各個層面,不同角度,多維演繹了詩人的鄉土情懷和文化憂思。我從茂椿先生的博客上讀到詩人的組詩,對于“湘椿”大樹圖像印象至深。老樹盤根,軀干粗壯,枝繁葉茂,生機勃勃。椿者,古樹也。《莊子》記載,“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拔地通天,遮天蔽日,穿越時空,萬古蒼翠,何等磅礴,何等神奇!《逍遙游》還借惠子與莊子的一番對話,給世人演繹了一段深刻的人生哲理。惠子對莊子說:“我有棵大樹,大家都把它叫做‘樗’(椿樹),它的主干滿身瘡痍,不能符合墨線取直的要求,它的小枝曲曲扭扭,也不能符合圓規、角尺取材的標準,即便讓它長在大路上,木匠也不會看它一眼。如今您的言論,也像這棵樹一樣,大而無用,所以大家不采納您的話。”莊子說:“難道您沒看見那野貓和黃鼠狼嗎?它們躬著身子躲起來,等待著那些出游的小動物。它們東竄西跳,不管高低深淺,結果往往中了獵人的機關,死在獵網之中。再說那牦牛,它大得如同天邊的云,這可說是夠大的了,然而就不能捕捉老鼠。如果您有棵大樹,為它無用而發愁,那為何不把它種在一無所有的地方,種在那種浩茫寂然郊野,悠悠然自得地在它周圍徘徊?它就不會喪生于刀斧之下,沒有東西可傷害它,又哪里用得著為它沒有用處而苦惱困惑呢?”莊子真是睿智,深刻,不過筆者重復這番經典對話,意思并不在于有用無用之辯,筆者想指出的是,詩人茂椿先生就像一棵長在侗鄉沃土上的椿樹,枝繁葉茂,生機勃勃,根深深扎在土地里,每一秒都在吮吸土地的營養,葉綻放在枝頭上,每一片都散發出故土的芬芳。胞衣之地有廣闊的天地,有最肥沃的營養,茂椿有足夠的才華,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居官而不自傲,為文而不張顯,扎實耕耘,佳作不斷,筆者堅信,茂椿會走得更遠,走得更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