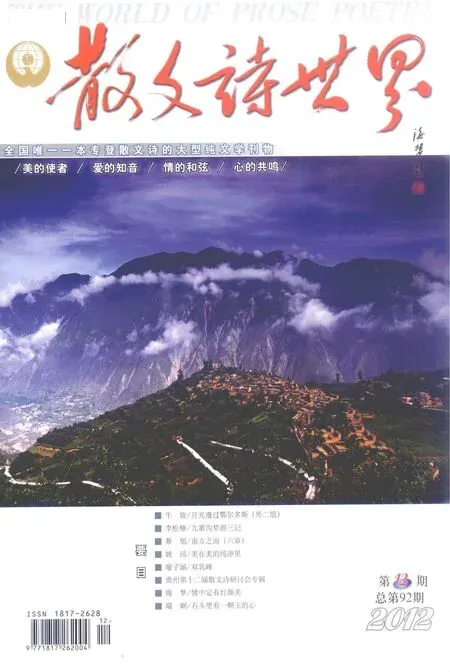江界河大橋(外二章)
楊昌瑞
我想駕一片云,攀登于江界河的懸崖絕壁,找尋那位在云彩上修路的人。
思想的跟蹤器一直閃著信號燈。從橋墩到橋面;從橋頭到橋尾;從河底到魚鱗,在崇山峻嶺里,在萬丈溝壑中,在滔滔烏江上,他的腳印重疊了又重疊。
就在一片樹葉拽著生命的句號謝幕時,修路人已去,衣衫飄然,如仙。他的風骨鐫刻在葉脈之上。在火花四濺的石頭上,在汗水揮灑的露尖,在刀耕火種的歲月里他的影子凝成雄健的江界河大橋。
我和風攜手,站在13.4米寬度的橋面,如一個舞者登上夢寐的舞臺。柔美的風最終決定以身相許,于是橋站成男人的姿勢,風躺在他銅色胸肌的懷里,膨脹對未來的希望。
橋的根深深扎在堅硬的石頭上,等待著歷史的扉頁一頁頁翻閱,就像雄健的男人張開雙臂等待愛流入懷。
山在我的腳下行走,一山一山描著陽光的色彩,眼睛走過的地方,畫幅都貼著貨真價實的標簽。263米的高度被陽光鍍成金黃的肌體,在云彩間,橋若隱若現。
461米的長度,不僅僅穿越他體下的河。咆哮的浪花在硬邦邦的石頭上磨成鋒利的寶劍,同樣擋不住他前行的腳步。他舉著天下第一懸臂大跨度桁式組合橋的頭銜,飛馳在世界的每個角落,把所有的驚嘆都鑲嵌自己的體內,在青山綠水間,一躍而起,如虹。
江界河大橋是一個大山的男人,用如鉤的手緊緊抓住隔河相望的兩座大山。在風風雨雨的日子里,在嚴寒酷暑里他依然挺直胸膛堅守,只為人們能從他肩上渡河。
鮮花和掌聲如雷,在人的心里響徹一生。
其實他什么也不要,他只是人的腳步的延伸。
甕安城之夜
行走在甕水長歌之都,踩著滿地星光。我在現實中體驗了一次夢游。
我和這城市最親密的相擁發生在午夜時分,就算我還有些清醒,我已經跌落在她懷里。
月光和燈光在追逐嬉戲,從渡江廣場到甕安河畔,她們揚起濃烈的油彩,潑向你,潑向我,潑向他。我的身上已經灑滿了絢麗的色彩,只要我輕輕一抖,五彩繽紛會滴落一地。
站在這高樓林立間,我仿佛踩著一個繁華大都市的影子。
我是第一次被誘惑進這座城池,沒有理由不把自己交給她,讓她在我身上自由宣泄。她滾燙的身體,把我推向火尖之上燃燒,連同我的五臟六腑一起燃燒!燃燒!燃燒!我想,就算我融化了,也要將狂熱從骨頭里涌出。
霓紅燈在麥克風里推杯換盞。燈光和陶瓷碰杯,清脆的聲音從這個城市傳到另一個城市。聲音如叮咚跳躍的山泉,從林間穿過,從透明的鵝卵中穿過,在黔山深處,過濾成一絲琴弦。
一杯啤酒,泡沫傾泄而出,在玻璃的光中一枝艷麗的花在悄然綻放!當臉被花瓣的色彩親吻時,舉著搖晃酒杯,為你燦爛的容顏喝醉。
扶著我回賓館的街道,一直在喧囂和奔跑。
這個城市注定要豐滿,一些欲望還不斷在肌膚的下面孕育。
明天,城市一陣疼痛后,一個嶄新的未來在灼熱的土地上豐滿隆起。
注:《甕水長歌》是循著甕安歷史長河中的一部戲,展現的是甕安歷史。
和海夢先生握手
海夢先生是一位尋夢者,在他的名字里,夢有了寬度。
八十歲的老人,如一個孩童行走在詩行里,每一個腳印都那么真切快樂。
我仰視他,仰視他對詩的種植、培育和護理。在我的仰視里沒有名利存活的土壤,我只想把肥沃的土壤放在散文詩里,讓夢發芽。
大海的夢正在綻放。浪花盛開為他獻禮。
他勤勞的身影耕耘在詩行里,八十頁詩行,八十個掌聲,八十聲喝彩。
《散文詩世界》里,他為八十個春天買單,卻存入了一個沉甸甸的秋天。
走進他,與他握手,與每一個動情的漢字握手。
在貴州省第十二屆散文詩研討會上,海夢先生的手圓了我的夢。
不,我不是握的他的手,我是握住一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