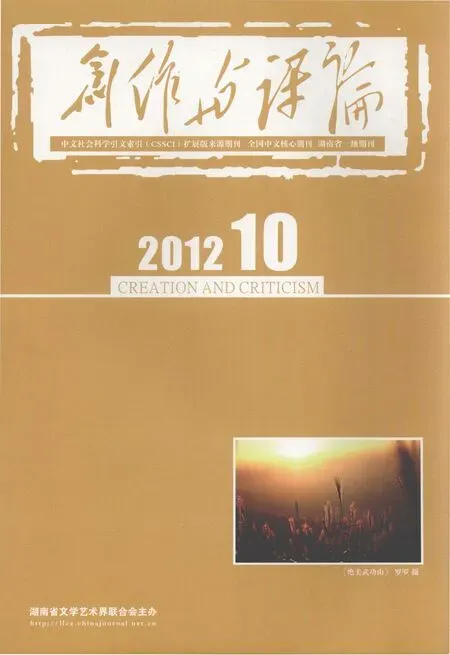太多的不安和喜悅
■ 張煒
我從很早就開(kāi)始寫作,摯愛(ài)文學(xué),不可救藥和沒(méi)有來(lái)由地愛(ài)著,愛(ài)得很深。以前我也說(shuō)受過(guò)哪些影響走上了文學(xué)之路等,但知道那是找個(gè)他人可以理解的話頭而已,實(shí)際上更多的是沒(méi)有來(lái)由地愛(ài)著。從1975年就開(kāi)始發(fā)表作品,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寫了快四十年,累計(jì)發(fā)表字?jǐn)?shù)到了一千三百多萬(wàn)字,還不算練筆的幾百萬(wàn)字。
仍然由于特別愛(ài)文學(xué),對(duì)與之關(guān)連一起的事物就要求格外高、格外嚴(yán),有放不下的牽掛。我自己缺點(diǎn)和弱點(diǎn)很多,卻對(duì)人性,社會(huì),人與人的關(guān)系,自然環(huán)境,道德?tīng)顩r,要求很高,甚至還有點(diǎn)苛刻。對(duì)黑暗的東西不能容忍。我在許多時(shí)候是憂慮和不滿的,有時(shí)竟然非常憤怒。情緒激烈時(shí),表達(dá)上常常是沖動(dòng)的。同時(shí)也深深地?zé)釔?ài)著一些事物,對(duì)自然,對(duì)友誼,對(duì)各種美,有一種說(shuō)不出來(lái)的柔情。因?yàn)橥甑钠D辛,我特別不會(huì)忘記并且一直感激著來(lái)自他人的善意和幫助。
最近因?yàn)橐庉嬏摌?gòu)作品之外的文字,這才仔細(xì)統(tǒng)計(jì)了一下,發(fā)現(xiàn)竟然積下了四百多萬(wàn)字的散文及其他言說(shuō)類文字。這個(gè)字?jǐn)?shù)太大了一些,讓我覺(jué)得十分突兀甚至不安。發(fā)現(xiàn)自己說(shuō)得太多,這并不好。從一般規(guī)律上看,一個(gè)從事虛構(gòu)的作家,最聰明的做法是少說(shuō)一點(diǎn),因?yàn)檎f(shuō)得多了,一方面會(huì)莫名地得罪人,另一方面自己作品可詮釋的余地就越來(lái)越少了,整個(gè)作家也就變“小”了。形象總是大的、多解的,作家自己說(shuō)多了,就會(huì)局限解釋的空間。
那會(huì)兒一度想改變這個(gè)狀況,就是以后盡可能地少寫散文。可是心里又有太多的不安、喜悅和憤怒,只想看到什么趕緊提醒一下。我知道這樣做不是為了一己私利,而是責(zé)任感的驅(qū)使。當(dāng)然還要想到生活和寫作的意義,并且知道自己作為一個(gè)寫作者,并不僅僅是為了寫虛構(gòu)作品。結(jié)果后來(lái)還是決定讓一切自然而然地下去吧,盡自己之力,能做多少做多少,真實(shí)地一路走去。面對(duì)這個(gè)危險(xiǎn)的世界發(fā)出自己的聲音,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yàn)槲揖褪沁@樣的人,不必因?yàn)榉氖裁次膶W(xué)策略而硬性地改變自己。
說(shuō)到運(yùn)用文學(xué)策略,一個(gè)作家還是小作了。一個(gè)人寫了那么多,苦心經(jīng)營(yíng)如此,又大多來(lái)自艱辛的底層,怎樣對(duì)待社會(huì)、讀者,怎樣對(duì)待評(píng)論家、漢學(xué)家,怎樣對(duì)待外國(guó)人,心里都該是十分明白和熟練的。做好這一切并無(wú)更大的難度,起碼比用心寫好幾部長(zhǎng)篇容易得多。這一類聰明和機(jī)智,差不多人人都不缺乏。但這樣做就要遷就許多,違心許多,天長(zhǎng)日久必會(huì)造成內(nèi)傷,說(shuō)到底這與從小對(duì)文學(xué)的深愛(ài)是相抵觸的。
人的文學(xué)志向是不同的。如果努力用寫作來(lái)?yè)Q取一些世俗利益,比如賺錢、獲取地位、獲得更多贊譽(yù)和獎(jiǎng)項(xiàng),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是什么壞事。但比較起來(lái),還有另一些目標(biāo)放在那里。如果是一個(gè)基督教作家,要他來(lái)回答為什么寫作,他可能回答是“為了榮耀上帝”。我們大多沒(méi)有這樣的信仰,但我們卻會(huì)明白這回答中包含了怎樣的深意,是很高的志向和境界,是很了不起的要求。
那么我是怎樣的?總結(jié)一下,知道隨著年齡的增長(zhǎng),名利心在一點(diǎn)點(diǎn)淡去。回憶刻苦寫作的這些年,許多時(shí)候只是受沒(méi)有來(lái)由的一種深愛(ài)的力量支配著,寫個(gè)不停。做文字工作的都知道,將一篇幾百字的東西在紙上落實(shí)好,讓其充分表達(dá)自己的意思,尚且還要費(fèi)不少的工夫——如果這樣較真地寫上千萬(wàn)字,不能不說(shuō)是一種辛苦。可是這種辛苦也有更多的欣悅在。人在生活中,如果不是一個(gè)傻子,只要活到了四十多歲,就一定會(huì)深刻地感受到絕望。所以也就是這種沒(méi)有間斷的寫作,這種勞動(dòng),安慰了我激勵(lì)了我,讓心靈維持在較好的狀態(tài),能夠向上提升而不是往下沉淪。就因?yàn)椴煌5厮妓骱烷喿x,讓我知道了人世間還有這樣一些不同的人生、不同的情懷。我必須說(shuō),寫作無(wú)論如何令自己不滿意,還是讓我變得比過(guò)去善良了,比過(guò)去好了。文學(xué)既然對(duì)我有了這樣的意義,就該感激文學(xué),它是多么重要。
除了文學(xué)使自己成長(zhǎng)、幫助了自己,還覺(jué)得留下的這些文字雖然謬誤不少,但其中的多數(shù)還是有助于這個(gè)世界的,就是說(shuō)它們有助于這個(gè)世界道德的提高、人的素質(zhì)的提高。它這方面的作用哪怕只有一點(diǎn)點(diǎn),但因?yàn)槭橇夹缘模砸策€是有點(diǎn)意義的。
從如上來(lái)看,從主觀和客觀兩個(gè)方面看,文學(xué)之于我既是這樣,也算很好地走向了、實(shí)踐了一種志向。可見(jiàn)這并不需要文學(xué)策略,而只需依照從一開(kāi)始就發(fā)生的愛(ài)的初衷走下去就行,是很自然的一個(gè)過(guò)程。我的成績(jī)微不足道,但這個(gè)過(guò)程,對(duì)我的意義不可謂不大。
愛(ài)文學(xué)是很重要的,一個(gè)“愛(ài)”字可以解決很多棘手的問(wèn)題。現(xiàn)在看來(lái),文學(xué)人士偶爾出現(xiàn)的一些不好的念頭,比如機(jī)會(huì)主義傾向、虛榮心,都是不愛(ài)造成的。現(xiàn)在一些刊物的問(wèn)題、寫作的問(wèn)題、出版的問(wèn)題,評(píng)論的問(wèn)題,常常出現(xiàn)一些讓人大不如意的狀況,也大都是不愛(ài)造成的。如果真正愛(ài)、深深地愛(ài),也許整個(gè)情形就會(huì)好得多。
隨著寫作歷史的延長(zhǎng),年齡的增長(zhǎng),會(huì)變得比過(guò)去寬容。我漸漸知道不寬容的主因,就是太以自己為中心了,不愿離開(kāi)自己的經(jīng)驗(yàn)去理解他人外物。其實(shí)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或許比人和動(dòng)物的差異還要大,只是讓差不多的眉眼衣著和語(yǔ)言方式給掩蓋了罷了。人太多了,人群當(dāng)中真的會(huì)有各種不同、甚至充滿奇跡。要理解一個(gè)人,就得知道他的出身、絕然不同的經(jīng)歷,包括一些生活細(xì)節(jié),甚至是神秘血緣等。我愿意努力去體會(huì)別人的行為,找到自己的方向。寬容的結(jié)果當(dāng)然不是變得更圓滑、更沒(méi)有原則,而是變得更加逼近真實(shí),更加有立場(chǎng)。
能夠始終保持對(duì)文學(xué)熱愛(ài)的初衷是很重要的。這樣才會(huì)樸素,才會(huì)找到真實(shí)。一個(gè)人相信永恒的真理,相信這種尋找的意義,就是信仰。這個(gè)過(guò)程是緩慢和持續(xù)的、不能間斷的,這看上去就必然有些笨拙。我以前引用過(guò)他人的一句比喻:“大動(dòng)物都有一副平靜的外表”。這樣說(shuō),絲毫也不敢隱喻自己是一個(gè)“大動(dòng)物”,而只是表明了對(duì)大動(dòng)物的力量、自信和專注的喜愛(ài)。是的,只有黃鼬一類小動(dòng)物才那么機(jī)靈跳躍,窺視多變。在這方面,大動(dòng)物是做不來(lái)的。
已經(jīng)寫了近四十年,二十七歲動(dòng)手寫《古船》,后來(lái)被要求反復(fù)改動(dòng),出版時(shí)已是兩年以后了。三十左右歲還寫了《九月寓言》,以及大批中短篇小說(shuō)和散文。現(xiàn)在共寫了十九部長(zhǎng)篇、幾十部中篇和一百多部短篇。可是今天卻不見(jiàn)得比當(dāng)年寫得更好——寫作就是這樣,一邊前進(jìn)一邊后退,獲得就是丟失。對(duì)一個(gè)創(chuàng)作者來(lái)說(shuō),并不一定是越寫越好。但僅就工藝和技術(shù)層面來(lái)說(shuō),或許應(yīng)該有起碼的清醒。記得畫家畢加索說(shuō)過(guò),他十幾歲的時(shí)候就已經(jīng)達(dá)到了拉斐爾的能力,繪畫技藝十分成熟,可惜后來(lái)一輩子努力做的,就是怎樣才能畫得像小孩子一樣。
這樣說(shuō),當(dāng)然也不會(huì)被誤解成狂傲到自比畢加索的地步,這兒不過(guò)是說(shuō)贊同這樣的看法,即藝術(shù)技法和工藝層面的東西從來(lái)都不是最難的,在藝術(shù)這里,一直有比技藝重要得多的東西,是它決定一個(gè)人將來(lái)能走多遠(yuǎn)。
《你在高原》寫了二十二年,有四五百萬(wàn)字——它最初長(zhǎng)達(dá)五百多萬(wàn)字,應(yīng)出版要求縮為今天的長(zhǎng)度。但長(zhǎng)度并不說(shuō)明更多,好才是目的。不過(guò)它畢竟呈現(xiàn)了相對(duì)長(zhǎng)的一段生命河流。時(shí)間給予的一些認(rèn)識(shí),難以靠其他方法比如能力之類可以彌補(bǔ)。出版后有人擔(dān)心它太長(zhǎng)無(wú)法閱讀,只是樸素的擔(dān)心,總歸不是文學(xué)爭(zhēng)論。說(shuō)到閱讀和理解,以前的八部長(zhǎng)篇不太長(zhǎng),都是在心里煎煮多年、用鋼筆一個(gè)字一個(gè)字刻在稿紙上的,有點(diǎn)像刻鋼版的感覺(jué)。那些長(zhǎng)篇讓我傾盡心力。可是閱讀它們的時(shí)候,難道會(huì)更容易嗎?事實(shí)并非如此。那些作品對(duì)我的重要性來(lái)說(shuō),像《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僅就個(gè)人所能達(dá)到的完美度和深邃度而言,絲毫不比《你在高原》差。所以文學(xué)作品對(duì)讀者和作者全都一樣,它從來(lái)不是一個(gè)長(zhǎng)度問(wèn)題,而是一個(gè)心靈問(wèn)題。
今后會(huì)一直緩慢而有耐心地寫下去。無(wú)論如何,這樣寫到最后,或許會(huì)擁有自己的一個(gè)文學(xué)世界。也只有這樣,朋友們才會(huì)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