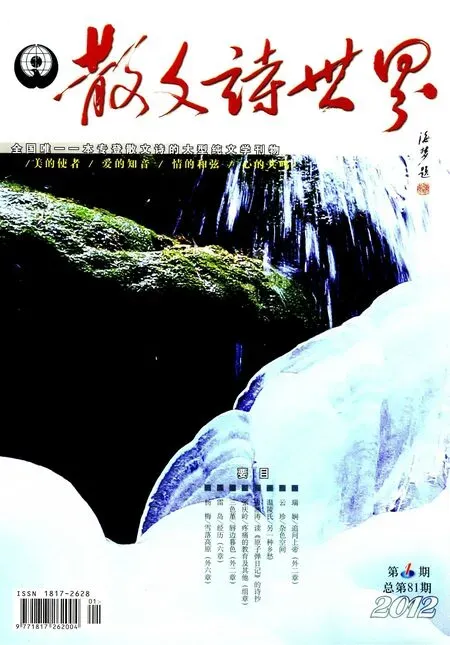一個可能世界的建構:蔓琳散文詩背后的敘事藝術
孫 婧
面對蔓琳的詩作,我發覺這是我評論的一個難題。這個內心寧靜而又思想跳躍的作家,不僅有著對人生存的感性的自知還有著一種深刻的理性自覺。在一些學者高呼后現代救救散文詩的聲音里,我們很欣喜的看到還有這樣一群修正病態、建構理想的散文詩人,蔓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在蔓琳的詩作中有著對現實中自我身份的追尋和對跨越現實的意識的補救;她既涵蓋著散文內容的豐富又包含有詩的韻味;她的敘事在捕捉著現實世界的生命軌跡,又在這種詩意的言說中刻畫我們在世界的感知經驗。以其散文詩集《穿過河流的月光》為例,這種對于個體身份的捕捉及其對于可能世界 (Possible worlds)的建構,就為我們提供了理論研究的有效實踐工具。《被禁錮的自由》《美麗被裝進籠子》講述的是女性個體在我們的生存世界即真實世界( Real world)所面臨生存的壓力以及由此而來個人選擇的困惑,她們在物質欲望中身份的迷失,精神與肉體的分離。
“給我一個快樂的理由,給我一次痛苦的借口,在你們的幸福中,我看到跪下去的卑微。這世界瘋了,上天寵壞了無心的女人,而我,扶在思想的背脊上哭泣。”(《被禁錮的自由》)
作家力圖傾力表達這種女性生活本身的復雜壓抑時,穿越了寫作者自身的意識層面和其作為女性個體的無意識層面,確定虛構的可能世界虛構人物是以真實的方式感知世界,從而跨越現實的局限性與被遮蔽性的思想性。
在《酒吧的夜晚》中,聲音、理想和現實,友情和金錢、靈魂肉體,包括那看不見的一聲嘆息,大量的細節表述,呈現一個酒吧夜晚的事件。“用一首詩,結束這個虛無的蒼白!”一句,讓我們看到作家內心的冷靜和對精神與肉體沖撞交錯的思考。散文詩集《穿過河流的月光》中“茶關”、“約會海水”、“攜著愛飛翔”“夢中的牽牛花”等等,在這些詩作里,是對現實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的一種構建,其實更多的是表述一個事件,事件以一幅畫卷呈現,填充了讀者想象與認知的經驗。蔓琳散文詩所建構的可能世界不是與現實相悖的瘋癲迷狂,而是有著對現實人生和人性的溫暖與撫慰,像《響器》《與雪山的距離》等都是很有分量的題材。蔓琳對于人生存的真實世界的關注,無疑強有力的反擊了學者對于中國的敘事藝術越來越脫離現實的幻想化的質疑。
《響器》是蔓琳收錄在《穿過河流的月光》的一首,七段八行,全詩如下:
我回來了,身形已經衰老。
翻過時間的懷抱,飛越每段歷史的痕跡,躺在您干裂的土壤里,聽風吹過原野,撫摸那兒時曾奔跑的每一寸土地。
誰能在我活著的時候檢閱愛情?誰能在我死后祭奠歲月?
生命用一種姿態重復,我渾濁不清的記憶。當時的月光,曾照我門前紛沓的小徑。
我的愛人,我一脈相承的孩子。
我要睡了。
然后,用別人的聲音,留我在這世界活著的方式。
這是一曲南下軍人命運的挽歌,從字面看這首散文詩就如同一則簡短的記事日記,主角是孓然地回歸故土的南下軍人“我”;時間:“翻過時間的懷抱”、“飛躍每段歷史的痕跡”;地點;土壤、原野、土地;事件:“我回來了”、“我要睡了”。寥寥數字,將“我”所要面對的身形衰老、生命消逝的悲劇意蘊完成,離開人世時,也許一切絢爛終將歸于平淡。“我要睡了”,它滿足了南下軍人對于生命的擁有欲望,“曾照我門前紛沓的小徑”是那種對于昔日輝煌幻象的回憶。人生命的終結是無法預知的也是一種生命的必然,作家寫作時借用了“我”一個南下軍人的身份,這個身份的建立就體現出了與現實世界對應的可能世界軍人垂死體驗的權威性。這種身份的調用使詩作本身充滿了對死亡的悲憫,應當說文本本身并未提及響器的有關具體信息,它的曲調、曲式、配器的安排、節奏,以及歌唱者等等。除了文本那一句“用別人的聲音,留我在這世界活著的方式”。這里就暗含著一個可能世界的安排,“我”之外的其他人的談論、歌唱、行動等其他因素組合起來 ,使文本之外的信息異常豐富,這樣創作者所建構的可能世界的信息就顯得更為深刻復雜,調動了讀者的經驗與想象,詩本身的意義也就更為豐厚。
蔓琳的散文詩有感性的體驗、感悟,有情緒的飄忽與孤獨中的沉吟,但不是唯一的,她還有著視角轉向,從小人物的命運開始,從一個視角的的切入,拓展更大的文學空間,開啟對生活透視的可能性。
心在黑夜流浪,想起夜色的美妙,連呼吸都急促。
月光劃落,在玉蘭綻放的潔白中,如愛人輕輕撫過的手,那是多么美麗潔凈的手啊。于是一瞬間,玉蘭格外燦爛了。
……
玉蘭記得那些它們彼此相擁的夜晚,記得月光無限的柔情,記得那些跌落于黑夜中靜寂無聲的相思,那些淺淡而清澈的目光,那些星與星的糾纏,那些冰清玉潔的火焰全都融化在了一起,像冰雪守著陽光,相擁著化為涓涓清泉。
玉蘭淡淡的芬芳著,將每一個與月光相聚的夜色收藏。在她的記憶中,月光的手輕輕撫過她晶瑩的花瓣,而愛,早已穿透夜色。
——《玉蘭與月光》
文本所展現的空間不是固定在人生存的現實世界的,由玉蘭綻放到與月光的相聚,它實際上是漂流移動的,并沒有被現實的常識規約鎖住,穿過月光的手,延展到了極大的想象空間,言之有盡,意之無窮。玉蘭、心、黑夜、月光里的柔情,這些詩句結構本身就含納一個豐富完整而又有序的可能世界,這不是超越現實的極端幻想與任性恣肆,而是有著充分的現實人生根據。在對于前途未知的假設中,蔓琳幫我們撿拾丟落的記憶與經驗。
敘事就如同是一個游戲的規則。無論是現實世界的延續還是向可能世界的滑動,都是作者自我本身思想的位移,所以說不同的敘事結構里也蘊含著不同的生存觀念與生存感悟。當然不同時代的敘事文本有不同的敘事結構,這種不同的結構體現不同的生存觀念。蔓琳這位生于70年代的作家,依然保持著作家的真誠與責任,更有作家個人的生存體驗:如《生命的誘惑》中:
已經忘卻了曾經怎樣受傷的記憶,已經忘記了那些用時間慰藉的傷口,那如水般汩汩涌流的希望之翼是如何在現實中折斷翅膀,我仿佛已經忘卻了。
她始終聚焦著文本的可能世界和現實世界之間、敘事人物與現實人物命運之間的互動,在時間上沒有終點,空間上無限延伸。《城里孩子的幸福》《黑與白的辯證》《心在明月湖流放》等詩一直以來為眾多評論家所稱道。正是基于現實社會和人生背景的感觸蔓琳把對豐富生活的感性觸發,以理性的建構反映在情感世界和片斷記憶中。
依賴于現代化電子技術的大眾傳媒的發展,電影、電視、網絡的迅速普及圖像時代的來臨改變了文學原有的存在方式,許多理論家說進入了讀圖時代,視覺圖像成為了人們主要的審美形式,造成了文學藝術深重的危機感,對于文學藝術無暇東顧,有人說文學正在走向消亡。很多作家從事的是商業化的寫作迎合市場和讀者的趣味,對資本欲和權力欲的頂禮膜拜。也許我們不禁要問,在這樣后現代消費主義的文化語境下,中國的散文詩還能走多遠?面對現代散文詩的時常缺場,諸如蔓琳這樣的作家依然保持對詩的關注并且以其創作親近讀者,至少在客觀上了改善了現代散文詩、現代文學的生存危機。所有的文化都涉及人的存在問題,都表現為一種符號,一種指意的實踐,文化不是政治的口號而是討論人生存的一些基本問題。人內心生活經常是充滿的缺憾和創痛的,真實常常被遮蔽,被生存的表象掩蓋,可貴的是青年女詩人蔓琳憑借對藝術上執著追求給讀者創造了一個審美的無限可能的世界,為理論界重建文學藝術價值提供了重要的實踐參照。
因為:
我們在乎的
不是浮華城市的交情
而是一路跌跌撞撞的歷程
上蒼,可以作證
我們無數磨難的日子
靈魂的傷,苦或者熬煎
但,我們依然義無返顧
眼睛、軀體、和手
蔓琳《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