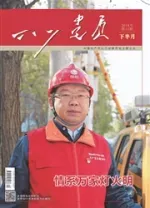未來10年是改革壟斷利益攻堅期
未來10年是改革壟斷利益攻堅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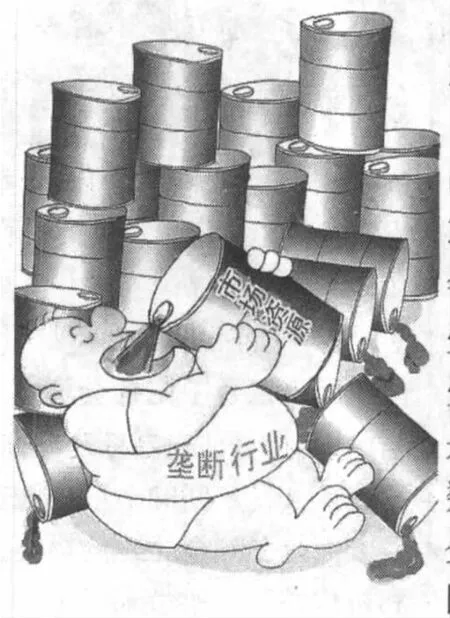
“中國過去10年,靠比較優勢迅速發展僅僅只是表象,實質動力是制度改革帶來的發展紅利。表象上說,未來30年,中國的中西部地區將成為新的外資匯集高地,中國經濟也將因此獲得新一輪發展動力。然而,中國現在發展的核心問題還是在于是否有魄力和決心,去改革既有壟斷利益,未來10年是改革壟斷利益的攻堅期。”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日前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如此表示。
《第一財經日報》 (以下簡稱日報):你認為這10年變革的核心是什么?
張漢林:我們基本上建立了開放經濟的制度體系,以及為它服務的開放經濟的法律制度和與市場經濟相關的法律體系。這是在用制度性的變革去推動經濟發展。這30年,最核心最重要的東西可能是制度的變革,是從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形成和完善。這加速了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革和發展。
中國從入世前被動地融入經濟全球化,轉變成積極主動地融入全球化。從改革開放初期的短期經濟,過渡到相對于自己國內消費人口來說,大多數的產業和產品供給基本上處于過剩的時代。
規則意識、法制意識、知識產權意識的健全,這個在過去都沒有,都是因為融入了全球化,才形成了這樣一種意識。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立法等方面,我認為怎么做都不為過,這是中國真正實現創新型國家目標的制度基礎和決定力量。
日報: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發展速度過快以至于影響發展質量,你認為呢?
張漢林:我認為我們現在年均GDP9%以上的增速是合適的。首先,中國的人口龐大,不能簡單地去和美國、日本比。其次,中國在高度全球化背景下的加速發展,可以充分利用全球的市場資源。我認為中國的GDP連續20年9%到10%的增速,才是合適的。現在的10年或者30年最大的受益者、受益地區是東部少數的國有企業和集團,但是中國西部、東北部地區,人口地域等資源沒有配置好。中國的前30年僅僅實現了兩個對外開放,第一個是東南沿海地區的開放,第二個是制造業的開放。中國的服務業和農業對外開放程度還遠遠不夠,我的信心來源于此。中國發展的動力來源于地區、產業發展的不平衡,這個任何國家都不具備。在中國,我們永遠擔心經濟過熱,其他發達國家永遠擔心經濟不增長。
東北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增長潛力,起碼還需要20年的投資和出口拉動。我們要承認,中國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很大的不平衡。在這個背景下,你要不要實現全國一刀切的貿易政策、投資政策等,這個時候就要反省東中西部的產業布局和投資政策。
日報:現在中國面臨很多新的挑戰與改革的阻力,很多人甚至對改革的預期是悲觀的,你認為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和突破口在哪里?
張漢林:中國雖然經濟發展不平衡,但是有幾個最基本的東西不能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不能動搖,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不能動搖。停步或者原地踏步或者倒退,只能讓事情更復雜和被動。
其實是改革開放不夠,而不是過頭了。醫療教育資源領域的問題,就在于此。融入貿易的全球化在短期內對中國收入分配會產生負面影響,但是長期內是好的,金融的全球化也是這樣。如果不深化改革,負面將是長期的。
最可悲的問題是,改革開放30年,入世10年,我們對內對外沒有形成良性循環互動的傳導機制。我堅定支持大部制,這個大部制不是缺乏協調扭曲的大部制。比如說,陸海空應該一體化,今后的管道運輸會很糟糕,因為大多數管道運輸在中石油那兒。
日報:現在關于中國制造的話題層出不窮,與此相關的主要包括入世以來的貿易摩擦,匯率、人力成本優勢在消減。你認為中國制造升級的瓶頸,或者突破點在哪?
張漢林:中國制造的問題最重要的還在于你怎么看待知識產權和智力在國內的作用。我們要給知識產權充分的利益,現在遠遠不夠。制造業強國德國就是這樣做的,你會發現德國不存在知識產權執法的問題,不存在知識產權的技術入股等問題。所以這就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了,是影響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根本,是一種文化。而這恰恰是我們民族文化中最缺少的。
我們總說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如果沒有知識產權的嚴格立法、執法和司法,是實現不了的。比如,中國移動和聯通,這些企業也都是靠行政和壟斷。
人民幣的國際化是必然的選擇,但是重要的前提是中國的金融業必須高度的自由,和進行市場化的改革。因為中國的資本化項目的自由化改革還是人民幣的國際化,必須要與國內金融業的改革相協調相配合。你看德國馬克變成歐元的過程,歐洲貨幣一體化的過程,都是高度市場經濟一體化的,金融業是充分發展的。人們都說證券公司的上市公司和產業布局是一個國家經濟結構和發展的晴雨表。而中國的很多上市公司就很奇怪。
至于貿易摩擦,我的結論是10年到15年都會持續。因為在加工貿易、發展模式、知識產權的保護等一系列的東西上,發展不平衡問題需要10年到15年才能基本解決。
(文/郭麗琴江艾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