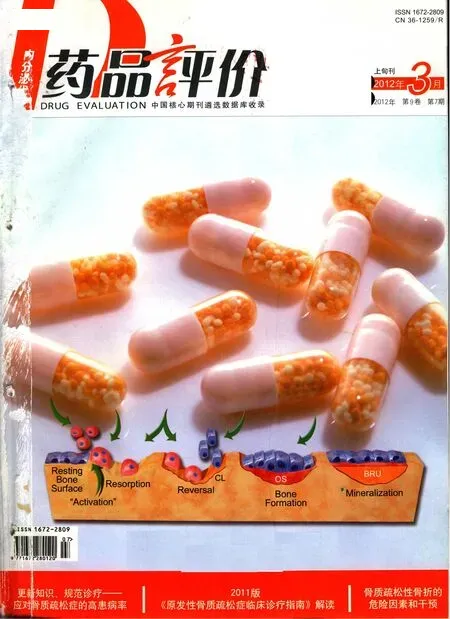骨質疏松診斷方法綜述
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代謝內分泌研究所 廖二元
隨著近代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免疫學和放射影像學的迅速發展,近年來在代謝性骨病,尤其是骨質疏松的診斷方面有了很大進步。新的實驗技術和特殊檢查為骨質疏松的臨床早期診斷和病因鑒別提供了較特異而敏感的依據。但是,和其他疾病一樣,骨質疏松診斷的基礎和關鍵首先是要收集完整而有價值的病史資料,通過體格檢查發現陽性體征并確定有意義的陰性體征。如診斷仍有困難,應根據需要和可能,選擇必要的實驗室檢查或特殊檢查,以便早期明確診斷。
骨質疏松的病史和癥狀診斷
1. 病史
幼小兒童要特別了解有無骨痛、骨畸形和活動受限;有無手足搐搦、精神失常或失眠;有無多尿、口渴、夜尿增多、尿痛、血尿、腰痛等。體重有無改變及變化的特點。例如,在臨床上,醫師很難對主訴為下背痛的患者作出明確的病因診斷,文獻中也提出過不少的鑒別診斷方法和鑒別指南,雖然都可應用,但實用價值如何,有待進一步驗證。Dudler等[1]總結大量的經驗和文獻資料,指出避免漏診、誤診和提高早期確診率的關鍵仍在詳盡的病史詢問和細致的體格檢查,這是最可靠、最基礎和最經濟的診斷方法。對女性來說,要查明月經初潮年齡,行經期、月經周期和量,絕經年齡和已絕經時間。了解生育情況,有無流產、早產,并記錄生育情況,妊娠次數及產次等。過早絕經者,多產婦、無產婦及月經稀少者均為骨質疏松的高危因素。
在既往史中,要注意了解有無長期消化道癥狀,如腹瀉、便秘、食欲不振、偏食;有無神經精神失常、不能行走或負重、身材變短、自發性骨折或反復骨折史。既往X線檢查是否發現過腎結石、異位鈣化灶,是否有長期臥床史等。對有手足搐搦,肝、膽、腸重大手術史者要詳細了解其原因和后遺癥等。要特別注意詢問有無甲亢、肢端肥大癥、糖尿病、腎上腺疾病、性腺疾病及其他長期、重大、慢性疾病等病史。雖然80%以上的全身性骨密度降低是由原發性骨質疏松癥(primary osteoporosis)引起的,但骨密度降低亦可見于許多其他疾病或疾病的某個階段[2]。有不少繼發性代謝性骨病僅憑確切的病史(如氟骨癥和糖皮質激素所致骨質疏松癥等)即可基本明確診斷。
許多代謝性骨病為遺傳性疾病,因而要仔細詢問家族一級親屬中及相關成員中的類似疾病史,尤其要查詢有無骨折、骨痛、早年駝背或其他骨骼畸形等病史。遺傳學家系調查是診斷遺傳性代謝性骨病或體質性骨病的基本依據,必須詳盡、準確。
2. 癥狀診斷
2.1消瘦
引起消瘦的常見代謝性骨病和內分泌疾病主要有甲狀腺功能亢進癥,1型與2型糖尿病(體重減輕較快)、腎上腺皮質功能減低癥、Sheehan病、嗜鉻細胞瘤、內分泌腺的惡性腫瘤、神經性厭食、胰性霍亂(血管活性腸肽瘤)等。不論是何種原因所致的消瘦或營養不良癥均伴有骨量下降和峰值骨量(PBM)減少,至成年與老年期后易發生骨質疏松性骨折。
2.2 性腺功能減退
任何原因引起的性腺功能減退都伴有程度不等的骨密度降低[3]。雄激素合成或分泌減少,則可使毛發脫落(包括性毛、非性毛和兩性毛)。各種原因引起的睪丸功能減低癥和(或)腎上腺皮質和卵巢功能減低癥等。由于性激素與骨代謝的關系十分密切,所以凡遇有毛發脫落的患者均要想到繼發性代謝性骨病可能。青春發育期后男性或青春期前的男孩如出現乳腺發育則屬病理性。引起病理性男性乳腺發育的疾病有內分泌與非內分泌疾病兩大類,前者見于Klinefelter綜合征、完全性睪丸女性化,睪丸產雌激素腫瘤、真兩性畸形、甲狀腺功能亢進癥、先天性腎上腺皮質增生等;這些內分泌疾病往往均伴有程度不一的骨代謝異常。
2.3 骨痛與自發性骨折
骨痛為骨質疏松的常見癥狀。在骨質疏松癥中以女性絕經后骨質疏松最為常見,嚴重者常發生自發性骨折,或輕微外傷即引起骨折。骨折后由于局部出血水腫壓迫神經、或神經受牽扯和局部肌肉痙攣可引起局部疼痛,但沒有骨折的骨質疏松者也可有骨骼疼痛,可能與骨小梁斷裂有關。但個人對疼痛的敏感性不同,故疼痛的程度個體間有很大差異。除女性絕經后骨質疏松外,其他類型的骨質疏松癥和大部分骨退行性變、骨腫瘤、骨骼的病理性骨折等均可出現類似的骨痛、自發性骨折,或輕微撞傷、跌倒后的骨折,應注意鑒別。
骨指數
骨指數主要以下有三種:
1. 掌骨指數
測量第二掌骨中部橫徑(AB)和外側骨皮質橫徑(CD與XY),掌骨指數 = (CD+XY)/AB×100 ,正常值為33~75,少數人在75 以上。
2. 股骨指數
測量法與計算法同掌骨指數。股骨指數正常值為32~76,多數人在46以上。掌骨指數 + 股骨指數=周圍指數。周圍指數正常值為90以上。
3. 第三腰椎指數
測量第三腰椎椎體中央高度(AB)與椎體前緣高度(CD)。腰椎指數=AB/CD×100,其正常值為74~97,多數在81以上。
以上骨指數測量主要用于骨質疏松癥的診斷,周圍指數<88為周圍型骨質疏松癥。腰椎指數< 80者為脊柱型骨質疏松癥。如兩者均存在為混合性(全身性)骨質疏松癥。骨指數雖有粗糙的缺點,但在條件不允許時,仍不失為骨質疏松診斷的重要參考依據。Singh指數是測定骨折的常用方法。
血生化指標測定
1. 血清總鈣
各實驗室的正常值范圍略有差異,測定方法不同也對結果有一定影響。常用的正常值為:嬰幼兒2.5~3.0mmol/L(10~12mg/dl);成人2.10~2.55mmol/L(8.4~10.2mg/dl)。成人至70歲前,血清總鈣均較穩定,95%以上的人群波動在2.20~2.50mmol/L(8.8~10.0mg/dl)之間。一般認為,如血清總鈣低于2.20mmol/L(8.8mg/dl)或高于2.55mmol/L(10.2mg/dl)則屬異常。除疾病外,實驗性干擾因素很多,分析結果時應予注意。
測定離子鈣具有一定的技術難度,一些單位改用測定可濾過鈣也具有同樣意義。血清可濾過鈣正常值為4.7~6.8mg/dl[10],其與離子鈣的相關性良好,但可濾過鈣在診斷間發性輕型甲旁亢方面的敏感性低于離子鈣。
2. 骨密度降低伴血鈣升高
原發性骨質疏松癥不伴血鈣升高。一旦患者的血鈣(早期為游離鈣)升高就可以否定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斷。而且,許多原發性甲旁亢和其他原因引起的繼發性骨質疏松早期可能僅表現為骨密度降低,容易誤診為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血鈣(尤其是游離鈣)升高的主要原因是過度溶骨,除甲狀旁腺分泌過多的甲狀旁腺素(PTH)外,能引起自主性溶骨的其他激素主要有破骨細胞活化因子(osteoclast.activating factors,OAF)、1,25-(OH)2維生素D3[1,25-(OH)2D3]、PTH相關肽(PTH-relatedpeptide,PTHrP)、T3/T4和糖皮質激素。骨密度降低伴血鈣(尤其是游離鈣)升高有兩種可能,一是原位的或骨轉移的癌細胞自主溶骨(如多發性骨髓瘤細胞或進入骨組織的一般癌細胞),但是,如無OAF作用,通過這種途徑導致血鈣升高的可能性較小;二是由于非甲狀旁腺腫瘤(如肺腺癌、乳腺癌、多發性骨髓瘤、淋巴瘤或頭頸部腫瘤等)分泌一種或多種OAF或PTHrP所致,其臨床特點是:①血鈣多顯著升高,但去除腫瘤后血鈣正常,如復發又再次升高;②血PTH被抑制(假性甲旁亢例外),血磷正常或輕度減低;③二膦酸鹽(bisphosphonate)類藥物治療雖可使血鈣降低,但不能有效提高骨密度。
因此,只要血鈣升高,就應積極尋找腫瘤病灶。對于甲狀旁腺腫瘤(或增生)來說,一般可作甲狀腺區B超、甲狀旁腺CT/MRI檢查,如仍為陰性,則作甲狀旁腺甲氧基異丁基異腈(MIBI)掃描。對于非甲狀旁腺腫瘤來說,可根據具體情況選擇CT、正電子發射斷層顯像術(PET)CT、MRI、核素掃描或其他必要的腫瘤定位檢查,并同時檢測P1H、PTHrP或其他OAF,如受體結合NF-KB受體活化因子配體(receptor activator of NF?KB ligand,RANKL)。雖然原發性甲旁亢與腫瘤性高鈣血癥的血鈣和骨生化指標均明顯升高,血磷均顯著降低,但前者的PTH升高而后者的PTH降低。
3. 骨密度降低伴血磷升高或降低
骨密度降低伴血磷降低的主要原因是低血磷性骨軟化癥,典型病例診斷不難。患者在經過長期的中性磷酸鹽治療后,往往伴有明顯的軟組織鈣化,使骨密度呈假性升高。一個細心的臨床醫師可能發現,各部位的骨密度降低并不一致,或在低密度的X線片中出現高密度影,這往往是合并骨硬化的強烈信號;此時無論用骨密度判斷病情變化或評價治療療效均失去意義。
腎臟疾病引起的繼發性甲旁亢者的特點是血PTH和骨生化標志物升高,而血鈣正常。如患者出現血鈣升高,即提示增生的甲狀旁腺已經具有PTH分泌的自主性,應診斷為三發性甲旁亢(tertiary hyperparathyroidism)。
骨密度降低伴血磷增高是終末期腎病(end stagerenal disease,ESRD)的主要并發癥[4]。慢性腎病引起的繼發性甲旁亢因PTH升高,骨吸收與新骨形成增加和骨纖維組織增生而導致多臟器轉移性鈣化與心血管病變,更嚴重病例則可有Sagliker綜合征(面容丑陋、短肢畸形、腭骨與頜骨前突、軟組織腫脹、牙齒與牙床異常等)或鈣化性尿毒癥性動脈病變(calcific uremicarteriolopathy)表現,后者常見于長期透析治療或腎移植后患者,偶見于原發性甲亢、維生素D中毒、乳-堿綜合征、特發性新生兒高鈣血癥和腫瘤性高鈣血癥者。
4. 血清鎂
血清鎂測定對代謝性骨病診斷的重要性在于缺鎂常與其他代謝性骨病或全身性疾病同時并存。血鎂正常并不能排除鎂代謝異常,另一方面,高鎂血癥很少單獨存在,往往并發于某些疾患或作為某些疾病的表現之一。
正常人血清鎂總量為0.7~1.0mmol/L,其中游離鎂約0.40~0.55mmol/L,陰離子結合鎂約為0.23~0.35mmol/L。
嚴重的高鎂血癥可導致心律紊亂、心肌梗死、昏迷、心跳驟停和呼吸衰竭[5-7]。低鎂血癥常合并低鈣血癥和手足搐搦癥,尤其多見于重癥疾病、新生兒心肌梗死、惡性高血壓、心力衰竭及許多慢性消耗性疾病。
骨轉換標志物測定
骨組織在構塑和重建過程中,骨基質不斷生成與分解,一些有相對特異性的基質產物、酶和裂解物進入血液或尿液。測定這些物質的含量,并結合其他檢查所見,可協助代謝性骨病的診斷。
臨床疾病的診斷或療效評價主要是要了解骨的轉換率高低,骨形成和骨吸收狀況及其相對強度。因此,可將這些標志物分為三組:一組是代表骨形成的指標;二組是反映骨吸收的指標;三組是提示骨的特殊變化,如某些遺傳性骨病和骨源性腫瘤。但是,標志物的測定也存在下列缺點:①有些標志物的組織特異性和細胞特異性不高,如血清堿性磷酸酶總量除來源于骨組織外,亦可由腸、肝、膽、肌肉等組織釋放入血;②骨轉換率升高時,往往伴有成骨和破骨活性的同時升高;③指標測定的方法缺少特異性;④正常值范圍廣,病理變化與正常反應和生理變化往往重疊;⑤在同一個體中,連續測定的批間變異系數較大,有時可高達20%~40%。這是由于個體的飲食習慣和活動強度影響的結果。因此,單憑生化標志物往往難以對疾病作出正確判斷。
Sasaki等[8]發現在6個月的糖皮質激素的治療中,腰椎骨密度顯著下降,OPG在用糖皮質激素2周內即顯著下降,且TRAP(反映骨吸收)的表達亦顯著下降,而骨吸收指標僅暫時性下降。血清OPG水平與骨密度呈正相關。Bekker等[9]發現皮下注射OPG可抑制骨吸收,用于治療骨質疏松。但Browner等[10]的研究沒有發現OPG與基礎的骨密度及后繼的中風或骨折相關。我們的研究表明E2增加正常人成骨樣細胞OPG mRNA和蛋白的表達,而且呈劑量依賴性,而孕酮不具有上述作用,提示E2和孕酮預防絕經后骨丟失的機制不同。
測定血清中OPG、RANKL、OPG/RANKL比值可能更好地反映骨轉換水平,Lindloerg等發現OPG/RANKL與雌激素治療引起的小梁骨BMD升高呈負相關。正常成人血清OPG(ELISA法)為0.94±0.34ng/ml。
骨腫瘤標志物
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MM)是異常漿細胞(骨髓瘤細胞)過度增生的一種惡性腫瘤。在多發性骨髓瘤和未定型單克隆γ蛋白病(monoclonal gammopathy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患者中,常可發現細胞遺傳學異常(如delta 13)和免疫球蛋白的位點易位。腫瘤細胞分泌異常的M蛋白、本-周(Bence-Jones)蛋白和促破骨細胞因子可作為本病的生化診斷標志物。患者經治療后仍有H-ras基因的過度表達,往往提示預后不良。血清ALP、血鈣和血磷升高無特異性,但可反映骨損害的嚴重程度。血PTH下降說明高鈣血癥是非PTH依賴性的。
約70%以上的系統性肥大細胞增多癥(systemic mastcytosis)可并發骨骼病變,其中以全身性骨質疏松癥為最常見表現。本病的診斷較困難,除骨活檢和骨髓檢查外,血生化標志物異常可能為本病的最重要診斷線索。
肺癌和乳腺癌易侵犯骨骼。骨骼損害可表現為轉移灶的非特異性浸潤性溶骨、骨質疏松或轉移性病灶征象。這些病變也可能與腫瘤細胞分泌某些異位激素(如ACTH及其類似物和PTHrP等)或局部因子(IL-1、IL-6、TNF、TGF等)有關。甲狀腺髓樣癌(C細胞癌)的特異標志物為降鈣素、降鈣素基因相關肽(CGRP)及katacalcin(KC)。
遺傳學與分子生物學診斷
大多數代謝性骨病屬遺傳性疾病。染色體核型分析可明確Turner綜合征、Klinefelter綜合征、常染色體三體或單體綜合征等的診斷。一些代謝酶缺陷所致的代謝性骨病(如磷酸酶異常、同型胱氨酸尿癥、黏多糖病、黏脂病、軟骨發育不全、腺苷脫氨酶缺乏癥等)可用分子生物學方法檢測酶的異常部位或受體的缺陷本質,明確診斷。
有些代謝性骨病的病因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發展被逐漸闡明。例如,家族性低尿鈣性高血鈣癥是一種常染色體顯性遺傳病。由于主細胞的Ca2+受體(感受器)基因發生點突變而部分或完全喪失Ca2+濃度信息的傳遞功能,主細胞接受Ca2+濃度刺激的“調定點”升高;鋰鹽可干擾主細胞的“調定點”設置和Ca2+感受器的敏感性,故可導致主細胞增生肥大,甚至形成腺瘤。又如,遺傳性低血磷性佝僂病/骨軟化癥的病因已基本查明,可通過PHEX基因,FGF-23基因突變分析或測定血清水平來明確診斷。
臨床上最常見的原發性骨質疏松癥的危險因素中,遺傳因素占70%~80%。調節骨代謝的激素、酶或局部因子的基因和它們所表達的活性蛋白均存在顯著的異質性,其中一些基因類型與骨質疏松有密切關系。例如,具有HH骨鈣素等位基因、或TT轉型生長因子-β1等位基因,或AA IL-1受體拮抗物等位基因、或維生素D受體等位基因者易患骨質疏松,甚至骨折。這說明本病為多基因遺傳性疾病, 用分子生物學方法篩選高危人群的易感基因將是本病防治的發展方向,并可望從根本上防治骨質疏松。從我們篩選雌二醇相關基因的情況來看,這方面的工作任務還十分繁重,估計參與的基因很多。但哪些是最有意義的,目前尚難肯定。又如,Yamada等研究顯示,TGFβ1基因的T869C多態性(Leu10pro)和C509T(Cys509Thr)與BMD有關,具有此多態性者易發生骨質疏松和骨折。
以腎臟、骨骼和腸黏膜為靶組織的激素(PTH、降鈣素、1,25-(OH)2D3),激素受體和鈣受體基因均存在表達和功能上的異型性。由功能正常到功能喪失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病態譜系,反映在臨床上的是個體某器官礦物質代謝的質量和數量方面的差異。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重大課題,對探討各種代謝性骨病的發病機制、診斷和治療具有重要意義。
現已發現,由激素分泌細胞增生、凋亡、腺瘤或腺癌引起的許多內分泌代謝性疾病都存在遺傳信息的缺失或病理性獲得,鑒定這些遺傳信息的異常是病因診斷和治療的最終目標。隨著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與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這個目標的實現已經開始。例如,高功能性甲狀旁腺組織,特別是甲狀旁腺腺瘤中的細胞DNA常在多個部位有遺傳信息的缺失,常見的缺乏部位為1p、11q或抑癌基因(如p53基因或視網膜母細胞瘤基因)位點,真正意義上的病因診斷應該針對遺傳信息異常的部位和本質進行。
骨代謝激素測定
血PTH、PTHrP、降鈣素、維生素D等測定是診斷代謝性骨病的重要方法。血PTH對高血鈣的鑒別尤為重要。是診斷原發性與繼發性甲旁亢、原發性與繼發性甲旁減的最主要依據;同時也是診斷和鑒別其他代謝性骨病的重要手段。但是,循環血中的活性PTH水平很低,而血液中存在濃度比活性PTH高得多的無活性PTH片斷甚至前PTH原、PTH原等物質干擾了PTH的測定。另外,腎小球濾過率和甲狀旁腺的PTH分泌率的改變也對血PTH值有明顯影響。因此,分析結果時必須考慮血PTH測定的敏感性和代表甲狀旁腺功能活動的特異性。近年,人們使用雙位點夾心法來測定PTH,目的是精確分開PTH1-84、PTH-C和PTH-N片斷。提高了PTH測定的診斷效率。目前用雙位點法測定PTH的敏感性已經達到鑒別原發性甲旁亢和非甲狀旁腺性高鈣血癥的要求。
PTH在血循環中主要有四種存在形式:一是完整的PTH1-84,占5%~20%,具有生物活性;二是N端PTH1-34(即PTH-N),量很少;三是C端PTH56-84(即PTH-C,其中又可分為若干種不同長度的片斷);四是中段 PTH(即PTH-M)。后二者占 PTH的75%~95%,半衰期時間長,但無生物活性;前二者半衰期時間短,不超過10min。此外,還有少量的PTH原、前PTH原等[11]。
骨密度測定的診斷標準
根據WHO推薦的診斷標準[12-14],骨礦含量或骨礦密度的檢測結果可分為:骨量正常、低骨量、OP和嚴重OP四類。骨量正常:BMC(BMD)大于同性別峰值骨量平均值減1SD。低骨量(或骨量減少):BMC(或BMD)小于峰值骨量平均值減1SD,但大于峰值骨量平均2.5SD。OP:BMC(或BMD)小于峰值骨量平均值減2.5SD。嚴重OP:OP伴一處或多處骨折。
動態試驗與特殊試驗
這類試驗很多,如腎小管磷重吸收率(TRP)、磷廓清試驗、最大腎小管磷重吸收率(TmP/GFR)、PTH興奮試驗和鈣受體調定點試驗等。隨著激素測定技術的進步和疾病病因的闡明,這類試驗的作用已日漸減少,但在某些特殊條件下,仍是協助許多代謝性骨病診斷和鑒別診斷的重要方法。
放射學和放射性核素檢查
常規放射學檢查的主要目的是發現和鑒定骨骼的畸形、骨折、骨關節病、異位骨化和異位礦化、骨壞死、骨折不連接和一些較顯著的骨骼形態改變;其次,也可測定骨質的密度和密度改變的范圍與程度;最后,有些代謝性骨病往往有特殊的X線表現。這些異常改變用其他非放射學檢查方法是無法替代的。隨著科技發展,人們已開始用微CT、微MRI等對骨組織進行定性與定量分析,明顯提高了診斷的準確度和效率。
放射性核素檢查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對局部或全身的骨組織進行顯像或骨密度測定,協助骨病變的診斷,療效評價和預后判斷。例如,用骨SPECT定量(QBS)檢測骨密度和骨轉換率。二是對甲狀旁腺病變進行術前定位,以明確診斷,有助于制定手術方案,縮短手術時間,減少術后并發癥。
甲狀旁腺病變的定位技術很多,各有優缺點。除高分辨超聲、CT和MRI外,近年來核素技術的應用較多。90年代以前,多用201TI/99mTc-過锝酸鹽或201TI/123碘化物顯像;1989年以來多采用99mTc-MIBI(锝-甲氧基異丁基異氰化物)作甲狀旁腺顯像劑(單用或加用放射性碘化物)。最近,有人試用99mTctetrofosmin作甲狀旁腺顯像獲得成功。
1. 99mTc-sestamibi掃描
在有關原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癥患者術前是否要驗明病變的甲狀旁腺腺體數目及部位的爭論中,唯一一致的觀點是至少要做99mTc-sestamibi掃描。當掃描證實只有一個腺體時,其正確率幾乎等于100%。一些醫院的掃描效果比別的醫院要好得多是因為技術上的差異所致。但只要該法掃描證實為單一腺瘤,大多數醫院都不會在掃描時漏診。通常該法檢測腺瘤的敏感性為85%~100%,準確率約94%。檢測的最小腺體重400mg。本法對增生的檢查價值不如腺瘤。對準備再次行甲狀旁腺手術的患者,術前檢查更有幫助。99mTc-sestamibi掃描的另一優點是可對腺瘤的功能作出判斷,這是其他方法所欠缺的。
2. SPECT掃描
SPECT掃描是借助注射放射性的99mTc-sestamibi、201TI、123I或99mTc-MIBI等得到三維圖形的技術,有時會很有用,但一般在甲狀旁腺功能亢進癥第一次手術前沒有這個需要。可發現60%左右的甲狀旁腺腫瘤,但2.0g以下的小腺瘤易于遺漏。有被改良的99mTc-sestamibi掃描取代的趨勢。
甲狀旁腺攝取99mTc可能與嗜酸性細胞功能和數目有關。一般通過99mTc-MIBI的早期相和后期相顯像之差來確定病變的范圍和性質。經過長期的實驗和臨床應用,現認為99mTc-MIBI優于TI/Tc法,因為前者在甲狀腺的清除比甲狀旁腺快。雙相99mTc-MIBI法的早期相主要用于顯示甲狀腺和異常的甲狀旁腺,后期相主要用于顯示甲狀旁腺病變。本法的診斷率高、操作簡便,加用123I作雙核素的甲狀腺-甲狀旁腺早期相顯像可進一步提高病變的分辨率,但99mTc-tetrofosmin可能與99mTc-MIBI的敏感性相似。
各種甲狀旁腺影像檢查要根據臨床需要和具體病情選擇。當甲狀腺明顯腫大時,超聲檢查易遺漏甲狀旁腺病變,故選用MRI較為合理。如高度懷疑甲狀旁腺增生性病變,則各種影像檢查的敏感性相差不明顯。核素檢查對腺瘤的診斷優于其他方法。
骨組織形態計量分析
經穿刺獲取骨組織標本,制成骨切片,在顯微圖像分析儀或激光掃描共聚焦顯微鏡(CLSM)下測量骨小梁、骨細胞、骨皮質等的各種參數,全面分析判斷骨組織的形態學特點。這種方法的優點是能將病變觀察深入到骨組織或骨細胞水平,對發現早期病變很有幫助。其次,X線照片、骨密度分析、定量CT或定量MRI等均無法觀察到骨有機質和骨細胞的變化,而形態計量分析可精確測量有機質和細胞的一些參數,對骨形成和骨吸收有更為深入和客觀的了解。
顯微圖像分析只能在一個骨切片層面上進行觀察分析,而CLSM可通過不同深度的一系列光學切片重建骨組織的三維結構。對骨組織和骨細胞(體外)還可進行動態觀察。但該技術屬創傷性,而且只有同一層面的骨切片才有較好的可比性。
[1] Dudler J, Balague F. What is the rational diagnostic approach to spinal disorders[J]. Best Pract Res Clin Rheumatol, 2002, 16(1): 43-57.
[2] Singer A. Osteoporoeis diagnosis and screening[J]. Clin cornerstone,2006, 8: 9-18.
[3] Doumouchtsis KK, Perrea DN, Doumonchtsis SK. The impact of hormone changes on bone mineral deficit in chronic renal failure[J].Endocr Res, 2009, 34: 90-99.
[4] Weisinger JR, Carlini RG, Rojas E, et a1. Bone disease after renaltransplantation[J]. Clin J Am Soc Nephrol, 2006, l: 1300-1313.
[5] Schelling JR. Fatal hypermagnesemia[J]. Clin Nephrol, 2000, 53(1):61-65.
[6] Birrer RB, Shallash AJ, Totten V. Hypermagnesemia-induced fatality following opsom salt gargles[J]. J Emerg Med, 2002, 22(2): 185-188.
[7] Morisaki H, Yamamoto S, Morita Y, et al. Hypermagnesemia-induced cardipaulmonary arrest before induction of anesthesia for emergency cesarean section[J]. J Clin Anesth, 2000, 12(3): 244-226
[8] Sasaki N, Kusano E, Ando Y, et a1. Glucocorticoid decreases circulating osteoprotegerin(Oeg):possible mechanism for glueocortioid-induced osteoperosis[J].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2001,16: 479-482.
[9] Bekker PJ, Holloway D, Nskanishi A, et al. The effect of a single dose of osteoprotegerin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J Bone Miner Res,2001, 16 (2): 348-360.
[10] Browner WS, Liu LY, Cummings SR. Association of serum osteoprotegerin levels with diabetes,strokes、bone density, fractures,and mortality in elderly women[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1,86(2): 631-637.
[11] Shevde Nk, Pike JW. Ectrogen modulates the recruitment of myelopoietic cell progenitor in rat through a stromal cell-independent mechanism involving apoptosis[J]. Blood, 1996, 87: 2683-2692.
[12] WHO. Assessment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 Risk and its Role in Screening for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R]. WHO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Geneva, 1994.
[13] Kanis JA, Meton LJ, Christiansen C, et al. The diagnosis of osteoporosis[J]. J Bone Miner Res, 1994, 9: 1137-1141.
[14] Cummings SR, Nevitt MC, Browner WS, et al. Risk factors for hip fracture in white women[J]. N Engl J Med, 1995, 332: 767-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