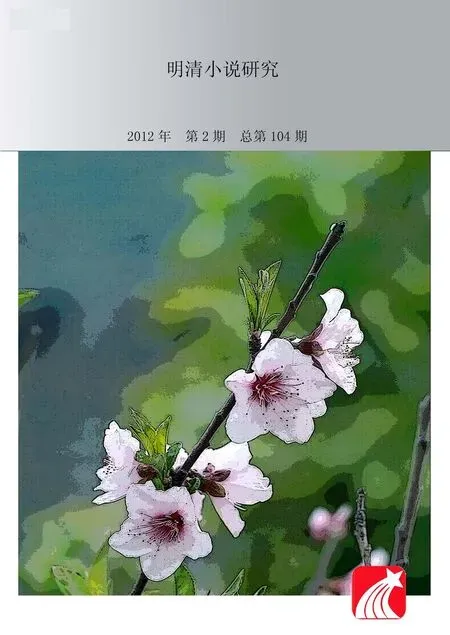流言時代:《孽海花》與晚清三十年
··
魯迅在1923年出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將《孽海花》歸為“清末之譴責小說”之中。①此論影響久遠,不過魯迅更多是從思想傾向出發得出判斷,并沒有詳加分析。后學踵武其后,往往蕭規曹隨,然而“譴責”之說只是諸多看法之一種,并非唯一不移之定論。僅就當時廣為暢銷的《孽海花》而言,并無太多魯迅歸納出的 “筆無藏鋒、辭氣浮露”的特色,倒是頗有些自然主義傾向。如果說《孽海花》確實包含有主文譎諫的構思,那更多是委曲輕謔的載道言志傳統的剩余產物,如果從題材敘述的角度,它像一個在商業環境中被放大的、用書寫馴化的、通過大眾傳媒擴散開來的“流言”。
在進入論述之前有必要簡單交代一下,之所以選擇“流言”這一角度切入,是因為近現代中國小說文體的成型一方面固然由于西方Novel譯介的影響②,另一方面復可追溯至神話、史傳、志怪傳奇③,但從文體自身演變來說,四大奇書、三言二拍這些話本章回的假語村言,無不具有民間口頭文學的色彩,換句話說,它們在文人化之前很多都有“流言”的背景,而即使在文人創作成為主流,說部故事再次沉入民間“小傳統”之后,這種性質依然作為潛在的因素若隱若現。另外,本文沒用其他類似詞語諸如訛言、謠言、傳聞等,是因為訛言,顧名思義,本身即帶有虛假信息的意思,而本文所討論的文學話題顯然無關乎真假。謠言按照傳播學約定俗成的定義,即“社會中出現并流傳的未經官方公開證實或者已經是為官方所辟謠的消息”④,信息與謠言區分的界限并不明顯,因為即使是官方的聲音也未必代表著一定就是真實。⑤這一點需要注意,尤其是針對晚清民初的輿論傳播環境。傳聞比較中性,較貼近本文所要討論的文學書寫作為無法確定信息真偽的一種話語的意思,但是更適用于新聞傳播學的信息流通的社會科學話語中。⑥本文采用“流言”一說,主要是在傳聞的基礎之上,強調其在產生、傳播及作用于讀者的整體動態運作過程。簡而言之,本文中的“流言”是指流通在各類傳播媒介中,無法判定真偽的信息,它在社會中產生,在傳布中成為一種反作用于社會的話語,進而帶有了意識形態的意味,形成特定的文化表現形態。
一
曾樸自述《孽海花》⑦的構思是“想借用主人公做全書的線索, 盡量容納近三十年來的歷史, 避去正面, 專把些有趣的瑣聞逸事, 來烘托出大事的背景。”⑧它著意追憶、記敘、描摹當下性的事件,并試圖勾勒現實的可能性與社會運行發展的軌跡。這種緊跟時事,并且企圖從日常瑣碎細節的敷陳中,把握數十年的社會全景圖畫的欲求,必然同作者本人寫作時的時間緊迫、收集資料的限度、以及結撰文本時的各種技術上的條件限定產生一定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要在結構,胡適在1917年給陳獨秀和錢玄同的信中斷言:“《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老殘游記》、《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諸書,皆為《儒林外史》之產兒。”⑨曾樸本人卻未必同意,他說到《孽海花》和《儒林外史》:“雖然同是聯綴多數短篇成長篇的方式,然組織法彼此不同。譬如穿珠,《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著一根線,穿一顆算一顆,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鏈。我是蟠曲回旋著穿的,時收時放,東交西錯,不離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學里說的花序。《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從頭開去,謝一朵,再開一朵,開到末一朵為止。我是傘形花序,從中心干部一層一層的推展出各種形色來,互相連結,開成一朵球一般的大花。《儒林外史》等是談話式,談乙事不管甲事,就談到丙事,又把乙事丟了,可以隨便進止;我是波瀾有起伏,前后有照應,有擒縱,有順逆,不過不是整個不可分的組織,卻不能說它沒有復雜的結構”。⑩魯迅也認為“結構工巧,文采斐然”是其長處,然而曾樸在實際寫作中其實并沒有達到他所構想的這種收放自如的傘形結構,而其實遵循了流言的運行邏輯——抓住那些最有受眾效應、最能吸引讀者眼球的話題。
曾樸有意無意中采取 “流言”式的方式——街談巷議、八卦瑣聞、謠傳、大眾輿論、知識精英的見解……這些都被納入到文本的規劃當中。而他所書寫的30年正是晚清民國鼎革之際,報紙雜志日益發展時期,在喧囂雜亂的局勢之中,信息流通的渠道多樣,也并沒有某個權威到能定于一尊的輿論機關,于是伴生的是訛言繁興、謠言蜂起。從新聞的原始失實到黨派的政治讖語,再到商業利潤和政治利益合力下的墮落新聞,再到獨裁時代的官方謠言,流言成為這段時間大眾傳媒典型的特征。而民間的悠悠眾口,對于甲午海戰、戊申變故、義和拳民、庚子西狩等國內外大事也充滿了一知半解、零星碎亂的猜想和哄傳。《孽海花》這種結構說起來煞有介事,其實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一方面現實中主客觀各種創作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小說”這一文類的現代改造尚是方興未艾。因此在小說的敘事行進中,一再顯示了中國傳統敘事模式與西來小說敘事方式的捍挌之處。
胡適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認識的:“其體裁皆為不連屬的種種實事勉強牽合而成。合之可至無窮之長,分之可成無數短篇寫生小說。此類之書,以體裁論之,實不為全德。……《孽海花》一書,適以為但可居第二流……此書寫近年史事,何嘗不佳?然布局太牽強,材料太多,但適于札記之體(如近人《春水室野乘》之類) 而不得為佳小說也。”因為作者固然有抱負要筆錄歷史、立此存照,然而因為沒有一種明確的歷史觀念,所有滂沱散碎的史實、故事、軼事、風聞、笑談、趣聞、謠言被強行編織在一起,使得敘述者常常顧此失彼,或者即使沒有失去主線,在左支右絀的顧應全局中,也顯得力不從心。當然,于今而言,這到并非缺點(當然也不是優點),而是它顯示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書寫傳統——傳統說部的傳統:一種源自民間口頭經過文人加工雅化的模式。而從根本上說,這就是一個巨大的流言。在文體上,《孽海花》一向被視之為社會小說、歷史小說,不過作為從歷史演義、民間說部、傳奇志異向現代連載小說轉型階段的產物,它所具有的當下性新聞要素、傳播方式以及創作理念卻一再顯示出特定時代所具有的流言傾向。曾樸本人通法文,又受到陳季同的指導,熟諳法國文學。在近三十年的時間里,他有系統地翻譯了五十多種法國文學作品,特別是小說和戲劇。他自言:“這書的主干的意義,只為我看著這三十年,是我中國由舊到新的一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內飛也似的進行。我就想把這些現象,合攏了它的側影或遠景和相連系的一些細事,收攝在我筆頭的攝影機上,叫他自然地一幕一幕的展現,印象上不啻目擊了大事的全景一般。”這仿佛是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式的法國自然主義的中國回聲,有學者據此分析《孽海花》的人物形象就具有典型化的特征,更有論者稱曾樸是“中國現代長篇歷史小說的開拓者”,“最早突破傳統歷史小說‘復活’‘歷史’模式,用‘生活史’和‘精神史’形式表現歷史進程”。然而,以世態風俗描繪去展示時代風貌本非舶來之物,中晚明小說于此已經較為普遍,無須法國19世紀小說再來啟發。
就內容而言,無論是褚愛林講述的龔孝琪敘述其父龔自珍的故事,還是云南倮姑演唱黑旗戰史,還是冀東嘴里傳出的臺灣故事……除了正面敘述的雯青、彩云的線索,幾乎旁逸斜出的情節都是口耳相傳的流言,無一不是在筵席歡宴之上、酒酣耳熱之際的消遣談資,固然每每有扼腕嘆息、感慨激昂的議論,袖手空談之后,也就像筵席一樣散去。而即使是作為線索的狀元娘子出使記也不過是個更大的傳說。事實上,《孽海花》全本35回也沒有寫到八國聯軍入侵北京、賽金花舍身救民的情節,但是其后的續書和形形色色的文人作品與口頭文學共同編織了一個“義妓救國”的故事。賽金花與瓦德西是否發生交集,真相固然無法尋得,進而言之,真相也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流言本身就是一種現實。
值得注意的是,曾樸作為一個分裂的敘述主體在《孽海花》中所顯示出來的掙扎:在意識層面,他可能有著婉而多諷的愿望,并且試圖用自詡的結構來約束故事的進程。但是他可以約束筆端文字,卻無法控制現實社會的狂飆突進,作為面向市場的商品,《孽海花》在不自覺地敘述中時常要受到集體無意識的左右,從而為道聽途說、流言蜚語的內容添磚加瓦。這個時候我們很容易產生一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1930-2004)式的感悟——不是小說人物,也不是作者在傳播小道消息、街談巷議,而是故事在操縱者他們,流言本身成為一種力量,左右著傳播群體、圈子、社會場域的話語運行。
流言像歷史一樣長久,不同類型的敘事或多或少都具有流言的性質。古典說部如《三國演義》、《水滸》,固然也有實事的影跡,不過一個年代久遠,一個事實細小,這給了作者較大的虛構轉圜的空間。與《孽海花》同時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老殘游記》等等,卻都具有較強的時效性,每每以正在發生的現實入文。而在小說文體的掩護下,現實又不能真正坐實,捕風捉影、空穴來風容或有之,而流言的特色顯然被放大了。小說本身就是對各種無法證實或證偽的信息的一種分類,這些信息因為敘述而得以在文本(社會之外的另一個空間)里被聚集起來,當它們高度集中的時候,傳播效果要遠遠大于它們分散的時候。信息的非法身份也使人在接觸這類信息時獲得快感,從而更容易接納這類信息。《孽海花》超越同儕的顯豁之處,不僅在于它幾乎是晚清最暢銷的小說,還因為它敘事的野心,涵蓋內容博大、牽涉關系面廣、關系近現代文化轉型最重要的三個話題:性別、知識、國際關系,上至國家存亡絕續,下至市井狹邪艷情,既可窺探宮闈,復又貼近日常人生,遠超過官場腐敗、道德淪喪、社會寫真的層面。
二
緋聞、政治、鴻泥片爪而又充滿誘惑力的外來事物是最易于激發根植于人們內心深處的窺視欲望,前者是愛欲本能(Eros),后者是死亡欲望(Thanatos)和未知事物的渴求。據此,《孽海花》中的流言大致可以歸結為三大中心:放誕美人傅彩云的風流史;以及由此發散開的名士風流,新學、外交、西北地理以及與之相關的國際政治外交;異域的想象與懸想以及凸顯出來的西方形象。這三個話題俱是清末民初這一特定年代的話語集散地,尤能引發廣泛的關注,分別體現了天崩地解時代的性別政治,不同闡釋系統中的知識權力爭斗,東方主義(Orientalism)與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的互動式的文化建構。
1、放誕美人與性別位移
傅彩云的原型賽金花可能是晚清民國之際最有流言價值的“箭垛式”人物,關于賽金花的文學想象與書寫本身就足以構成一部不同主體欲望投射的浮世繪而曾樸則自言雯青的原型洪鈞“為吾父之義兄,同時又為余闈師之師,誼屬‘太老師’,故余當時每稱賽金花為‘小太師母’。”賽金花本人在1933 年答《明報》記者時說:“我幼時與曾樸相識,極親熱,他十分愛我,后來我‘領家’圖錢將我許與文卿了,曾樸當然勢力不抵一狀元,情場失意,遂作小說,憤而罵我與文卿”。這兩人說法俱難以證明真偽,有意味的是,在《孽海花》中傅彩云是被當做一個禍水(femme fatale)來塑造的,這是傳統文學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母題:戲子無義,婊子無情。
彩云似乎是天生淫賤的典型,并沒有體現出太多所謂“現代性”的因素,而更像是體現了人的本我(Id)層面。不過曾樸卻設計了一個“煙臺孽報”的前因來解釋彩云辜負雯青的道德困境:彩云被視作煙臺妓女梁新燕的轉世,雯青發跡之前與梁海誓山盟,梁資助他進京趕考,最后得到的是始亂終棄,憤而自殺。彩云嫁給雯青之后與家丁、瓦德西、戲子的風流韻事,可以說是對于負心漢的現世報。這種設計多少有些詭異(Uncanny)色彩,曾樸在無意間透露出反諷的意思:傅彩云年輕鮮活、蓬勃昂然的生命力與金雯青的自命不凡、昏聵腐朽之間構成戲劇性的張力:當兩人初見面時,雯青像才子佳人小說中的陳詞濫調一樣,款款深情、雙目垂淚;彩云只是像個無知小獸一樣,以職業性的養成習慣勾攏客人、曲意逢迎——原本應該成為解語花的女性這里反轉為惑世的尤物,將經典的古典愛情場景中人物角色行為實行了逆轉和調換。
出使歐洲之行,相比較于雯青的顢頇遲鈍,傅彩云伶俐剔透、艷名高熾,“聯邦帝國大皇帝飛蝶麗皇后、世界雄主英女皇維多利亞的長女”維多利亞第二也聞名已久,將她作為中國美女的代表:
這就是中國第一美女,金公使的夫人傅彩云呀!你們瞧著,我常說她是亞洲的姑婁巴、支那的馬克尼。今兒個你們可開開眼兒了!”維亞太太笑道:“不瞞密細斯說,我平生有個癖見,以為天地間最可寶貴的是兩種人物,都是有龍跳虎踞的精神、顛乾倒坤的手段,你道是什么呢?就是權詐的英雄與放誕的美人。英雄而不權詐,便是死英雄;美人而不放誕,就是泥美人。如今密細斯又美麗,又風流,真當得起‘放誕美人’四字。我正要你的風情韻致瀉露在我的眼前,裝滿在我的心里,我就怕你一曉了我的身分地位,就把你的真趣艷情拘束住了,這就大非我要見你的本心了。”
這里當然有東方主義的視角,但是“放誕美人”形象對傳統文化的無視——并非反叛,如果有反叛的地方那也是無意的,卻恰恰契合了時人們渴望改革、推翻舊制的反叛欲望,公眾對于名流艷史獵奇獵艷之余,無意激發了潛在的脫離現有秩序的共同欲望。
傅彩云完全是遵循著快樂本能生活的人物,充滿實用主義和功利,并且并不以為恥。我們固然可以將之理解為煙花柳巷長大的缺乏教育女子的蒙昧,或者從小見慣弱肉強食的生存環境逼迫下陶冶出來的生存智慧。從另外的角度看,這也未嘗不是一種市民新道德的萌蘗和新女性觀念的鱗爪。統觀全書,我們會發現女性角色占盡風流,從在中越邊境助戰劉永福的女武士花哥,到俄國虛無黨義士夏雅麗,甚至是錢塘江上給學臺祝寶廷下圈套的水妓珠兒,都各呈異彩,而男性角色幾乎都呈現了人性和道德上的負面因素。因為傳統道德的約束范圍實際上并不在這些處于邊緣位置的女子身上,而是男性的專有物,如今他們自己推翻了自己,其中透露出的性別意味有著明顯的傾向性。
2、西北地理、外交焦慮與知識差異
流言的第二個核心元素是雯青的旅行、交游和學術。金雯青是科舉黃昏時代的成功人士,作為當時道德文章典范的狀元,金雯青在帝國傳承已久的知識系統中游刃有余。無論是在科場奪魁,還是官場交際,或是文人雅集,還是花肆尋芳,雯青都是佼佼者。然而“萬國交通時代”已然來臨,知識/權力必然要發生位移。第三回薛淑云(影射現實中的洋務運動鼓吹者、外交官薛福成)請眾人在上海一品香大餐,席間,眾人議論風生,都是說著西國政治藝學。雯青在旁默聽,茫無把握,暗暗慚愧,想道:“我雖中個狀元,自以為名滿天下,哪曉得到了此地,聽著許多海外學問,真是夢想沒有到哩!從今看來,那科名鼎甲是靠不住的,總要學些西法,識些洋務,派入總理衙門當一個差,才能夠有出息哩!”在這里雯青第一次感到了文化震驚和認同危機。
雯青和他的朋友們是占據著要津的京師名貴、舊學名流,他們孜孜埋首于傳統制藝之中樂此不疲,標榜風流文雅,用心經營自己儒雅學士、博古名臣的身份與地位,領導著京師學術文化風氣。這些尚書、學臺、名士、大臣,出于基本的傳統倫理基本都會憂國憂民,然而此時已是五洲十國交通時代,西方文明日新月異,堅船利炮無情地摧毀著他們的思古之幽情、儒雅之風流。但是,如果簡單地以舊人物與新時代、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法來進行劃分也并不妥當,事實上任何時候都是新舊雜呈錯綜于一起,并且雯青這樣的人物也是絕頂聰明,仍然希望迎頭趕上,成為時代文化的弄潮兒。不過問題還是在于空口大言與實際踐行中產生的距離。
十年之后這群人再聚海上味莼園,“如今大家眼光,比從前又換了一點兒了”。談到“大戰國世界”的地緣政治,日本、朝鮮、俄國、中國之間的博弈,外交、公法、練兵、實業、銀行、鐵路、政體、教育、文字、文學……舉凡涉及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都在這幫關心時事的士人的觀照之內。然而侃侃而談的袞袞諸公更多的還是如同晚明士人一樣,袖手空談,止于流言,少有切實的行動,雯青出使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而其關于西北地理的認知也始終沒有走出傳統注釋經典的藩籬,而缺乏現代地緣政治的洞見。
金雯青在不同的文化系統中表現截然不同,在士人宴樂、科舉官場、交往清談中游刃有余,但是一旦離開文化的母體就手足無措、笨拙顢頇。輪船上以催眠術調戲俄國虛無黨人夏麗雅一段就是個開始,自詡風流蘊藉的狀元公使完全應付不了一介平民之女,反倒需要沒有文化的彩云從中斡旋,并且被騙去數額不菲的金錢。諸如此類的受挫一定所在多有,不過小說對于雯青黯淡無光的公使生涯語焉不詳。在傅彩云明艷動人、不可方物的影像之側,金雯青是孜孜矻矻埋首于古籍經卷中的形象——表面上雯青是意識到國家安全和領土權利,換個角度,也可以視作是一種受挫后的退縮以自保心態。
如果說傅彩云以妓女的身份體現了女性、平民在時代變動中的訴求,金雯青則是晚清以降精英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的西北地理考證,正顯示了當時學術界的焦慮和發展路向。王國維論有清一代學術史脈絡稱:“道咸以降,涂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晚清以降,尤其是庚申之后(也就是雯青剛中狀元之時),士人在經世致用理念的感召之下,言西北地理成為一時顯學,如論者所言:“除了治今文外,治西北史地和外國史地也是晚清學術界的風尚。這也和當時講富強的風氣有關。有清一代陸上的外患大抵來自西北,而海上的外患則來自東南。于是晚清學者治西北史地以謀籌邊,治外國史地以謀制夷,這兩門學問遂盛極一時了。”雯青正是此種潮流中的一份子,而他的治學與實踐的轇轕,卻殘酷地顯示了在不同知識系統的斗爭中間,中國舊有闡釋系統的失敗。
小說中有個反諷式的場景:雯青欲從商人手中花重金購買中俄地圖的草稿,彩云認為不過是個爛紙,不值當費錢。雯青卻自鳴得意:“我得了這圖,一來可以整理整理國界,叫外人不能占踞我國的寸土尺地,也不枉皇上差我出洋一番;二來我數十年心血做成的一部《元史補證》,從此都有了確實證據,成了千秋不刊之業,就是回京見了中國著名的西北地理學家黎石農,他必然也要佩服我了。這圖的好處正多著哩!”彩云道:“老爺別吹。你一天到晚抱了幾本破書,嘴里咭唎咕嚕,說些不中不外的不知什么話,又是對音哩、三合音哩、四合音哩,鬧得煙霧騰騰,叫人頭疼,倒把正經公事擱著,三天不管,四天不理,不要說國里的寸土尺地,我看人家把你身體抬了去,你還摸不著頭腦哩!我不懂,你就算弄明白了元朝的地名,難道算替清朝開了疆拓了地嗎?依我說,還是省幾個錢,落得自己享用。這些不值一錢的破爛紙,惹我性起一撕兩半,什么一千鎊、二千鎊呀!”虛圖與實地之間的沖突,展演為雯青彩云之間觀念的差異,似乎是文野的分判,卻是傳統天下理念與現代實用主義的對立。國界邊境這樣的概念也是到現代民族-國家時代才開始,雯青固然有這樣的認識,卻還是囿于既有的迂闊思維之中——實際上,即使地圖本身沒有錯謬,在帝國主義的血與火的暴力入侵中,光憑著文化上的說辭又有何用?
即使雯青沒有買錯地圖,他兢兢業業地做成的《元史補證》除了學術意義之外,對于其所預期的經世致用也遙遙無期,就像他同時代的諸多學者,如小說中寫到的黎石農、何愿船、張舟齋,個個都是西北地理的名家,卻依然不能在國際外交的實際事物中有任何有益的稗助。知識的闡釋系統發生了變化,擁有堅船利炮、科學民主的西方文化成了解釋知識的立法者與主導者,文獻考證的地理學與國界線在實地科學測量和兵戎陳陣的雙重壓力下,顯得蒼白無力。
3、西方的想象與渴慕
作為較多描寫涉外內容的小說,《孽海花》可以說集中地體現了或隱或顯的存在于當時大眾心中對于外來文化的態度。按照雯青出使的實際情形以及關涉中國地緣政治的親疏,《孽海花》主要寫了德、俄、日三個國家。對德國的記敘最多,不但詳細描摹金、傅二人與德人之間的酬酢往來,濃墨重彩于維多利亞第二和瓦德西,還竭力鋪陳自身對德國首都柏林城繁華景致的觀感。對俄、日的描寫則較為簡略,風貌景致只字不提,而以人物為主,前者以女杰夏雅麗為代表,包括其戀人克蘭斯和貴族出身的魯翠等人。后者以小山清之介為代表,包括其兄弟小山六之介、下女花子和宮崎豹二郎兄弟等,分別是俄國虛無黨人和日本浪人。
從敘事時間與實際時間的對比來看,對于出使德國的描寫較之在上海、北京宴會上的高談闊論而言,也是很少的。雯青在這里完全失語,而一向關注地理的他,一路經行,也并沒有留下深刻印象,僅僅一筆帶過:“經過熱鬧的香港、新加坡、錫蘭諸埠頭,雯青自要與本埠的領事紳商交接,彩云也常常上去游玩,不知看見多少新奇的事物,聽見了多少怪異的說話,倒也不覺寂寞。不知不覺,已過了亞丁,入了紅海,將近蘇彝士河地方。”而對于柏林風景的描寫也每每服從于老套的話語系統,不自覺地堆砌習見的陳詞濫調。這種歸化(domesticate,assimilate)的寫法常被后來翻譯研究者詬病,然而恰恰是作為流言的小說的必須——作者無從得知真相,而利用讀者熟悉的套語系統,以其不落實處的文字描述,反而成就了最為肆意的想象;用虛擬的方式,拉近自己與所渴慕而又無緣親赴的西方彼岸世界的距離。
在寫到德國皇后引吭高歌時,唱的德語歌卻是如同《離騷》的歌行體:“美人來兮亞之南, 風為御兮云為騷”。對俄國虛無黨夏雅麗的生平和外貌描寫,對于日本浪人小山清之介兄弟的介紹,都明顯地采用了傳統的史傳筆法乃至修辭慣用語。這是異文化交流中常見的修辭現象,本不足為怪,不過它所顯示的雜交性(Hybridity)帶有怪異的協和,姑且可以稱之為西方主義,不過與東方主義不同的地方在于,這種西方主義帶有強烈的渴慕意味。無論東方主義還是西方主義,實際上都是一個想象他者的過程,并通過界定他者來定位自身。
小山清之介的原型就是在《馬關條約》談判時刺殺李鴻章的狂熱軍國主義分子小山豐太郎,他試圖阻止談判的進行,促使日本將侵略中國進行到底。這種外交上的大事,自然眾口風傳,《孽海花》通過倒敘推衍出墮落的俳優藝人奮而投身到愛國事業中——相映成趣的是梅毒纏身、事業無成的小山清之介因為有報國之念才放棄自殺打算,而準備到中國盜竊機要軍事地圖!夏雅麗更是勇毅果敢的巾幗英烈,為了推翻專制政府,不惜棄愛舍身、蹈死不顧。而瓦德西也是翩翩濁世的少年將軍,更與老朽過氣的清國狀元形成鮮明對比。彩云私通瓦德西這種性上的渴慕與背棄,恰恰反應了背后的政治文化強弱攻守之勢。
較于其他幾部譴責小說以單一的謔笑譏刺手法塑造“他者”,將異國人刻意符號化、平面化的做法,《孽海花》要更勝一籌。但是,顯然它在有意無意間的扭曲和變形也顯而易見。這其實是流言的表征,而在表征的底層則是勃涌聳動的民眾意識。如同有論者言:“異域想象的興起是與晚清社會的種種變化糾葛在一起的,是租界的建設、城市的發展、電影的引進、翻譯文學的勃興、使臣日記的大量涌現等種種合力作用的結果, 它們為想象提供了最初的動力和必備條件。需要注意的是,這之中包含了起承轉合的過程。同時由于深受本國文化的熏陶,晚清小說家向異質文化的接近是有限度的。他們對于西方文明的關注,是以晚清中國社會的實際問題和困境為出發點的,因而他們關注的并非整個西方實體,而只是其中的某些方面。”除了為數不多的使臣、商人和留學生,《孽海花》時代的人們對于國外的了解大多通過上述幾種途徑,而流言無疑是其中最常見的一種。甲午之后,中日俄三國邊界之爭日囂,而彼時知識分子赴日留學已經成為潮流——日本在“脫亞入歐”之后,已經成為西方世界在東方的代言人,而俄國在1917年之后則成為先進道路的典范。由此也可見,《孽海花》與當時現實間極為密切的關聯——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器物模仿到“以夷為師”的制度重建,再到文化上的激進思潮的引進(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短短幾十年間的急劇變化確實已經流播于眾口、彌散于人心。
三
《孽海花》的開頭就是個傳統隱喻的元敘事,虛構一個寓言式的框架:孽海上面的奴樂島,“年復一年,禁不得月嚙日蝕,到了一千九百零四年,平白地天崩地塌,一聲響亮,那奴樂島的地面,直沉向孽海中去。”有個“愛自由者”希望打聽奴樂島的切實情形,被告知天下無處不是奴樂島,并得授卷書,聞聽故事,言說中國也有類似事情。于是決定開始編譯新鮮小說、發布新奇歷史。這種楔子式的引言在古典小說中屢見不鮮,《西游記》、《水滸》都有著相似的原型結構。《孽海花》的新鮮之處就在于起先就營造了一個“陸沉”的意象。沉入孽海的時代焦慮癥,體現了時人亡國滅種的危機感。1904年,奴樂島沉沒,日俄在中國東北部開戰,曾樸接手金松岑開始《孽海花》的寫作。
與晚清許多其他小說相比,《孽海花》成書的過程就足以構成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最早是1903年,金松岑應東京江蘇留日學生雜志《江蘇》之約,寫了《孽海花》前六回,原擬做成時髦的“政治小說”——梁啟超最遲在1898年的《譯印政治小說序》就提出此一倡議,1902年梁開始寫作《新中國未來記》,金著算是政治小說影從云集的一個產物,不過他沒有完成。
1904年,曾樸于上海創辦小說林書社,接手《孽海花》的創作。金松岑原擬的“愛自由者撰譯書”廣告是“述賽金花一生歷史,而內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爾界約事件,俄國虛無黨事件,東三省寧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東京義勇隊事件,廣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國復據東三省止,又含無數掌故,學理,軼事,遺聞。”待到與曾樸商議,計劃更為明確,分為“舊學時代”、“甲午時代”、“政變時代”、“庚子時代”、“革新時代”、“海外運動”,打算寫60回,囊括清末30年的重要事件,以啟民智、覺民心、鼓民力為旨歸,就像小說第一回篇末贊詩所謂:“三十年舊事,寫來都是血痕;四百兆同胞,愿爾早登覺岸!”——“陸沉”的恐懼使得作者希望中國能自拔于沉淪的悲劇。
這個龐大的計劃注定了小說將成為一個漫漶無邊的流言——盡管曾樸本人閱歷豐富、交游廣闊,身經體驗的現實畢竟限于一己之視野,更多的來自耳聞目睹的材料敷衍編排。當其時,整個中國社會中多重文化體系與文化判斷標準之間相互對抗、彼此影響,激發了個人和群體的離心傾向,先進知識分子不由自主地要疏離、掙脫傳統觀念、思想、制度的束縛,而一時之間又難以形成定于一統的價值體系。所以,各種觀念思潮必然如同雜然爛漫的流言一樣飄蕩在傳媒的公共空間。
此際的歷史小說的宗旨主要是開民智、振民氣,小說家常以強烈的政治功利性超越歷史以表現歷史,實現對民族民眾的啟蒙。但啟蒙主體本身其實也時常處于觀念的碰撞之中,折中調和之后反倒成了最為平庸的路人之見,“這書寫政治,寫到清室的亡,全注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寫皇家的婚姻史,寫魚陽伯、余敏的買官,東西宮爭權的事,都是后來戊戌政變,庚子拳亂的根源。”這樣的歷史觀念其實是流言的歷史觀念,在啟蒙理性的歷史哲學尚未成為主流、進化論的線性歷史以及因果鏈條還沒有成為世人的常識,這種古已有之的紓解現時焦慮和歷史緊張感的認知模式就一如既往地發揮著作用。
小說情節起始,庚申之變不久,士人云集京城大談富國強兵之道,到法、越南疆啟釁時節,京朝士大夫企慕曾、左功業,人人歡喜紙上談兵,更成了一陣風尚。雯青坐鎮江西學政之時,正是1885年越南戰事不久,在花哥演唱戰史的幻想同時,并置的是雯青對于巡撫小姐的心猿意馬。而主人在慷慨激昂、涕泗橫流的悲壯戰史表演之后,輕輕一句“請君且食蛤蜊,今夕只談風月”,就將民族悲壯歷史輕飄飄一轉為助興的閑言。寫到清流黨一以貫之的毛病: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到最后歷經龍漢劫灰、幾起幾落,改名曹夢覽的滬上名妓接待過清廷士子、達官新貴、商界大亨、革命黨人,在溫香軟玉之傍,軍國大事都做佐酒佳肴;民族成敗也不過喚取紅巾來一揾英雄之淚。
諷刺自然是有的,然而只不過是信手拈來,控制文本行進的是流言自身的結構以及流言話語的社會互動。在社會動蕩不安、輿論控制削弱、官方權威喪失、群眾心理焦慮之時,流言無疑是大多數不自覺選擇的一種緩解壓力的宣泄渠道。因而作者不過是參與了流言增生中的一個程序,大眾對于流言的消費渴求則是其源動力。近代以來已經形成了相對于官方而言獨立的報刊雜志作為公共領域的代表,與官方的意識形態競爭,并常常拂逆或左右官方的意志,同時也成為超越親緣、地緣的聯系網絡與對話關系,而且形成一種聲氣相通的“想象共同體”,原先對事情的零星反應透過報刊而形成了集體輿論,它們所產生的影響廣泛而復雜。作者曾樸不過是“特緣時勢要求,以合時人嗜好”,將原本星散于人口的流言整合、放大、打磨并定型。
流言不惟記錄過去與當下,更有對現實有意無意的曲解,對未來或多或少的預言的傾向。目前對于流言進行研究的主要有三種:用功能主義的方法進行研究流言的格拉克曼(Max GlucKman)認為,流言蜚語是一個由文化決定并進行傳遞的過程,是一種社會事實,具有約定俗成的規則和重要的功能,有助于維系群體的統一、道德和歷史。流言的本質是借助公共傳統的預期,不斷地(非正式或間接的)從負面對行為進行評價和判斷。而且,流言有助于群體控制其內部相互競爭的小群體和野心勃勃的個體。通過流言,那些原本隱藏在幕后(含沙射影、模棱兩可和自以為是)的不同意見得到釋放,從而能夠維持表面上的和諧與友誼。最后,流言是作為群體成員的一種標志和特權,甚至是一種責任,是群體在進行流言蜚語,它是群體的所有物,成為其中的一員就是要傳播(關于其他成員的)流言。羅伯特·潘恩(Robert Paine)對流言進行溝通主義的分析,認為流言應當被理解成個體運用文化規則的一種手段,傳播流言的個體具有相互爭奪的利益(權力、友誼、網絡、物質),他們需要對此進行推進或保護。在進行流言過程中,其對象并不是群體的價值觀念,而是別人或他們自己作為個體的野心。簡而言之,流言允許道德秩序屈從于個體的意圖。這是一種功利性的行為,通過某種非正式的交流造成局部影響,個體在有選擇地參與、遏制、利用信息的過程中進行爭斗。象征互動主義(Haviland,Heilman)關注的則是,社會現實和社會關系如何通過日常交談不斷地獲得表述和爭辯。在流言蜚語中,個體可以看作是在主動地推測他們的生活和世界的本質。所以,流言為個體提供了一幅關于他們社會環境的圖景,也提供關于正在發生的事件、當地人和他們的地位的當前信息。根據這些資源,他們可以制定出行動計劃。流言也是個體協調行動的手段:在他們自己中間協商文化規則的范圍和側重點,并決定采用怎樣的社會行動。流言本質上是一個內在的溝通過程,通過它,個體在一起檢驗并討論他們共同生活于其中的規則和習俗。此外,由于規則在運用中具有相對性和模糊性,這種解釋永遠都不是最終的結論。因此,流言每時每刻都在瓦解、評價、重組日常世界。
從社會學方面對謠言和流言進行研究的學者認為,流言作為恒久的社會現象,無論是“過于有序”還是“過于無序”的社會都會促使人們選擇它,它往往使人們以言行事的能力進一步受限,進而在“言”與“行”兩個向度之間形成一種更強大張力,當達到一定的臨界點時,如出現極權或暴亂,心靈和世界(社會)間嚴重失衡,與此同時人們以言行事能力卻被進一步削弱,這時候謠言就成為一種有效的平衡手段。
以上諸種說法幾乎都可以在《孽海花》的文本及傳播中找到對應之處。流言這種根植于人性深處而又活躍互動于現實處境的現象和特性,其生產、傳播、消費、影響中更進一步證實了虛構與現實、書寫與實踐之間彼此相互為用。《孽海花》的寫作時常因為現實的變故中斷,曾樸在1904年用兩個月完成了20回,其后經歷辦刊、譯介、立憲、入幕、為官,直到1927年重新創辦“真善美”書店,并出版發行《真善美》雜志,到了1930年,《孽海花》才斷斷續續連載到35回,還沒有結束。而早在1907年的時候,就有包天笑未完的續書《碧血幕》在《小說林》刊載,陸士諤《續孽海花》共六編陸續問世,此后還有張鴻(燕谷老人)60回的續本。不過,后者圍繞的是賽金花的故事,實際上人為縮小了原著流言的內核,因而影響也就遠遠不及原著。而其寫作到發表的1904到1930年的幾十年,正是中國易代之際、軍閥混戰、黨派紛爭,現代新聞出版、輿論管轄最懈怠的時期。以此種淆亂不堪的社會為底色,形形色色的流言大行其道。與《孽海花》幾乎同時出現的另外幾部著名的小說《老殘游記》、《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都有著這樣的流言式結構與內容。
《孽海花》沒有結局——事實上作為流言它也不可能有結局——它所書寫的種種核心流言在日后也一再流布展演,直到發生變異。《荀子·大略》言:“流丸止于甌臾,流言止于知者。”其實,流言并非止于智者,流言只是止于流言自身在行進中被證實或者證偽。如今,《孽海花》中的中外關系、西北地理、外國想象都已經不再是流言的主體,而賽金花這樣的“紅顏禍水”卻一再顯示出其恒久的流播價值,是否表明階段性的政治、外交乃至知識、制度都已經發生了變異更新,而性別話題依然葆有了20世紀初就誕生的一些問題沒有解決呢?
注:
① 魯迅《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305頁。
② 西方文學中的Novel也是一個直到18世紀后期才正式定名的文學形式,此前用“散文虛構故事”(fiction)來加以稱謂。在這個文體嬗變的過程中,現實主義美學和大眾讀者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參見[美]伊恩·P·瓦特(Ian P.Watt)《小說的興起: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研究》,三聯書店1992年版。
③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三聯書店1994年版)在 “小說文體的孕育”一章中敘其脈絡至神話、史傳、諸子散文。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的本體和文體發生發展的流變,持相似觀點,將小說產生發展的源頭概括為:子書、神話、史學三大母體。
④ [法]讓-諾埃爾·卡普費雷(Jean-No·l Kapferer)《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頁。謠言的政治色彩比較濃厚一點,從中國古代的讖言到如今在互聯網上流傳各類謠言莫不如此,相關研究,見丁鼎、楊洪權《神秘的預言——中國古代讖言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美]奧爾波特(Gordon W. Allport)等《謠言心理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美]卡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謠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⑤ 卡普費雷區分了法文中謠言(rumeur)、閑話(potin)、傳聞(bruit)、流言(ragot)、流言蜚語(commerage)這些詞的差異,流言是作為信息的一種,成為一種謠言或傳聞內容的主觀判斷。中文的“流言”則含義要更為豐富,在不同的場合、語境中分別具有上述詞語包涵的意義,無法在英文或者法文中找到對應詞。見讓-諾埃爾·卡普費雷《謠言:世界最古老的傳媒》,第18-20頁。
⑥ 董叢林《晚晴社會傳聞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的。
⑦ 《孽海花》從報刊連載到成書,經歷改變作者、寫作中斷等事故,拖延時間長,且版本繁復,本文第三節將加以論述。因為版本之間的文字差別不影響本文論述,所以凡所引《孽海花》文本皆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整理版本,此后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