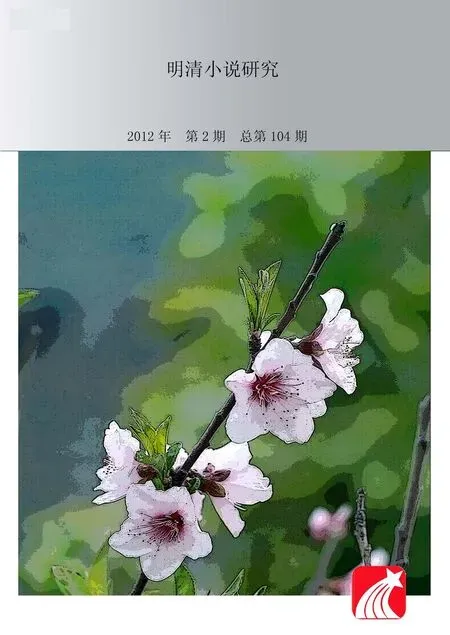再談陳森生平著作的若干問題
· ·
刊登在《明清小說研究》2011年第1期的《也談〈品花寶鑒〉的成書年代——兼論陳森的生卒年》(以下簡稱“《也談》一文”),對《品花寶鑒》成書年代的推論較之前人研究有了更為令人信服的說法,并且首次介紹了王拯創作于咸豐七年(1857)的《追悼陳上舍森嘗為〈石函記〉傳于時者》一詩,將陳森的卒年較為明確地考訂為“不遲于1857年”,這不失為近年來陳森史實研究中的一大亮色。但是,由于相關資料有限,對于陳森生平及創作相關史實的進一步認知,還有待于研究的繼續深入。因此,筆者不揣谫陋,就陳森生平著作等方面的一些問題撰成小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生年考
受資料限制,迄今為止,學界關于陳森生年的推論,多猜測之說。《也談》一文對生年的考證依據與尚達翔《說〈品花寶鑒〉》完全一樣,皆為陳森的《品花寶鑒自序》(以下簡稱《自序》)。陳森在文中提到,自己在“年且四十余”之時放棄了科舉考試。而上述兩文都將道光十七年(1837)視作陳森最后一次參加科舉的時間,由此得以推算出陳森的生年。只是,尚達翔得出的結論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左右①,這一令人費解的結論不知是否由年代計算上的失誤所致?《也談》一文則將其更正為嘉慶三年(1798)左右。但是,這一結論因為未能參考《梅花夢》傳奇中的相關表述,而讓人遺憾其未能得到進一步的考查與驗證。其實,嚴敦易早在《陳森的〈梅花夢〉》一文中,即已根據《梅花夢》男主角張若水的年紀,進而推算陳森的年紀:張若水在《梅花夢》中的出場年齡是十五歲,幾年后在北京遇見陳森時,應在二十歲上下。張若水“愿執弟子禮以學詩,年差少余,抑抑自下”,因此推斷陳森年紀稍長于張。照此推論,張若水的生年應為嘉慶八年(1803)前后,陳森的生年應在嘉慶五年(1800)前后。而嚴敦易的結論卻是陳森生于嘉慶元年(1796),這與上述尚達翔的推論同樣令人費解。但是,嚴敦易的考證過程,較之前兩種推論,顯然更加周密。
陳森的《梅花夢事說》(以下簡稱《事說》)一文撰寫傳奇本事甚詳,指出《梅花夢》敷演的是無錫張若水與妓女梅小玉的一段真實的悲歡離合故事。陳森透露,男主角張若水在現實中“年差少余”,且在后文中對張若水幾段經歷言之甚詳:時間、地點及人名皆言之鑿鑿。又,張若水曾作《梅花夢》七律十二首呈陳森,因此,《事說》及《梅花夢》傳奇中的記載無疑是帶有強烈紀實意味的。退一步說,即使張若水其人也是陳森的假托或虛構,但從《梅花夢》中一些涉及年齡的細節中也可考察作者陳森的一些真實情況。《梅花夢》屢次提及故事發生時張若水的年齡為十五歲。如《蕩湖》出,船妓詢問張若水:“相公妙齡多少?”張答道:“十五歲”。《顧曲》中則謂:“癡兒女,正十五青春稚嬌。”陳森又指出:張若水在梅小玉病逝后“意索然,郁郁居鄉者數年……束裝游清江者復數年。于道光壬午至都門”。在梅樹下夢見玉奴,玉奴笑問他:“時隔十二稔,何遽忘之耶?”嚴敦易在此前的論述中并未注意到張若水流寓北京的時間已然明確給出了,即道光二年(1822)壬午。且其時相距張、梅相識相戀的時間已有十二年。由此可以確切知道,1822年張若水二十七歲,則其生年當為嘉慶二年(1796)。陳森既言稍長于張若水,不妨假定其年長張一至四歲,則其生年當在1792至1795年之間。又據《自序》中道光十七年(1837)時陳森“年且四十余矣”,并參考《也談》一文推斷陳森生于1798年前后的話,則筆者認為以目前所掌握的資料而言,將陳森的生年認定為1795年左右會更為合理一些。
二、《石函記》為什么就是《品花寶鑒》
《也談》一文在引用王拯《追悼陳少逸上舍森嘗為〈石函記〉傳于時者》時,認為陳森既在《品花寶鑒》中署名“石函氏”,因此《石函記》就應該是《品花寶鑒》。如此推論略嫌簡單。由于無法確知陳森自稱“石函氏”始于何時,而根據“石函”二字中暗含著的“玉”字,是否也可以將《石函記》認為是《梅花夢》的別名呢?如嚴敦易在《陳森的〈品花寶鑒〉》中即指出:“這里還有一個有興味的問題,本劇女主角名叫梅小玉,而《品花寶鑒》的男主人公,則名叫梅子玉,兩個名字中間,有無聯系用意?正自難說。我頗有點疑心《梅花夢》或竟是作者自道之作,張若水即是他本人的化身,故《事說》所記甚為惝怳。”照此分析,《石函記》也極有可能就是頗具自傳色彩的《梅花夢》。因此,還需通過對于王拯詩歌的深入解讀,探究《石函記》的真相。詩曰:
東風三百梨園隊,天寶當年樂未涯。璧月樓臺空色相,采云歌管左風懷。搜神干寶才難盡,荷鍤劉伶恨豈埋。昔日龍城曾記錄,雨余陰火散秋齋。
如果說從首聯可以大致推測作品的題材是摹寫梨園情狀的話,那么頷聯“璧月樓臺空色相,采云歌管左風懷”中所用到的“左風懷”一典,則為指實《石函記》為《品花寶鑒》提供了有力的證明。“左風懷”語出宋代晏殊的《類要》,其義據元代方回的解釋:“男為左,女為右,今取此義以類。凡倡情冶思之事,止于妓妾者流,或讬辭寓諷而有正焉,不皆邪也。其或邪也,亦以為戒而不踐可也。”②因此,“左風懷”實際上就是男風的代名詞。在宋代以降的文學創作中,不乏引用者。如,元代滕賓《瑞鷓鴣·贈歌童阿珍》:“分桃斷袖絕嫌猜,翠被紅興不乖。洛浦乍陽新燕爾,巫山行雨左風懷。手攜襄野便娟合,背抱齊宮婉孌諧。玉樹庭前千載曲,隔江唱罷月籠階。”③清代孫擴圖《吊故友鄭板橋》中有“平生痼疾左風懷,翠被春寒亦復佳”句,并自注云:“古以男色為左風懷。”④因此,王拯一詩實際說明了《石函記》是一部描寫梨園人物與男同性戀的作品,《梅花夢》因為敷演的是才子佳人的愛情故事,首先被排除在外了。而《品花寶鑒》的主題既在于品評伶人,又在于摹畫狎優、同性戀的種種情狀,與《石函記》主旨格調倒是極其吻合,因此筆者認為《石函記》應為《品花寶鑒》的另一題名。詩歌末尾所言“昔日龍城曾記錄”,“龍城”指王拯的故里柳州。這說明了《品花寶鑒》在柳州亦受到了傳抄與追捧。這一情形無疑也驗證了《自序》及《羅延室筆記》中關于該書傳播情況的介紹。
三、陳森,亦名“森書”
關于《品花寶鑒》作者的姓名、字號,在研究中曾引起關注的是:“森書”的“書”字是否為衍誤?魯迅在著《中國小說史略》時,言《品花寶鑒》作者為常州人“陳森書”。1932年8月15日,魯迅致臺靜農信中說:“上月得石印傳奇《梅花夢》一部兩本,為毗陵陳森所作,此人亦即作《品花寶鑒》者,《小說史略》誤作陳森書,衍一‘書’字,希講授時改正。”⑤這一說法影響頗大:趙景深引述了魯迅的這一修訂:“(《品花寶鑒》)作者是陳森,……普通作陳森書,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一九三○年改訂本)因為作者的手稿《梅花夢傳奇》上自署毗陵陳森,以為‘書’字或許是誤衍的。”⑥嚴敦易也在《〈梅花夢〉與〈品花寶鑒〉》⑦、《陳森的〈梅花夢〉》⑧兩文中,支持了魯迅的推斷,認為魯迅關于“書”字乃衍誤一說證據確鑿。周紹良在《〈品花寶鑒〉的成書年代》中,則以清代常州人莊縉度的《題〈梅花夢〉樂府,為采玉山人陳森賦》為據,同樣認為陳森為單名,“書”乃“書寫”之意,與名無關。⑨在諸如《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中國古代小說總目》、《中國古代小說百科全書》等辭書及絕大部分的個人著述中,《品花寶鑒》的作者均作“陳森”,而“森書”一說則被認為是錯誤的記載。細讀魯迅與嚴敦易的相關論述文字,均未提及“陳森書”引自何種文獻。清人楊懋建在《夢華瑣簿》中的著錄是“常州陳少逸”⑩。近人崇彝的《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也著錄作“陳少逸”。而“森書”一名的記載則出現在清無名氏《羅延室筆記》中:“高品者,即陳森書,常州名士,即作《品花寶鑒》者。”另外,徐珂《清稗類鈔》云:“高品為陳森書,即作書之人也。”魯迅所引“陳森書”,也許就是根據《羅延室筆記》,或者《清稗類鈔》。其實,魯迅在1932年依據《梅花夢》傳奇的署名,對前說做出修正,的確體現了其治學態度的嚴謹。不過,當一些史料仍然處在沉睡狀態中,未被喚醒,研究者窮究的歷史真相就不會輕易顯現。近日,筆者閱讀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刻本《香南居士集》時,發現其中有作于道光十八年(1838)的兩首詩:《喜晤陳上舍森書復言別》與《立秋日領客普照寺因與陳子話別》。詩集作者為覺羅·崇恩(1803-1870),字仰之,號語鈴、雨舲,滿洲旗人。富收藏,精鑒賞、工書畫。官至山東巡撫。1838年,任泰安知府的崇恩,與自京師南歸途中的陳森相見于泰安,并作此二詩紀念。第一首詩題中的“上舍”在清代往往用來指代秀才或者未得功名的讀書人,“森書”兩字在原本中以小號字出現,說明確系人名。那么此處的“陳森書”是否就是《品花寶鑒》的作者陳森呢?浙江圖書館善本閱覽室藏崇恩所著《枕琴軒詩集》抄本(殘本),扉頁有陳森的題詩,并附跋:
道光戊戌六月,自考南歸。道過泰安,即謁雨舲太守大人。欸留信宿,并見示《枕琴軒詩集》。敬題一律呈教,時六月十八日,黎明微雨,雷聲殷殷繞戶。鄉夢乍醒,疑已驅車于亂石巉巖間,不知猶宿山墀逆旅也。石函陳森書。
如果說陳森跋文的署名“陳森書”仍然容易引起誤會,以為“書”乃“書寫”之意的話,那么據跋文中提及的時間、地點、人物皆與崇恩兩詩中所敘事件吻合的事實,則完全可以確定崇恩《喜晤陳上舍森書復言別》中的“陳森書”就是陳森無疑了。因此,陳森,又名“森書”,“書”字絕非衍誤。
四、《梅花夢》的創作時間
自《品花寶鑒》進入現代研究視野以來,對其成書年代的激烈討論一直持續著。相對而言,《梅花夢》的創作時間因為有《事說》一文的詳盡介紹,學者只需徑采其中說法即可,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嚴敦易、尚達翔等學者就一致認定《梅花夢》創作于道光三年(1823)八月。近年出版的多種戲曲史編年著作,皆采信這一說法。筆者之所以贅述這一問題,一方面是希望陳森的創作史實能夠被準確描述,另一方面也希望借助于考證《梅花夢》的創作時間,從而更清晰地把握《品花寶鑒》的創作心態與創作語境。據《事說》記載:
道光癸未,余游京師。有同郡錫山張生,名若水……曾有記《梅花夢》七律十二首,請余改正,并為序。余以旅況窮愁,久置筆硯,未應也。今春,授徒于故大司馬汪宅,日長炎炎,無以消夏,因制此曲,即名曰《梅花夢》……余素不解音律,亦不好聞歌吹聲,率爾為之,未半月而就。……時八月十二日,采玉山人陳森少逸甫書于都門汪氏之“退逸居”。
根據上述引文,筆者認為《梅花夢》的創作應在陳森入京翌年,即道光四年的夏天,而非道光三年的八月。原因如下:
首先,據原文,“道光癸未”只可視作陳森入京的年份,文末所署“八月十二日”只可視為寫作《事說》一文的月日。細讀該文,在“道光癸未,余游京師”后,緊接著又出現了另一個有關時間的記載,即“今春,授徒于故大司馬汪宅”。依照上下文意的承接與表述的習慣,“今春”所指的年份與“道光癸未”之間,應存在一定的時間間隔,若理解為同一年,顯得有些勉強。
其次,據南京圖書館藏民國影印道光手稿本《梅花夢》扉頁的張盛藻題記:“此《梅花夢傳奇》稿本,道光四年間京朝諸名公有題詠。”劉承寵所作《梅花夢序》在卷首,注明寫作時間為“道光四年六月”。卷末題辭的有吳企寬、劉沅、孫昭等人,而在書寫順序相對靠后的江少泉題辭,亦注明了時間,為“道光四年嘉平”,即該年十二月。因此,可知上述序跋題詠確系作于道光四年。又,細讀各人題詠,多指明此《梅花夢》為新近創作完成的。如劉承寵序中有“妙得新聲”句;吳企寬有“新聲合奏梨園部”;劉沅有“梨園解譜新詞”;孫昭亦言“三疊新聲奏綺筵”。據此,筆者認為《梅花夢》作于1824年,而非1823年。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根據陳森自述,在炎夏中花半個月時間即完成了傳奇創作,而劉承寵《梅花夢序》的出現也是夏季的六月,可以想象,《梅花夢》在完成后的第一時間就已在陳森的好友圈中傳播了。因此,就傳奇文本的流傳而言,并不像他在《自序》中所說的將其擱置、略不在意。而《梅花夢》的創作及流播實可看作是《品花寶鑒》創作及流傳的一場預演。
再次,依嚴敦易等人所論,《梅花夢》作于1823年八月,則與陳森自敘創作動機之一“日長炎炎,無以消夏”兩相矛盾了。農歷八月已是仲秋時節,而考慮到北京所處地理位置,以“日長炎炎”形容其時天氣是頗不可能的。筆者另有一推測,即陳森道光三年入京,很有可能是為了參加該年舉行的順天鄉試,八月十二日正該是入闈應試的關節。落榜后,依舊滯留京城。并于道光四年春,在“同里汪氏退逸居”謀得館席。至夏,以閑暇時間作《梅花夢》傳奇。關于《梅花夢》的創作,還有一個細節應予關注,即該傳奇的創作分前后兩期。初成始得十六出,此即《梅花夢》最后一出《顧曲》中所說的:“譜成傳奇一部,得十六回,名曰《梅花夢》。……竟是文不加點、隨筆隨口,半月即成。”而至陳森八月十二日作《事說》時,《梅花夢》已增加至十八出。后兩出的創作,《顧曲》中也有所交代:“閱者憐你我苦情,不見完聚,雖有江上峰青之妙,未免凄楚些兒。故又力爭一回以《完約》作結。”又,梅小玉白:“張郎,我想十七回是單的,何不將我們今日批判的話兒添上一回,改作十八回,也可算我們是山人文章知己了。”很明顯,《梅花夢》的創作前十六回是一氣呵成的——“半月即成”,后兩回則是根據讀者的意見分別加上的。陳森撰《事說》在劉承寵六月作序之后,就不足為奇了。與《梅花夢》在創作過程中存在著作家與讀者之間的頻繁交流情況相似,《品花寶鑒》也是一部被讀者的閱讀期待持續影響著的作品,正如陳森在《自序》中所說:“某比啟余于始,某太守勖余于中,某農部成余于終,此三君者,于此書實大有功焉。”透過陳森兩次創作過程中的共同現象,既可以感受作者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的創作心態,也可以深味以處館、入幕為業的陳森在選擇創作體裁上的不由自主,同時也得以玩味陳森在創作中的游戲人生之意味。
注:
① 尚達翔《說〈品花寶鑒〉》,《明清小說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匯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76頁。
③ [清]張宗棣編《詞林紀事·詞林紀事補正:合編》(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9頁。
④ 轉引自卞孝萱《鄭板橋交游考》,《學林漫錄》第十六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29頁。
⑤ 魯迅《魯迅書信》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319頁。
⑥ 趙景深《〈品花寶鑒〉考證》,《中國近代文學論文集1919-1949小說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頁。
⑦ 嚴敦易《〈梅花夢〉與〈品花寶鑒〉》,《通俗文學》第三十七期,轉引自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6頁。
⑧ 嚴敦易《陳森的〈梅花夢〉》,《元明清戲曲論集》,中州書畫出版社1982年版,第341頁。
⑨ 周紹良《〈品花寶鑒〉的成書年代》,《紹良文集》上冊,北京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31頁。
⑩ [清]楊懋建《夢華瑣簿》,轉引自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