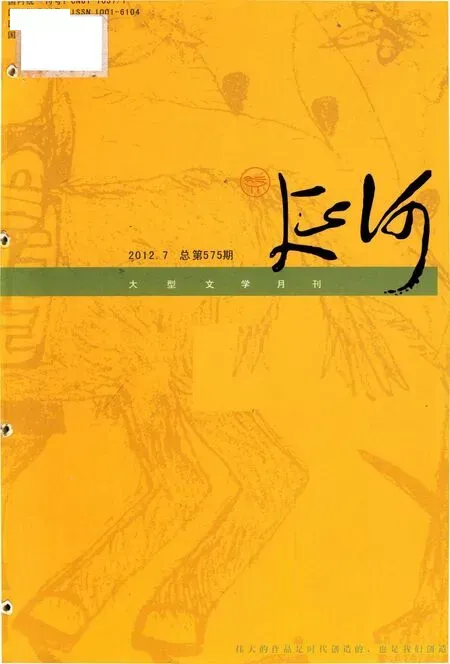那些關于歲月的記憶
衛尚科
“老一井”感懷
黃土高原,延河之濱,延長城西,石油希望小學院內坐落著“中國陸上第一口油井”——“延一井”。被譽為中華之最的“延一井”有稱“老一井”。我曾無數次來到“老一井”前,或陪領導視察,或陪遠方的朋友留影,或帶領新工進行傳統教育,或攜兒帶妻去尋訪……每次站在“老一井”前,猶如與百歲老人對話,與同代朋友交流。一幅幅畫面浮現在腦海,一段段故事縈繞在心頭。
站在“老一井”前,我仿佛看到了東漢的班固、北魏的酈道元和宋朝的沈括,雖說他們生活的年代相差了上千年、數百年,雖說他們穿著不同朝代的服飾、為不同的當政者效力,雖說他們堪察的時間不同、方式各異,但在他們的著述中,共同的都記錄了陜北境內有一種肥而可燃的液體,沈括老先生大膽地命其曰:“石油”,并預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這是多么偉大的預言啊!
站在“老一井”前,我仿佛看到清朝末年國家內憂外患、民不聊生的慘敗景象,八國聯軍打破國門,覬覦延長石油,當地人民英勇反抗,開明官吏積極奏請朝廷,打破了帝國主義掠奪延長石油的美夢。一百年前臨近歲末的一天,陜西巡撫曹鴻勛捧回“圣旨”,指派候補知縣洪寅為“總辦”,1905年便掛起了“延長石油官廠”的名牌。洪候補受命不可怠慢,外請技師搞堪察,內籌資金修馬道。一時間,金鎖關至延長展開了筑路大會戰,多少土工輪镢揮鎬夜以繼日流血汗,無數石匠輪錘把橇沒明沒黑連軸轉。費時一年,總長500余里的馬道便修通了,這在條件極為惡劣、機械設備極為簡陋的當年,是多么的不容易啊!
站在“老一井”前,我仿佛回到了1907年那個不同尋常的秋天,臥牛山的丁香樹綠里透黃隔著延河把手招,西灘洼的糜子、谷子笑彎了腰,延河、西河歡歡喜喜把歌唱,縣城居民奔走相告涌出西門看熱鬧:由日本技師佐藤彌市郎定位并偕工匠、機器歷經數月鉆探的油井出油了!這就是“老一井”即“延一井”。它的鉆成投產,結束了中國大陸不產石油的歷史,填補了中國民族工業的一項空白。從此,中國石油從這里流到玉門、大慶、大港……啊!“老一井”,你是中國石油的先驅,你是中國人、延長人的福芷,延長的山水為你的誕生而歡呼和歌唱,延長人民為你而自豪和驕傲!
站在“老一井”前,我又仿佛看到60年前從延安邊區政府領獎歸來的石油廠廠長陳振夏走來,他穿著深灰色粗布廠服,胸前戴著大紅花,手里捧著毛澤東親筆題寫的“埋頭苦干”粗布字幅,他步履輕盈,面含微笑,在一片歡呼聲中,向工人弟兄們展示了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親筆簽署的獎狀,他異常激動地向大家介紹了表彰大會的盛況,介紹了毛主席接見和題詞的經過,號召職工“埋頭苦干”,多產石油,支援前線。頓時群情振奮,歡聲雷動。“埋頭苦干”既是對延長石油人的褒獎,更是對延長石油人的期望。60年來,延長石油人發揚“埋頭苦干”精神,使企業不斷發展壯大,為老區的社會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埋頭苦干”將永遠激勵我們開拓前進!
站在“老一井”前,我聆聽著1953年榮獲陜西省勞動模范模的武志忠講述他當年參加工人支隊保衛延長石油廠的故事;站在“老一井”前,我看見油礦老領導劉生連踏著冰雪從延河向半山腰的鉆機擔水的身影;站在“老一井”前,我聽到1956年榮獲全國先進生產工作者的董存秀正在向勞模朋友介紹“三勻一快”的鉆井經驗;站在“老一井”前,我看見孟四海、王景芳、徐林、姚宏亮、屈興財、徐京科等一大批新老先進在各自的崗位上辛勤工作著,我看見數以萬計的當代延長石油人奔波在千里油區鉆井、壓裂、安裝、采油……偉大的延長石油工人啊,“老一井”不會忘記你,人民不會忘記你,歷史不會忘記你!
站在“老一井”前,我聽到了延長油礦年產原油突破萬噸、十萬噸、百萬噸、三百萬噸……大關時喜慶的鑼鼓聲和鞭炮聲;我看到了成千上萬延長石油人歡慶勝利的笑臉和歡快的舞姿。一百年前,我們從這里出發,揚帆破浪、一路高歌,艱難跋涉、從不退縮。油礦在先輩們雙手捧起的油苗中由小到大,企業在一代代石油人開拓進取中由弱變強。我們生產的煤油、石蠟點燃了延安土窯洞的燈火,點點燈火燎原了神州大地,照亮了全中國。我們的產品驅動著奔馳的火車、汽車和輪船駛向現代化的彼岸,我們創造的財富使老區脫貧、使國家強盛。我們自豪,我們驕傲,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啊!“老一井”,多少石油人把你神往,多少從你身旁走出去的人把你魂牽夢繞。你是歷史的見證,你是老礦人的驕傲。作為老礦的傳人,我們將繼承和發揚老礦傳統,以更加輝煌的業績給老礦增光,為“老一井”添彩。
逝去的老家
往年放了假,我的第一個任務便是回老家,因為那里有年邁的父母期盼著我的歸來。今年放了假,我卻遲遲下不了回家的決心,因為父母先后都已“上山”,失去了回家的動力,回不回都無所謂。在我看來,沒了父母,便沒了真正意義上的老家。
小時候,我的家里很窮,吃的大多是粗糧,穿的是母親縫制的粗布衣,鋪的是羊毛氈,蓋的是破舊的棉被。然而,在我的記憶里,那是一個充滿歡樂祥和的家,生活雖然拮據,但過得很舒坦。哥哥們在外工作的工作、上學的上學,在家務農的也因為隊上的農活忙,也很少團聚。白天,父母去隊上勞動,我到村里的小學上學。晚上摸黑吃過晚飯,我趴在油燈下看書寫字,雖說燈光很暗,但學習的勁頭卻很足。父親靠在被卷上翹著二郎腿,手執永不離手的旱煙鍋一邊抽煙,一邊瞇著眼想心事,一幅悠閑自得的神情。母親坐在紡車前,一手搖車,一手抽線,動作嫻熟,姿態優雅,影子打在對面的墻上,猶如一幅美妙的圖畫,紡車節奏均勻,快慢有致,猶如在演奏一首美妙的樂曲。寫完自定的作業,我便鉆進被窩,一會看看默默無語的父親,一會豎起耳朵聽聽優美的紡車聲。我心想哪一天才能長大,象四個哥哥那樣飛出這個家,上學、工作、贍養辛勞一生的父母。不知不覺便進入了甜蜜的夢鄉。
星期六下午,在鎮中學上學的四哥回來了,家里的寧靜也便打破了。我跟在四哥身后寸步不離,問他一周所見到聽到的大事、小事,我給他說村里、學校、家里發生的大事、小事,海闊天空,無所不談。第二天上午,如果是春夏,我們不是在自留地看菜摸瓜,就是到山洼里挖藥材;要是秋冬,我們就上山砍柴,若是下了大雪,我們便去套野鴿、夾山雞。下午,四哥要返校了,母親給他裝上一包圓圓的兩面餅,我依依不舍地把他送出村。
過年,是全家團聚的時候,也是家里最熱鬧、最溫馨的時候。進入臘月中旬,在外工作、上學的哥哥們相繼回來了。全家按計劃攤米黃、做豆腐,磨面、殺豬、做年糕,掃窯、糊窗、貼對聯,一直忙到三十晚上,全家老少十幾口聚集在父母住的窯里過大年。這時的父親,猶如大功告成一樣,悠然自得地仰靠在鋪蓋上,依舊是翹著二郎腿,仍舊是手執旱煙鍋,花白的山羊胡有節奏地上下翹動,嘴角掛著發自甜甜的微笑。母親和嫂嫂們打著馬燈在鍋灶上忙活,準備年夜飯,又是蒸八碗、又是炒菜、又是過米酒,滿屋里蕩漾著濃濃的、香噴噴的飯菜味兒。哥哥們互相拉著家常,無拘無束,自由自在。我和侄兒們更是樂不可支,跑里跑外,歡呼雀躍,看燈籠、放鞭炮,大點的壯著膽子去點鞭炮,其余的則既想看又害怕,鞭炮還未點燃,便雙手捂著耳朵往后躲了,鞭炮炸響了,大伙松開雙耳暢懷大笑了。
有一年,從省城開會回來的大哥,帶回了一瓶燒酒、兩合帶把香煙,拿到父親面前,熱切地說:“大,把煙鍋放下,抽一支這個。”父親接過一支,抽了兩口,笑著說:“沒勁,還不如旱煙,花錢買這干啥?”帶把香煙即過慮咀香煙,在當時算是高檔的奢侈品了,聽說只有中央首長才抽這種煙,在我們那樣偏僻的山村連見也沒見過,更不用說抽了。出于好奇,我們圍了一圈爭著看,父親樂了,“這煙沒勁,叫娃娃們一人耍上一支”,說著給我們男孩一人發了一支。我們接過煙,象得到高貴的獎賞一樣,高興地摸了又摸,聞了又聞。七碟八碗的飯菜做好了,全家圍坐在炕上,吃著雪白的饅頭,喝著香甜的米酒,品嘗著美味的菜肴,話著家常,道著祝福,其情切切,其樂融融。燒酒是極少喝的,在我的記憶里,這可能是第一次,打開瓶蓋,濃烈的酒香四溢,不需要酒杯,從父親開始,依次手持酒瓶抿一口,女人和小孩推托著一般不敢喝。輪到我的時候,禁不住好奇,便象喝水一樣大大地喝了一口,沒有咽下就嗆了出來,頓覺渾身內外發燒,呼吸受阻,很是難受,大人們又好笑又驚嚇,看我沒啥大事,母親安撫我吃了點飯菜,迷迷糊糊就睡著了。平生第一次喝酒,我便醉了。
光陰荏苒,歲月蹉跎。度過貧窮而快樂的幼年,邁進村小學的大門,隨后離開老家上了中學、上了師范,直到外地開始工作,一晃就是十多年。我一天天地長大了,含辛茹苦的父母卻一天天地變老了,雖然距離老家越來越遠了,但對老家的依戀和摯愛卻與日俱增。每到放假,我就迫不及待地擠車——騎車——步行趕回老家,偎依在父母的身旁,感到無比的幸福和踏實。我高興,父母更高興,他們一邊拿出積攢多時的好吃好喝供我享用,一邊絮絮叨叨問長問短,其情其境無以言表。
“相見時難別亦難”,快收假了,我要別了老家,離父母而去了,他們千叮嚀萬囑咐,每次都送上窯坡,目送我走得很遠很遠。這時,我不敢回頭看他們,我知道他們在流淚,我也在流淚。我心想:離開老家,還不如永遠住在老家,守住父母。
幾年后,父親病逝,我們弟兄五個也都成了家。母親在我們兄弟間輪換居住,于是老家的溫馨頓覺褪去了一半。
又過了幾年,母親去世,安葬完母親,我們聚在一起清理父母的遺物,各自分得了一份不值幾個錢卻又非常珍貴的“福”,隨后各回各家。此時,我突然覺得我的老家也隨父母一起遠去了,真正意義上的老家不存在了,我頓時傷感地淚流滿面。
父母去世后,我很少回家,只是每逢年節,偶爾上上墳,掃掃墓。前天,上墳之后,我走進往日紅紅火火的院落,只見荒草萋萋,難以落腳;父母用過的石磨已經坍塌,上扇躺在地上,沒在草叢中,無聲無息;當年徹夜飛轉的紡車,散落在已經坍塌的測窯,上面布滿蛛網和灰塵。我想父親手中的煙鍋也許成了玄孫們手中的玩具了。我不忍心踏進破敗的家門,只是指給遂行的兒子說:“這就是咱們的老家,你記住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