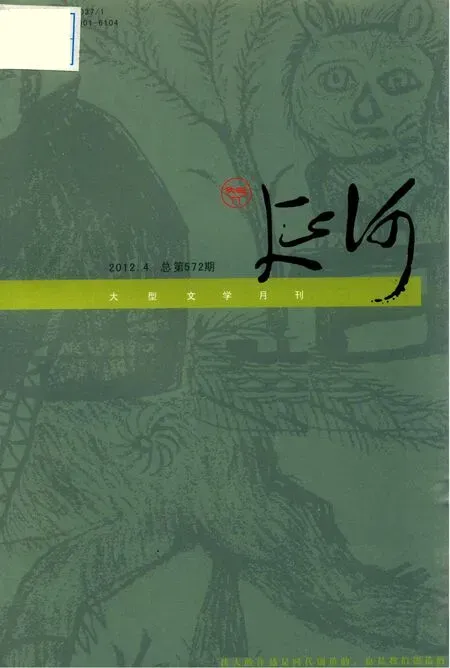關于鄉土中國的觀察與談話
惠雁冰、梁向陽
當下,隨著中國更大規模、更深層面的現代化推進,每一個中國人都在越來越多地面臨著一個具有嚴重意義的問題:城市化的推進,將會給中國鄉土社會帶來什么?在一個更加敞開的、公共性空前增強的文化現場,1990年代以來一直處于私人化寫作傾向明顯的中國當代文學又將發生什么樣的變動?我們感覺,這些基于現實的思考可能會成為持續性很強的話題,從而提到文學寫作的理論觀察議程上。于是,我們邀約了兩位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及其理論研究的年輕學者,做一次現場討論,以期拋磚引玉,推進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主持:在世界范圍內,根據您的個人觀察,是否覺得農業文明以及它的影響力正在受到新一輪的削弱?
惠雁冰:回答是確定的,尤其在現代化歷程啟動時間較晚的國度里,對商業文化擁抱的熱情正在與農業文明的日漸頹敗形成絕妙的反諷。盡管有些國家采取了一些補救的措施,但這些措施類似于一種幾無內質的粗豪標簽,或成為工業經濟借以擴展領地的一種修辭性的策略。
梁向陽:這個問題不好回答,我沒有既沒有出過國,也沒有所謂的“世界性”文化視野,不敢進行橫向的比較。但我以為人既然要吃飯,就要有糧食,就要有農業的存在。而工業化的農業能否安全地確保人類的繁衍生息,這仍然是個問號。所謂的轉基因糧食雖然高產,但是否安全,這仍是個未知數。我的結論,農業文明是哺育人類繁衍生息的最安全的文明方式,它理應有著合理的存在邏輯。
主持:我們姑且把“出生地”所在處稱為故鄉,那么根據您的理解,這個實有的故鄉,它在當今條件下的人文精神領域的位置是什么樣的?
惠雁冰:我曾經在前些年買過一套小書,題目好像叫“正在消失的事物”,涉及五行八作,農事人情。我對故鄉的追憶,常常要靠這一套小書來梳理思路。吊詭的是,當處身的故鄉完全要依憑線性的圖畫來取得與現實的聯系時,這樣的故鄉可能只是精神性的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民眾當下的心理結構中,故鄉已經被淡化到只是一種念想、一種回憶,一種置身其中卻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的精神圖景。
梁向陽:故鄉永遠是靈魂的歸宿之地。中國古人云:樹高千尺,落葉歸根。人就像一只在天空中飄泊的風箏,不管你飛到多高、多遠,永遠有一根線來牽著你的心,這就是故鄉。尤其是這個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故鄉的靈魂領航者的作用更為突出。
主持:我們有時候感到,故鄉好像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您覺得在現代中國的文化氣候里,故鄉的精神性在場與上述兩個問題有著什么樣的關聯?
梁向陽:我以為不管是精神的上故鄉,還是實有的故鄉,它永遠“在場”。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會“不忍登高臨遠,望故鄉渺邈,歸思難收”,將一腔腔鄉愁訴諸于紙,吟成詩、賦成詞。人是文化的動物,人具有精神性,我以為在強調物欲享受的當下,更需要強調精神的力量。
惠雁冰:在如此暴力性的社會變革中,故鄉的精神性在場尚不失為對現實的一種有聲色的阻抗。盡管這種阻抗是一己的,抑或是靜穆化的,甚至是美化而富有詩意的,但畢竟為我們日益呆鈍的靈魂開啟了一扇自我舐慰的暖窗,并使物質主義的喧囂中隱存了一絲的欸乃的槳聲與晚炊的青煙。也許其最重要的意涵倒在于昭示,人不僅需要物質性的生存,同樣需要精神性的皈依。
主持:當今中國正在發生的一些農村變革,您最為關注的是什么問題?
梁向陽:我最關注的問題是農民的出路問題。中國的“城鄉二元社會”制度,使農民處在先天劣勢位置,也決定了他們的奮斗注定要比城市人口艱難。若一旦在就業制度上不能確保“公平競爭”,這將導致廣大的農村人口看不到前行的希望,這也是我所最最擔心的問題。
惠雁冰:我最關注傳統鄉村的頹敗問題。賈平凹小說《秦腔》,我一直非常喜愛,竊以為這的確是為子孫后代“立碑子”的一本大書。可以說,在急速變遷的中國農村現實中,只有賈平凹深刻把握住了時代的流向以及這種強悍的流向所給予鄉村的顛覆性影響。可以說,賈平凹為整個鄉土中國唱了一曲深長的挽歌,挽歌中有著常人所難理解的溫情與善意,也有不斷閃現的焦慮、憤激,更有面對大潮無力回天的矛盾與困惑。從這個意義上講,賈平凹以他蠻癡性的鄉土姿態,演繹了故鄉精神性在場的全部內涵。
主持:如果說,中國農村的未來狀況必然和城市的發展走向勾連在一起,您覺得這是一種幸運還是一種悲哀?現在,農民和土地開始互相脫離的傾向仍在受到鼓勵,您覺得這里邊有沒有文學性言說的新空間?
梁向陽:人類的生存方式可以有許多種,城市化未必是最好的一種。好像在目前情況下,許多人理解的現代化似乎等同于城市化。農民脫離農村,追求幸福生活這無可厚非。但是,城市以及整個社會做好接納農民的準備了嗎,我不敢妄下斷語。文學是人類的想象,人類只要有夢想,就一定有文學言說的空間。
惠雁冰:這一點很難說幸運還是悲哀。幸運與悲哀的心理體驗既取決于躋身城市的蹇旅者的審美視向,同樣也取決于渴望走出土地的務農者的現實訴求。當我們指摘故鄉身影不再,轉而希望能有一塊寄存心靈的園地時,又該怎樣看待拿到土地征遷款的農民們即時升騰的征服城市的光榮與夢想?每一個社會屬體在面對時代的變遷時,都有自己的特殊訴求,這種訴求的背后是切實的生存體驗與無所不在的文化傳統。所以,回答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鄉土化”與“被鄉土”分別指涉的是哪一類社會屬體?文學言說的空間當然有,我感覺“留守文學”已經顯示出精神上的貧困,對征遷后一夜暴富的農民生存現狀的體察,倒不失一種可行性的視角。
主持:對現在寫到農村、農民、農業的一些底層文學作家,或者準備在這個領域投入創作精力的未來年輕作者,您有什么建議或意見可以提供?
惠雁冰:“底層文學”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不僅包括農村中的務農者、城市的農民工,還應該包括都市中的普通市民階層。現在的底層文學所反映的內容過于逼仄,應該有所拓展。
梁向陽:要用心來體驗你所要表現的對象,要用心表現來你所要建構的豐富的文學世界。我想只要全心身地投入到這個世界中,你總會能找到合理的表達方式。
主持:對中國農村的觀察。現在有一種說法叫“空巢農村”,或者“空殼家庭”,許多村莊現在出現了人去室空的景象,春節一過,村子里多年聚居的大家庭就像分崩離析一樣,只剩下老弱病殘孕。您覺得這種現象對未來中國的損害是什么?您覺得,現在的勢頭還會維持多久?
惠雁冰:這種現象對未來的損害可能體現在中國經濟結構鏈條的松散,以及中國整個社會結構的失調,也就是說社會生態不平衡。從城市化的進程來看,這樣的勢頭可能風頭正健。
梁向陽:傳統的農業文明體制,也創造了一整套與之相匹配的文化制度體系。譬如春節,就是典型的農耕文化節俗。農村現在成了“空巢農村”,進城務工的農民依然是城市的“邊緣人”,不能有效地融入城市體系中。似乎整個農民階層已被“懸空”了,處于一個更加“邊緣”的位置,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恐怕這個問題解決不好,遲早會出問題的。
主持:新農村建設,現在我們特別關注它的和諧問題。但如果農村人都進城了,或者農村人的心都進城了,農村會不會成為城市發展的一個附屬品?在這種情況下,談論和諧是否就會失去它的現實依據?您覺得,我們能否扭轉這種看起來十分困難的局面?
梁向陽:我曾在《延河》雜志2006年第10期發表過一篇措辭激烈的文藝評論《關注當下農民生態,就是關注和諧社會建設》,已經系統地表達過我對農村、農民與農業問題的關注。我當時的觀點是:“欲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就不得不關注當下的農村的景象;欲構建‘和諧社會’,也不得不關注當下農民的生存狀況。”
中國農村問題是長期的“城鄉二元”體制下所形成的系統問題,要解決起來自然有難度。我以為為政者只要有關切之心,建構確保農民生存與發展的合理制度體系,總是能夠能夠找到避免問題出現的辦法的。
惠雁冰:農村的概念,本就是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一個環節與城市相對而言的,建國之后,“鄉土”向“農村”的指稱變遷,已經預示了中國農村城市化的道路,這與中國百年來的恥辱、貧困及其催生的現代化焦慮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之后,延續并加快了這種社會發展的思路。所以,從目前國家的發展路向上來看,農村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一個附屬品。現在所提出的和諧社會,與匡正歷史性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失調的社會改革理想相去較遠,尤其是地方政府將新農村建設越來越作為一種形象工程來經營。要改變這種現狀,就要看國家的政策力度。
主持:在您接觸過的農村生活范圍里,有什么人,或者什么事(現象)讓您產生了寫作沖動?您有沒有考慮過這方面的寫作問題?
梁向陽:我出生在陜北農村,最初的文學創作的出發地就是陜北農村。1980年代,我有機會闖到京城求學,已感受到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所形成的悖論。年少氣盛的我總是想雄心勃勃地拯救苦難的“陜北高原部落”,胸中有抒寫不完的激情。現在想來覺得好笑,你連自己的命運也拯救不了,更遑論拯救別人。年輕人應該做點夢,甚至是不切合實際的、好高騖遠的夢,這對人生有好處的。
惠雁冰:我的家鄉清澗縣可以說是在城市化進程中變化不大的一個縣,縣城、農村的好多地方還是延續著舊有的生活傳統。我的父母、奶奶、我的親戚都曾讓我有訴說的沖動。但因為工作問題,暫時還沒有考慮這方面的寫作問題。
主持:如果客觀地評價一下當前中國農村問題的文學寫作狀況,您舉得成績和缺陷哪個更大些?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一下您的印象和評價,您最想說的是什么?
惠雁冰:盡管現狀不盡如人意,但成績還是大于缺陷。我感覺現在的創作者輕易地放棄了對生活的深刻體驗,所以,關心農村者不少,但真正的精品不多。我還是推崇柳青、路遙那種視創作如生命的作家,我最想說的是路遙的一句話,“只有初戀般的真誠與宗教般的情感,人才能成就某種事業。”
梁向陽:前些年,著名文藝評論家賀紹俊先生曾說過:“我們很少能讀到一兩部真實反映當下農村生活的有影響的文學作品。這是一個應該引起文學界憂慮的事情”。其實,這個現象現在依然存在。文學本身雖是審美的意識形態,擁有時代屬性,這無可厚非。但是對于有良知與有承擔的作家而言,不關注八億農民的生存與發展,這是一個說不過去的問題。
主持:農村在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時候,給人感覺它好像是一個象征符號,是臉譜化的,沒有什么特色,似乎也缺乏那種激動人心的文學力量。它好像是作為一個模糊的、抽象的“故鄉”在文學藝術中存在著,我們一生的使命就是在進行與它有關的逃離或是皈依。這種感覺原來應該是彌漫在古典文學中的一種感覺,在這方面,我們現在好像正在與那種傳統背道而馳。不知道這種感覺對不對?
梁向陽:你的感覺很對。鄉村在中國古典文學的意象中,一直是古代知識分子的心靈休憩之所;到五四時期的作家筆下,已經成為承載“化大眾”思考的“道具”,借以傳達一種急切改變社會的焦慮聲音;在解放區作家的筆下,鄉村成為農村“翻身記”的載體,傳達了革命的話語邏輯。然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席卷而來之時,我們許多書寫農村題材的作家已經“找不到北”了,既不屑于解放區文學的優良傳統,也放棄了五四作家的書寫品格,做出一些無病呻吟的“四不像”飯菜。文學是人類良知的一種存在形式,任何時代的作家,只有投入時代的激流中,才能有大的出息、大的作為!
惠雁冰:我的感覺也正是這樣,關鍵是創作者沒有把自己融入到生活中,如果都像柳青一樣,離開大城市,去長安縣一呆十三年的話,情況就遠遠不是這樣。問題是,現在還有這樣一些“有出息的作家”嗎?
主持:苦難意識和問題意識,是我們寫到農村題材時始終繞不開的一個精神區域,您舉得這樣的寫作是不是有些千人一面的程式化嫌疑?我們的認識局限和突破方向可能會是怎樣的?
惠雁冰:對,從趙樹理、張賢亮就開始了。突破的路徑應該是從生活中找感悟,而不是從政策中找方向。
梁向陽:現代社會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始終以“現代化”的標準評判農村現象,呈現在文學作品中的思維自然是較為相似的,這是它的不足。然而,中國廣大農村生態的豐富性與復雜性,并不能用簡單的邏輯概括就能窮盡與詮釋的。我的理解,人類的創造與其思維密切相關,思維方式的改變直接影響到文學想象的突破,而思維方式與社會環境相關聯。要在法治的體系下允許作家以多元的思維方式思考中國農村問題、思考農村問題,這是突破的前提。
主持:在農業文化的書寫中,請您列舉出您最為認可的兩個人,或者一兩部作品。
惠雁冰:葛亮《阿霞》、賈平凹《秦腔》
梁向陽:新時期以來,我國出現了一大批擁有深度的農村題材作品,均給人以深刻的文學啟示。相對而言,我更喜歡路遙,因為他是新時期作家中較早地正視中國城鄉二元社會對立、并用文學的方式來思考農民出路的有良知的作家。他的小說《人生》、《平凡的世界》自問世以來,就一直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文學的本質不是華美的語言與復雜的結構技巧,而是展示人性的光輝,傳達一種精神與力量。就這方面而言,路遙做到了,他所建構的文學世界給了我們溫暖、給了我們力量,使無數社會底層的奮斗者在追逐美好未來的道路上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