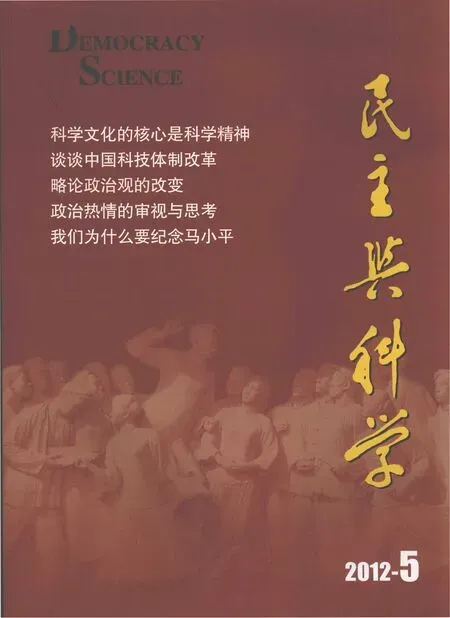我們的思想離真實有多遠
■李海霞
我們的思想離真實有多遠
■李海霞
研究生復試,感慨良多。為了考察復試生有無求真的素質,我問:“一個人感情用事或者客觀誠實,會對科研產生什么影響?”一考生回答:“這都要從正反兩個方面來看。客觀誠實有利于了解事實,但是太多了也不行。它有頑固保守、不利于創新的一面。感情用事可能摻雜主觀情感,但是思想活躍,容易創新。”我一震,不相信考生們不理解客觀誠實和感情用事這對兒常識性概念,又問了13名考生,只有一名明確傾向于客觀誠實。有人還說“感情用事”者感情豐富,搞科研就是應該傾注感情。有個男生竟斷言:“感情用事是理性的。”在他們眼中,客觀誠實無所謂褒義,感情用事也無所謂貶義,似乎后者還更有益。
其實糊涂不是偶然現象。在“辯證法”的掩蓋下,人們模棱兩可地生活在混淆是非的醬缸里。一般的人從來沒有問過自己:“我正在說的這句話是真的嗎?”真假不分意味著真假的概念沒有真正形成,“人”還是功能主義的動物,即使掙揣到“精英”也沒有大不同。試想一只狼見到了羊,會去追索羊的物理化學和生物本真嗎?它只想到解饞!
科研是追求真理的活動,離開了實事求是還有什么話可言可信!追求正義也必須在認識真相的基礎上進行,否則無法區別公允和偏愛。客觀誠實唯恐不足,還會太多?只有“科研”的動機不潔,才會認為客觀誠實會阻礙科研。尊重事實,是一切理論和決策達到正確的必要條件。科學研究需要感情不假,但不是私情,而是求理解、求進步的熱情。也只有這樣才能具有開明的心態。
感情用事是不理智的沖動行為,受欲望的奴役。它源于認識能力和自控能力的低下,所以感情用事者短于分析推理,短于耐受勞苦,沒有探究能力,何以創造新思想?他們憑感覺下結論,難免對真實存在進行曲解和強奸。
創造性思維要求的基本素質是客觀、精確、內部一致、深廣、論證性和批判性等,每一條都與主觀模糊平庸的感情用事相悖。感情用事者是通過感性的好惡而不是理性論證來評判事物的,疑懼使其避新。且不說實行多數決定的制度有多艱難,就是推廣良種作物,甚至連生活上的一點小改變,比如拿菜當飯吃一頓,也是難以接受的。
感情用事是人類的原始反應,類人猿更為嚴重。大猩猩動不動就用手啪啪地拍打胸脯,情緒激烈。記得有個故事,一只攀樹玩耍的幼猩猩不慎吊斷樹枝,跌下來大聲尖叫。其成年猩猩以為是旁邊觀察的科學家害的,兇神惡煞地向他沖過來。科學家站在那里,紋絲不動地盯著它。這頭野獸沖到即將打到他的地方,震懾于他的威嚴而停住了腳。其實,類似的胡亂歸因現象在大多數人身上長存,一件事情沒做好,我們不是總抱怨條件和運氣不好嗎?
認為感情用事有那么多“積極意義”,原因有二。一是把感情用事和感情豐富混淆,事實上感情用事的心靈狹隘易變,導致寡情薄情;感情豐富者多情活躍,悲天憫人。另一個是把欲望和理由混淆。想現實怎么樣,現實就“應該”怎么樣,欲望就是理由。
任何時候,直面真實都是最明智的選擇。唯真話可能有見解,唯真話不會與自身矛盾。人向客觀跨進一步,就是向真理跨進一步,鄙薄真實就是返回愚昧。出污泥而服染,則心中的“科研”、“客觀誠實”、“感情用事”、“創造性”、“理性”等概念當然是一團迷霧,幾乎所有概念都是一團迷霧。一個人假如犧牲私利說過一次真話而不后悔,就不會把客觀誠實同頑固保守捆綁在一起;假如扎扎實實創造過一個新觀點,就不會認為感情用事適合創新。
這些考生都已經通過復試,將來的研習道路走向何方?